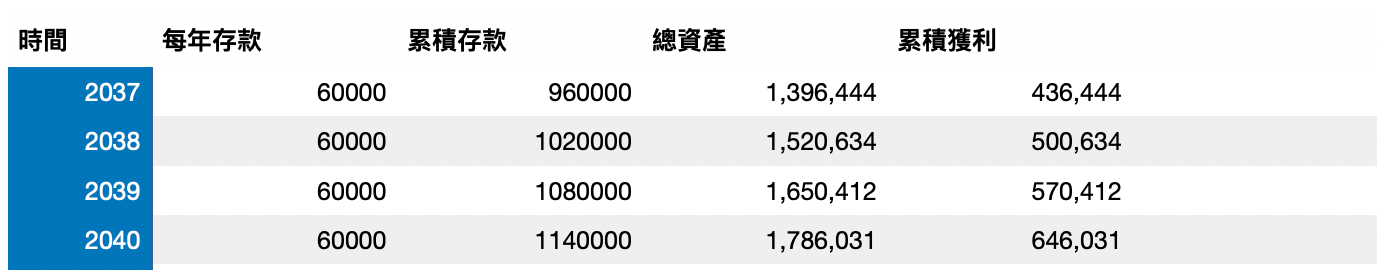他日我若爲龍神
1
除卻崑崙虛已被血祭陣法覆蓋之後,還剩下包括扶陵宗在內的八個節點。仙盟連同修真界所有家族、宗門、散修,分散勢力鎮守八個節點。爲求支援快捷,便修築了傳送橋。
大戰一觸即發,師父面容衰老得越發厲害,他也曾攬鏡自照,嘆息若有一日故人魂歸,大約再也認不出來他。
扶陵宗的事務基本上都已經由大師兄接管過去了,前些日子,師父自覺力竭便鄭重將掌門的位置傳給了大師兄,藥長老因爲近年爲修真界研製魔毒解法,不幸遭魔氣侵擾隕落,二師兄便接任了他的位置。
玉已真人原本從獨子殷舟死後就精神萎靡,又遭晚爾爾背刺,索性閉關去了,一時找不到接任的人,只好由我這個面冷的師姐來短暫替代一段時日。
我記得當初仙門大比之前,我和師兄們醉倒在雪地之中,梅花落滿了後山,宋萊放言說等大師兄接任掌門之後,一定要讓他當藥長老。當初展望已經實現,卻沒想到是以這樣的方式。
變故來的比我們想象得更快。
空明寺原本也有一個節點,做好了萬全的準備,但這次乃是魔神親自率兵,傳送橋在魔神揮手的那一刻便失去了效用,畫地爲牢,前後不過一刻鐘的時間,空明寺這樣澄澈的佛門之地便染透了鮮血。魔族水黑色的戰旗就插在空明寺上方,纏繞着魔氣的金色血祭就這樣用血繪就成了。
我站在扶陵宗的最高處,遠遠地可以那裏風雷滾動,但叫喊聲也聽不見,應當佛門子弟死的時候心中也並無怨氣。
空明寺的女佛子無羨很喜歡我,因着當初我和她在仙盟相伴除魔時所說一句:「小師父殺生,乃是爲了救天下生民」。據說這句話讓她當時心結陡然一解,於是給我留下一枚舍利至寶,乃是她寺高僧坐化後留下的。我見那處硝煙滾上雲霄時,手中所拿着的一粒舍利,突然碎裂開來。
我把頭埋進大師兄的肩膀上,哭泣道:「小師父死了。」
大師兄拍拍我的背,以示慰藉。
宋萊紅着眼睛,他看着我,咬牙切齒:「朝珠,事到如今,你還說謝如寂成了魔神,還站在我們這邊嗎?空明寺都是他帶着人屠戮的,陣法都已經成就。他親手推着修真界往着滅亡的路上走,你還要爲他說話嗎?」
我看着遙遠處升騰而起的黑氣,良久才聽見自己的聲音:「我信,我信他。」
我什麼都不能幫他做,便只有堅信不疑地相信他。宋萊怒視着我,如同看一個無藥可救的瘋魔之人,他指着外頭,揚聲道:「朝珠,你睜開眼看一看,他殺了多少人了!」
我睜開眼了,我早就睜開眼了,我看清謝如寂了,我會相信他。宋萊會意,再不與我多談。
旁邊有弟子抖着嘴脣問道:「我們是下一個,還是下下一個?」
誰都不知曉答案。扶陵宗內也湧進許多修士,都是爲了守護扶陵宗抵禦魔族來的,有個癩頭道士在正殿裏睡得七扭八歪,怎麼也睡不醒。癩頭道士道:「等魔族大軍到時再叫醒我,他孃的,睡飽了纔有力氣打架。」
大師兄早已敲過無數次重鍾,將門中弟子長老都叫到正殿裏來。大師兄眉眼和煦,白色的長髮再未束起,垂到了腰側,他道:「血祭陣法,修真界都已經明悉,空明寺因魔神帶大軍已經失落,扶陵宗不是下一個目標,就是下下一個、第八第九個。宗門弟子,都是來學道的,沒有叫你們送命的道理,若有要離去的便可以離去了。」
無人離去,都無聲地給自己點好了神魂燈。
大師兄抬起眼,看着陰沉天際露出的一線白,神情平靜,即使是經過這樣多的傷亡,親眼見無數神魂燈熄滅,大師兄和我們,還有宗中弟子,修真界無數修道之人,都堅信着那句話。
大師兄的聲音在正殿之中迴盪,這次並非用作鼓舞人心,而是單純地只是陳述一個事實:「天下大道,唯正道日日興隆。」
我原以爲謝如寂會把我們留到最後一個,沒想到第五個就輪到我們了。前頭的宗門、家族無一倖免,魔神之力下,凡人豈可阻擋?
2
我留在了扶陵宗,大師兄看着我幾次欲言又止。我才嘆息道:「師兄,我一點都不害怕,這樣的場景我比你們早很多就經歷過了。鯉魚洲的事務我也已經安排好了,從旁系挑出來了一個孩子,若我身故,就是她替我接管鯉魚洲。她比我還堅韌,也勤快可愛。我這次怎麼樣都要護一護扶陵宗的。」
他看着我,像是看着已經長成的妹妹那樣驕傲。
扶陵宗的護山陣法,守住了魔族小半個時辰,魔族沿着我曾爬過的三千玉階上來,又被靈炮給轟下去。此時還佔有上風,我踩在山門前的石碑上,宋萊心情緊張,便故意和我取笑緩解焦慮:「朝珠,你就和那個山大王一樣的架勢。」
但是下一瞬,他有點笑不出來了。靈炮轟飛處濃煙滾滾,魔族本還烏泱泱地往上爬,卻突然頓住,很有自覺地往兩邊退開,有人於煙霧處提劍拾級而上,周遭妖魔癡狂興奮地叫起來。
他黑色的長靴先露出,再是繪有暗紋的玄衣衣襬,握如寂劍的手修長好看,最後露出他卓絕的眉眼來,小半張臉已經被魔紋覆蓋。大師兄當機立斷,幾乎立刻大喊道:「後退十丈!」
諸人急退,他話音還沒落的時候,護山陣法被強大的神力給覆蓋,千百年前扶陵老祖飛昇時所留下的陣法便這樣破了。無數的妖魔在這一瞬間湧上來,謝如寂行至其中,安靜而冷漠。
我年少剛入扶陵山時也曾一腳踏在這石碑之上,倨傲地看着從三千玉階拾級而上的玄衣少年,扯過他的高馬尾,一點不見害臊,大聲道:「我們鯉魚洲的洲主夫人,待遇可是很好的,你確定不再瞭解一下嗎?」
如今我將將二十,已活了兩世,妖鬼嬉笑之聲貫徹向來和樂的扶陵山,周圍已經大亂起來,弟子與妖魔短兵相接。我緩緩抽出劍鞘之中的玉龍劍,磅礴的靈力在我周身翻湧,一劍下去不知幾何的妖鬼被劍風割裂,化作濁氣重新隱入世間。
我躍入混亂之中,宋萊沒抓住我的手,只能絕望地叫一聲:「朝珠!」
我沒回頭,一路穿過妖鬼,行至謝如寂前頭,他不避不讓,看我的眼神與在魔宮之中、前世殺我之時別無二致。我刺向他,他未曾躲讓,依照着原來的軌跡繼續拾級而上。妖鬼擋在他的面前,以身軀抵擋我的攻擊。
我再近一寸,重新發起攻勢,揚聲道:「謝如寂,出劍!」
他手中所握如寂劍從未抬起半分,我被魔神之力逼退,往後落到在扶陵宗前的空地上。宋萊看準了時機把我往後一扯,眼角發紅道:「朝珠,你他媽不要命了?」
我仰頭卻笑出聲。我剛剛體會到了修真之人與魔神的差距,如果說普通修真者之間,境界之分還可以靠對兵器的悟性、修煉的訣法來彌補,譬如我靈力皆無時還能和已是金丹的晚爾爾打了個百招,但與神力之間,完全不可行。
我捏着宋萊的手,把證據擺在他的眼前,大笑道:「謝如寂,沒對我舉劍。」
宋萊不能相信,我竟然因爲這個理由衝上前去。其實我只是想給他看,我的少年郎,乃是這世間最好最胸懷大義最臥薪嚐膽最背盡罵名的人。
他是那樣好,便也請你們,相信他。
我已經重新拿起玉龍劍殺魔了。然而扶陵宗終究不過負隅頑抗,我看見那個一直很想找謝如寂學劍的小師弟,在謝如寂身後發起攻擊。謝如寂頭也沒回,小師弟就被旁的妖魔給咬破了喉管,他倒在地上,血一直從他的喉管往外湧,成了腳下血祭中被獻祭的一部分。
直到他死,謝如寂也未嘗知曉,曾經有一個小孩來扶陵宗,爲了找他學劍。
謝如寂開始出劍了,劍風過處無聲無息,血濺於無形,廝殺的範圍從山門處,一直往後山的禁林延伸去。一路血流成河,一路血祭陣法緩緩浮現,已經有了大致的輪廓。
近年扶陵山的碧桃花沒能開,禁林旁的銀珠花倒是雪一般地開着,無奈被壓倒,被染上猩紅的顏色。
我看見大師兄因護着一個剛入門的小孩,被鬼氣掀掉大半的皮肉來。宋萊原本就不擅長打鬥,看着滿宗倒下去的人,鮮血一直漫過腳下,他突然轉過頭,把我往前一推,沒有再固執糾結於我盲目信任謝如寂的問題。
宋萊帶了點狠意和決絕:「朝珠,去尋你的玉龍門,去爬師父和你說的大荒山,別把自己白白耗在這塊,扶陵宗的血祭陣法已經攔不住。」
他倒也未必把希望寄託在我身上,只是大難臨頭要師妹保全性命罷了。前世扶陵宗被屠宗,也是他推着我往前走,叫我快跑。
我擦去臉上的血,啞澀道:「師兄。」
他怒罵出聲:「別和我在這裏糾纏,後山的道你最熟了。快走!」宋萊這般說道,回身將一個妖鬼刺穿。
我再不猶豫,穿過銀珠花,沿着後山的路下了扶陵山。宗中管制嚴格,不許隨便下山,尤其是玉已真人一貫愛盯着我倆糾錯處,我和宋萊自己尋了條隱蔽的道,時常去扶陵宗附近的村鎮集市去玩。
我沿着小道走,沒再回頭看,卻也知道那裏血光沖天,廝殺聲逐漸減弱,乃是漸漸浸入死一般的沉寂。
我的扶陵宗,再一次沒有了。
3
我去西洲的大荒山,尋找神器玉龍門了。
或許是運氣差、命也不大好,之前尋神器的路上總是十分坎坷。但我已經沒什麼好顧慮的了。我這條命,是二師兄強塞給我的。
師父曾道大荒之地,失落之洲,原本靈氣就枯竭,也不是修真人可以輕易涉足的。之前翻閱卷宗時,上頭說道西洲黃沙遍地,烈日炙烤,它那裏沒有靈氣,便也不許修真人動用靈力。無論是離突破飛昇只差一線的化神境還是剛入門的築基,行走在西洲都沒什麼不同,都得靠自己的雙足,走到因黃沙磋磨皮爛骨露也不一定能找到大荒山。更何況其中有兇獸橫行,險象環生。
我已經預備好所有後果。
可真到了西洲,卻感覺和卷宗上描述有所不同。黃沙漫卷不錯,卻已經生了茵茵細草。烈日苦辣不錯,卻有老樹可以依靠庇廕。我在大漠之中行走,前後都沒有生靈,卻未曾覺得害怕。
口渴難耐時,側邊便有一眼微泉,如同天道饋贈。
沒有兇獸橫出,沒有異象困擾,我便這樣一直往前走。行至一處,我卻突然頓住,蹲下身看着老樹根底的一點痕跡,上頭淺淺有一個鑿痕,約莫是無意間所留。
我直不起身來,這條路已經有人替我走過。試過黃沙炙熱燙骨、烈日苦辣難忍,他令茵茵細草生出,於荒洲種下老樹。他斬平凶煞蠻獸,化去狡詐險象。他將這條通往神山的路掃平一切阻礙,後頭的人不生疑心、走的正道坦坦蕩蕩。
我不能大哭,便如他的意往前走。
日月顛倒幾度,西洲的星星漫天,像是隨時會被風吹落。這裏與九域隔絕,便也不知曉外頭戰況。剩下的幾個節點,是否又被魔族侵佔。我的師兄們死守扶陵宗,總算是又留下我一個人。
生者比死者更加可悲,死的人一了百了,可我覺得我纔是被困在血祭陣中之人,承擔着他們的悲痛往前走去。我這兩世加起來,已經走了夠多的路,這回該我走到盡頭了。
長夜到了末尾,頃刻間褪去,一線天光大亮起來,神山就在我的眼前,太陽正從它的背後升起,金色的光芒照亮整座關山,也將我籠罩在其中。這裏沒有界碑,我心裏卻十分肯定,這就是關山。
關山自有路徑,無須我再劈開亂石闖出一條路,真到此刻的時候,我內心反而一片平靜。我攀登神山,到金光只籠着山巔一點的時候,終於到達,神器玉龍門懸浮於此,已經等待鯉魚洲的後代來尋已久。
它是神器,又取了個玉龍門這樣威風的稱號,樣子卻一點也不出奇,不過是個中空的框子,隱隱地散發着藍色微光。我慢慢地往前走近,眉心的金色印記逐漸發燙,全身的血都沸騰起來。玉龍門如有所感,周身的光亮愈發明朗。
我卻突然止步,回身看向來路,山水迢迢、萬里來路早已看不明晰。
我在崖上坐下,風吹拂過我的臉。我所相識的那些人的面容在我眼前飛旋而過,母親柔善微笑、大師兄牽着我的手站在山門前、宋萊和我相約偷雞、玉如跌下斷背山、晚爾爾將我一劍挑下登雲臺、賀辭聲摘下他眼上的白綾、無羨殺生以救蒼生、姨母在點兵臺聲嘶力竭、玉已真人張開手臂護住身後人、師父點着他眼角的細紋,無數的面容如同霧散。
最終我看見玄衣少年朝我轉過頭來,猶如鏡中花、水中月,他道:「你當真歡喜我嗎?朝珠。」你當真不是葉公好龍嗎?
我聽見自己的聲音,我說:「是。我歡喜你。謝如寂。」並非葉公好龍,我看見你,喜歡你,追逐你,相信你,我會救你。
我站起身來。大風吹動我的衣袖和鬢髮,玉龍門也顫抖起來。我這次,毫不猶豫地、果斷地握上了神器玉龍門。我體內的玉龍血咆哮,裏頭每一代洲主的聲音都在我心間響起,是那樣的欣喜。
玉龍門飛出去,變大變闊,懸立在山巔之外,金光日照玉龍門。
我倒退幾步,什麼都沒有動用,往山崖外奔跑出去,正如年少時在靈海邊赤足奔跑,穿過了玉龍門的那一剎那,天底間響徹玉龍長吟之聲。從我的頭到腳,穿過玉龍門的時候成了龍首、龍身、龍尾,此處西洲的限制再也不能困住我。
我看見時間的軌跡,大風中的過往,靈氣和魔氣在萬物之中游走。
我看見前世因,今生果,我死後謝如寂從叔父神魂手下奪回軀體,殺遍魔族,以一半神力倒轉時間,回到我們都還沒開始難過的時候。但他不記得了,我也不知曉。故而如今他雖爲魔神,卻只能與叔父周旋,他只有一半的神力了。
4
我看見了萬里之外的景象,乃是屍橫遍野的殘酷。我在西洲跋涉的時間太久,魔族攻下扶陵宗的節點之後,又一口氣侵佔了幾個節點。
九域之中只剩下最後一個節點沒被血祭覆蓋了,最後一個節點不在宗門家族之中,是在一處黃沙之水流過的平原。這個節點正是所有祭陣的最中心處,也是血祭套陣中,最核心的一個。
修真界還剩下的所有力量都匯聚在此,魔族亦然,此乃生死之戰。
贏則生,敗則死。
黃沙之水已成了血河,戰旗倒在地上,巨大的祭陣即將築成,其他八個節點的祭陣顏色也越來越明晰,九域的血祭之術終將完成,從此世間再無靈氣。修真界幾近暮山頹勢,魔族戰車上妖魔鬨笑,已經想好該如何掃蕩人世、茹毛飲血了。
謝如寂行至祭陣中間,祭陣曠大,無數的符文在他周身盤旋,把他晦暗的眉眼照亮。
修真界有人於血泊之中聲嘶力竭地怒罵:「謝如寂,你爲練成血祭,殺死這麼多人,真是罪不可赦!」
「你看看天下因你而流的血,你還有沒有心!」
謝如寂一概不理。祭陣的輪廓越來越細緻,其中所蘊藏的可怖力量讓所有人都心中一驚。
染透無數鮮血的血祭陣法終於大成,分佈於九域的血祭同時啓動,血色的紋路迅速蔓延完九域的每一寸疆土,衆魔亂舞起來,修真界的諸人面露絕望。
謝如寂身後的戰車上,他的叔父、魔域的主上站起身來,振臂高呼:「從今往後,天下該以魔族爲尊了!」
叔父垂眼看向謝如寂,眼中終於掩飾不住他貪婪的目光,他驅動攝魂之術,預備在這裏萬衆矚目的時刻奪舍,成爲新的魔神。他胸中澎湃無比,卻在片刻後頓住,他陡然發覺,他與謝如寂之間的聯繫,突然斷開了。
他控制不了謝如寂了。
這一刻,血祭陣法終於露出了它原有的面容,纏繞在表面的黑氣逐漸退卻,只剩下原本的金色將整個九域都籠罩起來,神光所過之處妖鬼被殺滅,所化成的黑氣不再流往世間,反而都被綿延整個九域的陣法給吸收,最終通通匯聚到黃沙之水的這個核心陣眼當中。
謝如寂在整個陣法的最中心,他單膝跪在地上,無數的黑氣湧入他的身軀之中。
謝如寂的叔父驚愕之下湧血,此刻才意識到不對,他大呼道:「謝如寂,你沒中我的攝魂術!你一直在騙我!這究竟是什麼陣法?趕快換回去。」
平原上無數的魔族大軍,在與修真之人搏鬥的、正要往前衝的,爲金光所威懾,通通灰飛煙滅,化爲黑氣,又捲入了陣法之中,流向謝如寂體內。短短片刻,謝如寂已經吸納了整個九域所有的魔氣。他站起身,將這代替他父親幾十年、安排好他一生的男人扯下戰馬,將他枯瘦的頭顱摁在陣眼之中,叔父發出慘烈的叫聲。
謝如寂平靜道:「斬盡天下邪魔的陣法。」
我師父從血泊之中踉蹌起身,不可思議道:「這是伏魔陣!這並非是改造世間清氣的血祭之陣。是用天下修真人熱忱之血驅動,來除盡世間邪魔的伏魔陣!」
原來,從謝如寂初初入魔開始,打的就是這樣的心思,借魔族之力爲天下鑄就伏魔陣。在繪製血祭陣法圖時就偷龍轉鳳,魔族拿着的陣法圖,從始至終都是僞裝成血祭之陣的伏魔陣。
他忍受罵名,墮入魔神,與叔父所周旋,終於得償所願。
叔父的皮肉一寸寸潰散,黑氣想要潛逃,卻被陣法一概收納。
謝如寂便如此摁着他的叔父,摁着分明是他唯一親人卻一直殘害他的叔父,融入了陣法之中。
陣法還在運轉,謝如寂跪在陣眼之中,將自己所有的神力都傾入伏魔陣中,無數曾因獻祭陣法而死的人在此刻復生。
5
我於神眼之中窺見景象,諸般變轉不過在很短的時間內發生。我心急如焚,以龍身匆匆從西洲出發,穿雲過霧,終於落到了那片平原處,我看不見別人、聽不見別人的驚愕聲,只看見天地間跪倒一個身影。我化爲人身,踏在被伏魔陣染透金色的泥土上,卻像不會走路的人那樣,差點摔倒在地。
謝如寂的魔神之身,已經因吸納過多魔氣而幾近崩潰,神血從他的肌膚表面滲出。他一向穿玄色,就算受傷也不過是顏色加深一些,他一貫又是會忍痛的人,看起來還像平常那般。可是誰知道他只是憑着最後一點力氣,撐着脊骨呢?
周遭修真界之人已經有人反應了過來,有人大喊道:「趁此機會殺了魔神!」
我師父回身就給了他一巴掌,罵道:「沒良心的東西,再分不清黑白清濁,滾去和孟盟主一起蹲大牢,要麼我把你和這些邪魔一起按到陣法裏去。」
我已化爲人身,慢慢地向謝如寂走去。他抬起眼,血順着他的下頜淌下,很少笑得這樣平和。
生生明火,明暗無轍。
謝如寂張開口,血便湧出來,他道:「天下邪魔已盡,世間再無魔氣。從此八方太平,山河無憂。舊神將隕,新神已生。朝珠,你的前路,有無數金光照耀。」
神殞之時,蒼山崩殂,天雷滾滾。黃沙之水沸騰起來,衝湧來去。他從未露出一點對自己的悲慼。謝如寂向來無愧天下,唯獨虧欠他自己。
「你曾道有日夢中,見扶陵宗碧桃花開放,我卻入魔殺你滿宗門。如今如寂劍就在我身旁,現在是你報仇的時候了,你我便當真兩清。世間最後一個邪魔,也就此被誅殺。」
我早已停住,淚流滿面,嘶啞道:「兩清?誰要和你兩清?前世今生無數世,我都要和你糾葛到底,生死不休。謝如寂,求求你,別把我一個人留在這裏,沒有你,我往後該追逐誰?」
謝如寂柔和地看着我,一身血污,眉眼間盛滿了破碎的金光,他道:「追隨你自己。你早已找到自己的本心,不必再記掛我。」
我奔走兩步,卻總是跌倒,我分明已是龍神,卻像還在蹣跚學步的無知幼童,幾乎是爬一樣地到了他身邊。謝如寂的眉眼逐漸黯淡,連身軀也支撐不住。在倒下的那一瞬間,我抱住了他,下頜蹭在他沾滿血污的發頂,大哭着祈求道:「別留下我一個人,謝如寂,我不知道怎麼才能走下去。」
他沒有聲音,我感覺他的氣息幾近全無。
沒有謝如寂,我能怎麼在塵世滾滾裏面走下去?
我要花上多少年,多少個輪迴,窮盡千世無數世去贖罪?我眼前一片黑暗,看不見來路光明,謝如寂,你騙我,明明我的前路再沒有金光照耀。我只能聽見自己撕心裂肺的哭聲。
我眉間發燙,朝龍留給我的那滴神血湧動,我於不可見的黑暗之中窺得一絲天光。我剜開心口,龍神之血滴落謝如寂的口中,他因吸納魔氣而崩潰的身軀被緩慢修復,氣息逐漸平穩起來,謝如寂艱難地睜開眼。我大悲大喜,欣喜若狂,龍神之心頭血,終於救他一命。
黃沙之水滾滾而來,已經漫過了堤岸,衝湧而上。不可數的高山接連倒塌,曾經劃過整個九域的地裂之口往四周蔓延。我已經看見了九域的軌跡,因着魔族撞倒不周山、顛倒結界,又連續戰亂,諸道混亂,九域的壽命已經走到了盡頭。
我說:「謝如寂,也許我不曾告訴過你,不論你是謝溯,還是謝如寂,抑或是什麼魔神,我是真的很喜歡你。」
喜歡到十五歲時給你帶銀珠花。
喜歡到十九歲時穿着嫁衣嫁給你。
只是我倆運氣都差了那麼一點,前世今生,都沒能得到一個好結局。
謝如寂猛然叩上我的脊背,如有所料地抬起眼,眼尾魔紋瘋長,飛石落下。我輕聲告別:「抱歉。再見。」
我把謝如寂的手扯落,站起身往外走去。
他分明已經力竭,又剛從閻王爺那塊被我搶奪回來,早已虛弱無比,卻還是往我的方向絕望而狼狽地攀爬幾步。謝如寂一瞬間忘記了如何行走,又忘記了如何呼喊,他是驚愕痛楚下的失語人,是遭受剜心之痛的癡情人。
最終謝如寂只能徒然地見我以龍神之軀,化身龍脈,填補江河地裂。
我用玉龍的形態,在九域上面盤旋一週,我看見高山生瘡,江河倒灌,九域之間分崩離析,無數人哭泣受難。
一道地裂劃過九域,逐漸增大,將世間生氣消耗殆盡。我於雲霄之間俯身,衝撞入地裂之中,以龍神之靈與身軀填滿溝壑,此地再成龍脈,以滋養萬物。
我與謝如寂,都願世間再無邪魔,願天下太平。
願諸人安康,從此喜樂無疆。
6
我以爲我早已身死道消,卻被困在一尊神像裏頭,變作了一尾小魚。不知哪個偷工減料的匠師竟將神像裏頭注滿了水,我閒得無聊,便從上往下地遊動着玩。
扭動着身軀看見尾巴時,我仔細看了看,才發現原來是一隻未長成的小龍。我心中好受了一些,堂堂龍神復生,至少不是一尾小鯉魚了。
我透過神像的琉璃目往外看,來拜這尊神像的人竟然十分多,絡繹不絕的。神像所置環境竟然莫名眼熟,我想了一會才意識到,這裏是洲主宮。很久之前鯉魚洲遭遇那場大火時,我姨母開出護洲陣法的祭壇,原先老龍神朝龍的神像就已經被推倒了,眼下不知道是誰的神像新修在這裏。
我心裏有些酸溜溜的。
其實我在這裏其實也挺好的,這些洲民上供的香火全進了我的肚子,周遭都是暖洋洋的白光。但是我的師父、我的師兄們,還要一個——我絞盡腦汁地想,只記得是一個穿玄衣的人,他們怎麼都不來找我!我就被困在這神像裏頭呢。
我這般想着,卻在神像下頭看見了一個穿着玄衣的人。
他安靜地站在那裏,抬眼看着這尊神像,神情分明那樣平靜,可我卻感受到了一絲柔和。我覺得我前世肯定認識過他,他也一定是我的仇人,不然爲什麼一見到他,我的心裏就酸澀疼痛呢?
來供奉香火的人來了又走,唯有他一直站在這裏,陪在旁邊,比我藏身的神像更像是一尊神像。
等到暮山窮盡顏色。靈海上也有了粼粼的光,再也沒有人來問津這尊神像了。他才動了一下,我翻了個身嘆息,他也要走了嗎?
沒想到他往神像這邊來了,我感覺被一股柔和的力量包圍着,從神像的琉璃眼處帶着下降到了神像的底座,底座居然可以掀開,水也沒往外邊跑。
那人俯下身,湊到底座前面盯着我,他的臉對我來說有些大,生得倒是好看,若我身死之前有洲主夫人,想必也該是這個模樣。但是看他的時候我總有一種想要流淚的感覺。可是我是一隻小龍,哭不出來。便只好撞上他高挺的鼻樑。
他卻突然怔住,喉間哽澀好幾次,纔出口道:「朝珠?」
我憤怒地跳躍起來。知曉我的名字。知道我的名字還不把我交給大師兄,交給我師父,交給那個穿玄衣的人,可我記不清他的長相,也記不得他的名字。我突然發現,眼前這個青年,穿的也是玄衣。
他看了我很久,像是重見故人,不敢多說一個字。
很久他才伸出手,浸入水中,把我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捧到自己的眼前,額頭輕輕地抵在我的龍角上,我原先預備撞他一下的,卻看見他眼角落下了一滴淚。
他竟然哭了。
7
我常常被這人攏在袖中。我生前也大小算是個龍神,沒想到復生之後還要依仗別人才能活,話說到這裏我又仰起頭喫下了一粒他喂的糕點。
鯉魚洲興盛昌隆,我親眼見着容姑喊他一聲君上,哪裏來的君上?我怎麼不知道鯉魚洲還有這樣一號人物。可這不知來路的君上把鯉魚洲管得比我還好,我心裏難免不平。
等他伸出手逗弄我的時候,我便扭過身不理他了。他便耐心地將我的鱗片擦得乾乾淨淨,帶我出去暖和地曬太陽。
我因救蒼生之故,鯉魚洲乃至九域都設有我的廟堂,就連洲主宮前新設的神像也是依着我的樣子塑的。不知是哪個匠師,所鑿刻面容十分細緻,處處可見用心。龍神朝珠的神像被很多人供奉着,每日的香火都不少,源源不斷地進了我的肚子裏來。
這人帶我去了扶陵宗,我發覺扶陵宗的碧桃花終於又可以開了,吹過扶陵宗滿山青翠。世間終於又回到了原本的安寧。
我見到了師父和我的師兄們,師父這幾年空閒下來,終於有時間重新琢磨他的駐顏之術,好賴回到了從前七八分的光景。大師兄當掌門當得已經很有一套了,隱隱有青年老成的模樣,我見了他十分歡喜,雀躍着就要往他的方向挪去。
卻被這玄衣人淡淡地捉住了尾巴帶回來。
大師兄問道:「幾年過去了,有這樣多的香火祭祀,朝珠還沒有化形嗎?」
那玄衣人的指尖落在我的龍角上,道:「尚且沒有,但她已有了神智,記得你們的,我就帶她回來看看你們,想必她心中十分高興。」
二師兄宋萊正蹲在我的面前,一副看見泥鰍的模樣,嫌棄地撇撇嘴。呵呵,我一點都不高興看見這個二師兄。宋萊直起身道:「那她和你一直待着,應當整日更高興。」
玄衣人的動作一滯,默然很久,才道:「沒有。她不記得我了,朝珠把我忘了。」
師父知道他的難過,便出聲安慰道:「謝如寂,你別急,當初你用魔神之身和天道做抵押換取朝珠復生的時候,天道不說了嗎,會把她全須全尾地還給你。」
原來我能復生,並不是運氣好。有人用自己的身軀爲籌碼,來換取我回來。故而他如今不再是神明,只是一介普通的凡人。
「我不急,我有很多時間,很多很多年,去等她記起我。我餘生,只做這一件事。」
8
我這樣享受了香火幾年,日子過得也算舒心。這玄衣人對我實在不錯,帶我走了很多地方。我時常有零碎的記憶閃過腦海,卻又沒能抓住。
有一日他把我放在洲主宮的清池裏頭,山崖上的風一直懶洋洋地吹進來,白色的紗被輕柔地捲起。
那玄衣人正從山崖處往清池走來,身姿挺拔,那時我就覺得身體有些異樣。
他朝我走來,如同前世今生每一世做的那樣。我的龍角開始消失,按在池壁上的龍爪也變成了白皙的手,黑色的長髮散落下來,我終於衝破了阻礙,修成了人身。
無數的記憶在我的腦海之中如煙火般炸開,我仰起頭,看着離我越走越近的玄衣人,聲音很輕。
「謝如寂。」
「我們是回家了嗎?」
他在我面前單膝蹲下,伸出的手輕微顫抖,最終落在我的臉上。
他說:
「是。朝珠,我們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