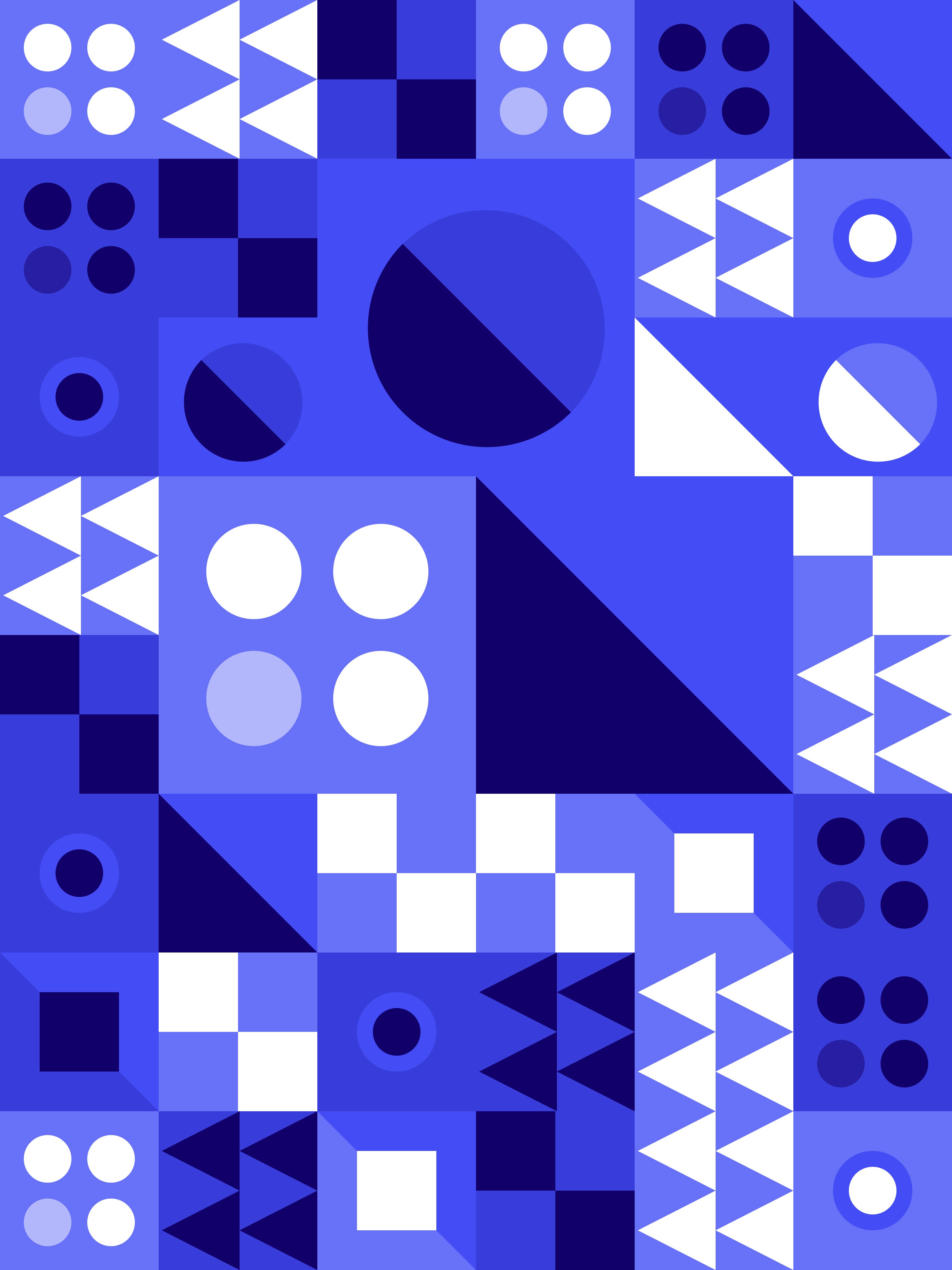《蝶還・梁祝》(7.1) 顛倒陰陽
馬文才懷揣著從梅疑霜那兒拿回來、那條他送給梁山伯的大紅汗巾子,大步踏入家門,猛地推開一扇扇門,急著找梁山伯問個明白。
因勾春散而起的藥效未全然消去,眼下他心火又起。
雨硯和冰墨難得看見他一臉怒火,紛紛不敢吱聲,默默把路讓開。馬文才一路找到了梁山伯自己的書房,才看見梁山伯正坐在一堆文件冊本中,凝眉苦思。
「文才?」梁山伯正埋首於蝶報消息本中,突然聽見身後門被猛地打開。他回頭,卻見馬文才臉色鐵青站在門口。
「你不舒服嗎?臉色怎麼這麼難看?」梁山伯心中犯嘀咕,猜想是不是馬文才從梅疑霜那裡聽到了什麼。「和梅少商談不順利嗎?」
「這是什麼?」馬文才從懷中拿出那條鮮豔的大紅汗巾子給梁山伯看,梁山伯的臉刷地一下白如金紙。
「看來,你知道我從哪兒拿回來的啊?」馬文才冷笑,一屁股坐到書房裡放的簡易睡榻上。
「文才,不是你想的那樣。」梁山伯蒼白著臉,微微抖著唇說。
「那我還能怎樣想?」馬文才又舉起那條紅豔豔的汗巾子,在空中抖了抖:「汗巾子是何等貼身衣物,你的竟然會落到了姓梅的手裡?還是我特意新送你的!」
「文才呀!」梁山伯起身離開椅子,奔到馬文才面前,拉著他的手跪下。「那是誤會!」
「誤會?」馬文才那雙極少興起風浪的眼睛,起了點風波:「那我問你,你有沒有他的?」
梁山伯思忖一會兒,小心翼翼地答:「有。」然後急忙解釋:「但我準備拿去燒了。」
馬文才只覺得血往自己腦袋湧,頓了好一會兒,又問:「是什麼顏色的?」
梁山伯既感覺莫名其妙,又心裡緊張:「鮮綠色的。」
「還綠色的?姓梅的真是想讓我戴綠帽啊。」馬文才扶著自己的額頭,苦笑。
「文才,文才!真得不是你想的那樣的。我和他什麼都沒做。」梁山伯準備辯解。
「什麼都沒做,卻非清清白白,是嗎?」馬文才拿開扶著額頭的手,將梁山伯一把從地上拉到榻上擁著。
「小梁兒,你厭倦我了?」馬文才緊緊擁著梁山伯,聲音嘶啞地問。「這幾年,我為了蝴蝶會,大江南北的跑,常常一兩個月不在家,你寂寞了?」
「沒有!絕對沒有!」梁山伯急得哭出來,「你怎能這樣說我!」
馬文才將臉埋在梁山伯的肩頭,半天不說話;梁山伯忽然感覺肩頭的衣服濕了,心中不捨加難受,可是一下子也不知要說甚麼好。
「小梁兒,我不能沒有你,你知道吧。」馬文才繼續臉埋在梁山伯的肩頭,「就算你倦了我,能不能……別離開我?」
梁山伯心知馬文才是位心高氣傲的男兒,要他這樣低聲下氣,實在傷他的自尊。梁山伯邊哭著,邊把馬文才的臉捧起,道:「我從沒厭倦你,從沒不愛過你。你為了蝴蝶會,為了這個國家奔波,我都懂;雖然你不在的時候我寂寞,但是我的一顆心總是牽縈在你身上呀。你想要我怎麼證明我的心呢?」
看見梁山伯哭得梨花帶雨,馬文才心中不忍,含淚將他擁入懷中,緊緊抱著。「證心最難,你不用證給我看。」
「可是,你懷疑我。」
「不疑了,不疑了。看著你,我知道你真心。」
二人相擁好一會兒,馬文才說:「那,小梁兒,能夠跟我說說,那條紅汗巾子是怎麼到了他手上的?」
「那天我去了宮裡見過幾位嬪妃娘娘,出宮後,就換回衣服,在京城裡蹓躂一下。就巧遇了梅少。」梁山伯一邊回想,一邊設法不去刺激馬文才。「他邀我去他在京城小宅賞花,我不疑有他,就跟去了。」
「這個男人真是一條豺狼。」馬文才低聲磨牙忿忿地說。
「原本也沒什麼,就賞花吃酒。只是,那酒吃了一碗,讓我力氣都沒了。他……他就把我給摁倒了。」
「去他娘的,我要跟他去算帳。」斯文的馬文才口出粗言,急得梁山伯抓緊他的袖子才安靜下來。「他有無對你胡來?」馬文才急問。
「他本來想的,後來因為我哭得厲害,他停了手。」梁山伯一臉通紅,「然後,他就扯下了我身上的紅汗巾子,繫上了他的。說這都什麼交情了,要交換一下信物,以後好見面。」
馬文才抱緊了梁山伯,心中疼惜。「還好,沒發生什麼。真的沒發生什麼吧?」
「沒有。」梁山伯搖搖頭,雖然有那一秒回想起梅疑霜撫觸的技巧真得不錯。
「那麼,你是怎麼拿回我的紅汗巾子?」換梁山伯發問了,換馬文才心中一驚。
「這個……無論我說什麼,你都不要誤會。」馬文才身上微微冒汗。
「哦?」梁山伯睜大了眼睛,立刻想到什麼,問:「難不成,你和他……?要不然,你怎麼會拿到汗巾子?」
馬文才忙緊緊抱著梁山伯,深怕他溜走。「那個……我這裡,也是個大誤會。」
梁山伯挑挑眉,半疑半信。
「我不是去找他商談入股蝶錦莊的事嘛。他就擺了一桌酒菜,說酒過三巡再談生意,我就連喝了三碗酒。對!就是那酒有問題。」馬文才忙道。
「然後呢?你也全身無力,被梅少摁倒在床上?」梁山伯急著接話,發揮推理:「然後梅少對你胡來?可是,文才,向來是你在上,怎麼可能換成你在下了?」
「說什麼話,就算我醉得一塌糊塗,也不會當下面的那個。」
「所以,是……梅少在下面?」
「嗯。」
「你怎能如此對我?因為他比我好看?」梁山伯氣上來了,想要掙脫,卻仍被緊緊箍住。
「別急啊,小梁兒,聽我說。」
「有啥好聽你說的?你一旦在上頭,任憑九牛二虎之力,你是絕計不會半途停手的。」
馬文才急了,忙在梁山伯臉上親了一口安撫,繼續道:「那酒被下了藥,一定。三碗我竟然就醉了,還把他當成你。不過,我發誓,我收手了。」
「怎麼可能?」梁山伯狐疑道。
「因為他叫錯了。」
「叫錯了?」
「你不是在我們那~個的時候,都叫我『才郎』嘛。他叫得是馬郎,我就清醒過來了,收手了。」
不知為何,梁山伯心中一陣感動。「才郎~」梁山伯望入馬文才的眼盼,輕喚。
原本快消去的勾春散,忽然又燒了起來;加上「才郎」聲助攻,馬文才身下一發不可收拾。
他推倒了梁山伯,準備行周公之禮。
「等等,文才,你不覺得梅少這樣離間我們,好像有什麼陰謀嗎?」梁山伯問。
「的確有問題。不過,現在不談這個,山山,你得幫幫我,姓梅的那廝給我下的藥還沒消……」
房外,雨硯和冰墨候著隨時伺候主人。他們聽見裡頭的動靜,不禁搖了搖頭。
「哎,真是床頭吵,床尾和。」
「老闆和老闆娘這對夫夫真是情比金堅啊。」
「欸,我得去準備洗澡水了。」
「說得是,我該去準備潤潤膏了。」
兩人偷偷壞笑起來。
作者悄悄話
- 馬梁小倆口,誤會解開了就好。真是萬惡的梅九少
- 馬梁感情出現危機,然後出現轉機
- 不是羅生門,而是內褲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