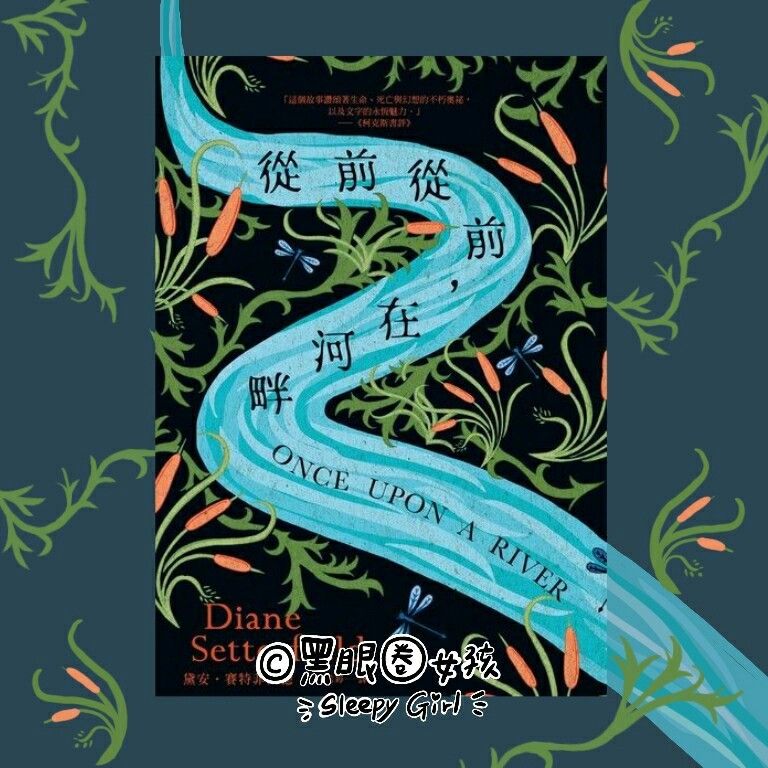「你究竟要長到幾歲,才能懂得分辨是非?」
當他這樣大聲斥問,把她逼得退無可退,再往後一步,就是無盡的深淵了。一旦掉下去,那墜落的心理驚恐,雖然是她這些年所熟悉的,但這一次,如果連一點點懺悔都不能夠表達,那從未來到永遠,都只能活在無法探底的自責中。而人世間有什麼過錯,值得這樣的煎熬?
在我的記憶裡,有一類電影的方向和「療傷」相反,力道卻是很近的。它們說的都是「愧疚」。那裡面有《七生有幸》,有《全面啟動》,有近期的《海邊的曼徹斯特》,還有《贖罪》(Atonement)。而如果比的是悔恨之深和無力感的無限綿延,則《贖罪》不會有對手。算一算剛好十年了,那池畔凝結的夏日愛戀,夜裡發亮的綠色長裙,小白昂妮細碎的腳步聲,和那雙看透了玻璃窗格、看見別人沒看見/看不見的事物的眼睛。那麼早熟,那麼精緻,卻暗藏著危險。那是被針扎破了手的童年。
而這是個愧疚的故事。
在二戰前夕的英國奢華莊園裡,大小姐瑟希莉亞和管家的兒子羅比相戀,又說不出口。這天下午,他們尷尬對峙的一刻,和當天夜裡激情的纏綿,都被瑟希莉亞十三歲的妹妹白昂妮撞見了。未經人事的她,誤讀了其中的人際意涵,再在一連串的巧合(或不巧)之下,誣指羅比成一樁性侵案的犯人。就這樣,羅比被逮捕入獄,接著戰爭爆發了,他從軍渡洋,和瑟希莉亞分隔兩地……
《贖罪》改編自伊恩麥克伊旺(Ian McEwan)的同名小說,以三段式的結構講一番過錯,和它對三個主人翁生命的重創。在敘事和跳接上,它的風格是強烈的,第一段彷彿《烈愛風雲》的光色中,反覆細細地描寫僅僅是一個下午和晚上、改變一切的事件始末;第二段戰時,詩意與慘絕兼具,來回穿梭在時空的前後,人物的聚散之間,既說記憶的不可靠,也嘆亂世羈絆的難以捉牢;最後第三段只有短短幾分鐘,一場戲的篇幅,把所有的偶線一把抓起,誰是傀儡師?誰是被擺佈者?誰是慈悲而誰在不捨?都紮成一個結,難以緩解。
這樣的節奏調度,讓全片既有大時代的氛味,也有細膩的人物凝視,在核心訴說的那個痛,又被包裹著,一聲聲、一聲聲呼喚著。
而整個故事是從白昂妮的角度去描述的。她既是這場風暴的推動者,也在中心處,更是真正承接後果的倖存者。從開場第一個鏡頭,就暗示這是她寫的一齣「戲」,她喜歡劇本,又更嚮往小說,因為「小說可以只靠文字,但戲劇必須依賴其他人(的演出和詮釋)」——初看這句話,你想這真是孩子的傲氣啊!想要控制一切,不願意讓任何人參與。但事後想想:她其實多麼希望自己在乎的人的命運,可以由她安排說了算?可以想給他們幸福就真的幸福?她多麼希望自己不負責任的、天馬行空的編織,影響的只有自身,無痕無害不會牽動其他人?
但那都是不可能了。這是個愧疚的故事,愧疚的來源不是無心,更接近無知。但這不是藉口。這怎麼能是藉口?《贖罪》殘忍地道出:即使是小小的幼稚的惡意,也可能造成「大人」式的宿命傷痕。我們都說童言無忌,那是輕巧和寬容,如果這小小的扭曲扳折了大大的命運岔路,如何還能一笑置之?在電影最後,我們得知羅比和小希的終局——他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仍然被憤怒和恐懼追著,在夢裡大叫,在醒來的片刻對同袍說:「我保證你再也不會聽到我的聲音了」,沒想到一語成讖;而她在根本來不及置信的幾秒之間,已經被淹沒在水裡,那曾在陽光下把她赤裸裸的激情洗亮,封存著午後微溫的記憶之水呀,竟成為她永恆的歸屬了。
這一切,在達利歐·馬里安利(Dario Marianelli)如泣如訴的音樂中,由導演喬萊特(Joe Wright)娓娓道來,戀情甜入心,鄉野和莊園厚重的空氣壓頂,分隔兩地的思思念念,和那文句的緊緊抓縛,在戰場的徬徨中,在大後方的無能為力裡,交錯出一點一滴的不忍和不甘心。分別飾演三階段白昂妮的演員:十三歲的瑟兒夏羅南(Saoirse Ronan),十八歲的蕾夢娜葛瑞(Romola Garai),和七十七歲的凡妮莎蕾葛瑞芙(Vanessa Redgrave),則最為耀眼:
瑟兒夏羅南在這之後,又和喬萊特合作了非常出色的《少女殺手的奇幻旅程》(Hanna),那雙碧色的眼睛在《贖罪》裡,即使還沒開始散發外星人似的氣息,但纖細又早熟的滿滿思緒,已藏在眼眸之後,讓她參與的每一場戲都張力嚴重傾斜;而凡妮莎蕾葛瑞芙畢竟是皇后級的人物,那段只靠口白,只用說話的抑揚頓挫和眉眼間的猶豫和力不從心、脆弱以及袒露,就把整個故事的後設做到完滿,把敘事格局墊高的演出,真的太神奇了。
不過,現在的我發現,蕾夢娜葛瑞在中段的演出,或許才是難度最高的。在壓抑和「空」掉了的神色裡,撐起一個角色的轉換期,她說:「直到現在,我才漸漸明白自己犯下的過錯造成什麼」。於是回到文首那情境,當她終於去拜訪姊姊,遇到幾乎失控的羅比,那只能一再呆滯地重述:「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抱歉……」的無助,真叫人心疼。而詹姆斯麥艾維(James McAvoy)在此和葛瑞的對戲,一個流暢如水如針地逼問著,一個只能招架不住地應和,那是狂風對弱草的不留情。
但是,心疼又如何?慌亂又如何?她真正最無助的,是只能在薄如草葉的紙上,用輕如鴻毛的筆,寫給他們一個夢。那場戲中有短短幾秒,當她看到姊姊出聲安撫羅比,溫柔地說:「快回來,回到我身邊……」這時候鏡頭拍的是白昂妮驚魂未定的表情,和連忙別過頭去——在這裏,一部分的她仍無法直視別人的親愛,不知道如何消化這場景;另一部分是看到了自己造成什麼,造成最親愛的人多大的憤恨和痛;還有一部分,是當我們跳到戲外去提醒自己:這一切都是白昂妮的幻想,是她多麼希望真的「曾經發生過」的。那麼,這是她在提醒自己「我奪走了什麼」吧?
那個神情,對我來說,即是全片的精髓了。
片中那場關鍵的圖書館溫存,我們先從白昂妮的視角,看到那無聲的書架上,大蝙蝠般交纏的兩人身影,那畫面讓幼小的她心生恐懼;然而包括這一段,及前述水池邊的窘立,都從不一樣的角度被複述兩次,一次是白昂妮「所見」,一次是小倆口完整的相處。如同打字機每一行到結尾,都要回到行首,才能繼續說下去。從片末我們知道——這一切都是老白昂妮的觀點,包括她所看見的,與她無法看見、但相信(或希望)的「真相」。也因此,相對於白昂妮的三個時期,瑟希莉亞和羅比從頭到尾都是同樣的形象,因為他們早就是她記憶裡兩張永恆的臉。那些甜蜜,那些告白,那些歡笑與不捨,其實都是她的信仰。
這也解釋了為何,片中所有瑟希莉亞和羅比的戲都那麼「文學」,那一枚眼神一流轉,一點光色一交織,都彷彿排練好的舞台和對白,不只是情愫燃起,還有戰時相隔兩地,那信中的字字句句,那外在的詩意,都是一個小說家內裡的宇宙所輝映出關於愛情、宿命、思念與盼望的星辰風景。
而風景越淒美,星空下的兩人越渴求彼此,就越折磨下筆的人。當羅比在戰場上跋涉,有個鏡頭是他忽然撞見就在眼前、數十個被槍殺的女學生「屍橫遍野」,那突兀的畫面除了控訴天地不仁,道出戰爭中人性的泯滅,也多多少少是白昂妮在藉著筆尖,鞭笞自己吧。身為某種程度上的同行,我們都明白書寫的療傷力量,越是寫下那些耽溺的、放不下的、思念或不捨的,就越能夠釐清和篩透,留下美好的,把痛苦忘掉。但這一切的前提是——傷口只在自己。是轉心一念之間,就可以海闊天空的。
當記憶的盡頭只有愧疚,當犯下的過錯怎麼樣都無法彌補,那樣的書寫只會碰到一堵牆,而一再提起身子往牆上撞去,那不是在整理傷痛,那是在逼自己不要忘記。
白昂妮給這故事下的標題是「贖罪」,即使她讓他們聚首了,卻沒有讓那當中的自己被原諒。寫下這樣一部小說的她,不真的能「贖」還什麼,只有細細地記下自己的「罪」。就像青少女時期的她,不斷地藉由照護他人,想洗清自我的厭惡,但即使救了百人、千人,也彌補不了曾經傷害的唯一。
但她畢竟做了一件溫暖的小事。她陪伴那個頭部受創的士兵,聽他說了最後的一些話,她聆聽,彷彿真正參與了他的「故事」。這樣的慷慨是對方僅僅需要的。
終究《贖罪》是個說「故事」的故事。小白昂妮看到一個場景,自己補上情節,這樣的自作主張造成悲劇;老白昂妮用一個故事對我們告白,也給了他們最後的善意(a final act of kindness)。故事活得比人長,故這不只是送他們一份禮,也是對自己永恆的懲罰。但你我陪伴一個將死之人,聆聽她的故事,也就彷彿參與了她,也就能夠選擇、稍稍原諒她了。
這樣的慷慨,是她僅僅需要的。在那無盡墜落的途中,若能有一絲絲的光,一點點探底的希望,就彷彿有個聲音在對她說:「我知道了。我知道你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抱歉喔……」
編輯:閃編
封面圖片來源:Pixab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