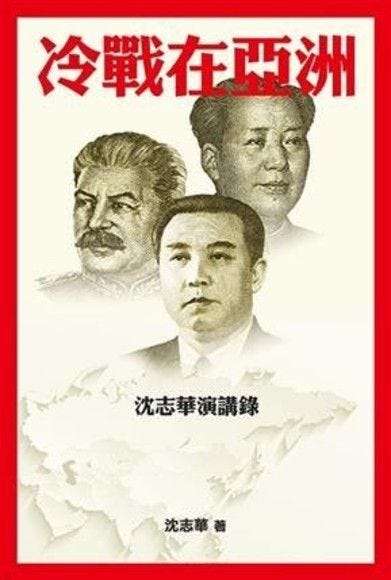作者自問:或許最好的方法是問自己,若是對歷史一點都不了解的話,對現在是否會有什麼影響?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
第一個首先要問的,我們要面對的是誰?第二個同樣重要,我們是誰?這就好像在看後照鏡,如果你一直往後看顯然會妨礙行進,但是它會幫助你是從哪裡來的,還有誰跟你走在同一條路上。對冷戰時期的雙方來說,最大的危險就是他們不瞭解彼此。美國只看蘇聯外交詞令的表面意思,理所當然地認為蘇聯的擴張只是想稱霸世界。而蘇共也是認為資本主義國家正在醞釀陰謀,一定會來干擾他們獲取利益、革命成功的決心。
事實上,受到先天地理環境跟歷史因素的影響,蘇聯也承襲了莫斯科公國以來的憂患意識(註1.),由於他們的國境缺乏天然屏障,不僅有過金帳汗國武力征服並稱臣的歷史。也因此常受到像是克里米亞汗國或土耳其、拿破崙或納粹第三帝國的攻擊。他們的政權首要之務,就是要尋找緩衝地帶以保護心臟地帶,並發展出「禦敵境外」、「擴大緩衝區」的積極防守策略。
當尼基塔.赫魯雪夫一九六二年把核子彈頭部屬在古巴境內的時候,他的部分動機其實是要讓美國徹底感受一下,自己國土處於巨大威脅,究竟是什麼感覺。而這點在俄羅斯-蘇聯史當中向來是非常了解的。
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在中國取得全面性的勝利。雖然當時美國對中國的了解遠勝於對蘇聯的了解,仍然在資訊不足、被誤導的情況下錯解他們的想法。像是評估中國共產黨處在史達林的控制之下、中國會盡全力發動韓戰等等。僅有少數的瞭解中國專家們認為以兩國巨大的文化差異,毛澤東無疑會成為亞洲版的狄托。(Tito,南斯拉夫的共產主義領袖,才剛戲劇性地與史達林決裂)而事實上,中蘇兩國決裂正是十年之後發生的事情。
作者強調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要素:如果你不知道其他人的歷史,你就不會知道他們的價值觀、他們的恐懼和他們的希望,或是他們如何回應你做的某件事。還有另一個原因是:那就是以為別人都和你一樣。
羅伯特.麥特瑪(Robert McNamara)拉花了許多時間,試圖去了解美國在越戰的時候做錯了甚麼。他的總結是:「我們對敵方和友方都做出了錯誤的判斷,」麥特瑪拉說道:「這表示我們對該地人民的歷史、文化和政治是如此的無知,也非常不了解他們領袖的人格特質跟習慣。」這,就是美國在越戰中犯下最大的錯誤。
遺憾的是,小布希政府並沒有從中記取教訓,不僅沒有表現得比波斯灣戰爭更好,作者認為如果他們努力了解伊拉克的歷史,也許就不會對當地人對於石油遭到掌控不滿而感到意外;從而犯下這種錯誤,陷入阿富汗跟伊拉克的戰爭泥沼。
知道歷史也有一個更明顯好處:避免懶惰的一概而論。「那些不願意記住過去歷史的人很容易重蹈覆轍」,這句話是喬治.桑塔耶那(George Santayana)的名言,也是一句政治人物、其他公眾人物看起來想要有格調的時候很愛用的格言。
不過歷史的確很有效的提醒我們過去的錯誤或麻煩。例如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同盟國決定這次德國跟其他軸心國成員不能再宣稱從未被打敗。他們對軸心國的策略是無條件投降,而德國、日本和義大利都在戰事結束後遭到佔領,另外他們也努力重塑這些國家,讓他們脫離非民主和軍國主義思想(沒有完全成功)。當有些人抱怨這個作法就好像羅馬共和國加諸於迦太基的那種野蠻的和平,美國的將軍馬克.克拉克卻說現代很少聽到關於迦太基的消息了(日後筆者會提及)。
當羅斯福總統和其他西方領袖討論關和計畫戰後世界時,他們心中還存留不久前的記憶。他們想要建造一個健全的世界秩序,好讓這個世界不會再次淪入彼此衝突的狀況。
所謂的戰間期-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日子其實極度不穩定,部分原因是國際聯盟缺乏主要國家的支持,聯盟也不是很穩固。這次,羅斯福下定決心要讓美國成為新聯合國的主要成員,他也準備好讓蘇聯加入以保持世界的穩定及繁榮。一戰後的一九二零年代並不是非常穩定,經濟大蕭條則讓一九三零年代變得非常緊張,各國為了世界安定建立關稅壁壘,以保護自己的勞工及產業。
但是對單一國家有利的政策,對世界卻並非如此,貿易和投資環境受到限制而變得更差,也導致國家彼此對立,作者認為無論如何這也是二次大戰的導火線之一。
為了避免這樣的狀況,布列敦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被建立了起來,世界銀行(WBG)、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國際貿易組織(WTO)(後又改名世界貿易組織)等等都是為了讓世界經濟穩定並鼓勵各國自由貿易而建立的。這些組織機構對於一九四五年後的國際秩序提供什麼樣的幫助,至今仍充滿爭議,不過後來一九三零年代的局面的確沒有再度發生。
我們的社會中有兩群人,他們特別仰賴於歷史作為指引。他們就是商業人士和軍方人士。因為他們想知道,如果採取某項特別行動的話,成功的機會有多少?這項投資是否會成功?或是以軍方的觀點來看,這場戰爭是否會勝利?掌握勝利的辦法就是詳細檢視過去類似的歷史。這就是個案研究。
投資人可能會經歷失敗,但是正常國家的軍人大部分沒有看過戰爭,少數資深軍官可能參與過一兩場。人們可以做出逼真的戰爭模擬訓練,但他們無法複製真正的戰爭:充滿暴力、死亡與混亂。所以歷史就成為一個很重要的工具,讓軍方學習那些原因讓人打贏戰爭,以及同樣重要的:是什麼原因讓人失敗。
作者的觀察是:雖然每間軍校的武器和制服都不相同,但是他們仍然發現讓學生學習伯羅奔尼撒戰爭或納爾遜戰役,還是有些幫助的。
然而研究過去的歷史並不保證一定能幫助軍隊取得勝利。在一次大戰之前,工業化的進展讓各國的防禦能力變得越來越強。從美國內戰一直到一九零五年的日俄戰爭,溝渠戰加上威力、速率更強大的武器,讓戰爭的成本提升許多,卻只有少數人認真看待這件事。大部分歐洲國家都小看了這種地面上的戰爭,並認為對手(非歐洲國家)能力較低。這種觀點在一戰的壕溝戰中陷入膠著後才出現改觀。
舉例來說,法國受限於自己的軍事歷史影響認為要採取攻勢,法國軍方的策略者也很愛強調他們高人一等的武力、精良的訓練和人數眾多的軍隊,包括許多的裝甲部隊。作者認為他們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太過於缺少注意防衛方面的科技,一九一八年之後又花了太多注意力集中在這方面。就算包括飛機、機動砲、坦克車及其他各式機動車輛等等科技,足以讓他們穿越對方的防禦工事進行攻擊,依然遭到忽略。當法軍在馬其諾防線等待德軍的進攻時,希特勒的部隊早就穿越防禦線的西側往前挺進了。
近年來很流行的另一個類比是「幕尼黑」。這是一個象徵說法,意指一九三零年代民主政體對獨裁者採取讓步政策,卻沒有辦法阻止另一場戰爭發生。這是以一九三八年的慕尼黑會議所命名的,因為當時的英國和法國同意希特勒,第三帝國可以獲取捷克斯洛伐克使用德語的地區(蘇臺德地區),隨著希特勒日後的侵略,慕尼黑就成了面對侵略時軟弱的代名詞。
對於妥協/姑息主義感到不滿的批評份子說,如果民主國家能夠挺身面對希特勒(最好是一九三零年代德國重新武裝之前),如果他們能勇於面對義大利或日本,那麼或許就能成功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但是這樣的類比真的有意義?作者表示了質疑:這難道表示你永遠都不該跟敵人對話,並試著找出相同點呢?如果是這樣的話,艾森豪與赫魯雪夫、尼克森與毛澤東對話時,他們是否也算是妥協份子?在形勢嚴峻的一九三零年代,民主國家對於一次大戰的傷亡慘重歷歷在目,很擔心那些新式炸彈武器將會摧毀文明。內維爾.張伯倫等人當初沒有弄懂得是(因為事情總要回顧才能看得最清楚),他們誤以為希特勒會見好就收,以為一旦他滿足了「合理」的目標(德奧合併)之後就會收手。
一九五零年,當北朝鮮的軍隊進入南韓後,杜魯門總統了解他必須做出一些行動:「共產主義正在韓國產生效應,就像希特勒和日本在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前做得一樣。」他這麼說法被後來認為並沒有錯。以目前所知來說,毫無疑問史達林跟希特勒一樣,都認為自己將面對的是一場可輕易獲得勝利的賭局。然而,以史達林的舉動來看,如果事情變得太麻煩,他已經準備好隨時撤回對北韓的援助。但卻很少證據顯示,即使面臨民主國家的強烈反對,希特勒會放下對歐洲的野心。他已下定決心準備開戰。
談到歷史類比,甘迺迪說:「一九三零年代教導了我們一堂很重要的功課,那就是侵略性的行為如果沒有經過仔細檢視,將會導致戰爭。」面對古巴核武危機之際,他很明智地使用海軍封鎖而非全面開戰。幸運的是,他剛唸了巴巴拉.塔克曼(Barbara Tuchman)的書《八月砲火》(The Guns of August),這本書講述的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起源與經過,因此他深知一連串錯誤的判斷決策會導致什麼樣的結果。後來,甘迺迪的繼任者林登.詹森總統再次使用這個比喻,這次是用在越戰身上。當詹森必須決定是否與越南在陸地上開戰之際,他的幕僚們很仰賴歷史類比。他們也發現戰爭如果接近中國邊境,中國可能會出面干預,這不僅讓局面變得複雜,也限制了美國處理越南問題的方式,這是美國上次面對韓國問題時所沒有遇到的狀況。
但是談到英美對中東地區卻又成了負面案例:一九二零年代,勞倫斯(註2)批評英國政府干預伊拉克事務:「英國人被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帶進一個圈套,而且很難優雅光榮地逃脫。他們會陷入這樣的陷阱,是因為資訊不足的緣故……我們的士兵們,無論在印度或是英國都處於很糟地氣候和補給狀況中,但卻必須護衛一片很大的區域,每天都因為巴格達政府錯誤地政策付出代價。然而這個責任不應該放在軍隊的身上,因為他們只是依照該政權的指示去行事。」
二零零二年,英國與美國決定快速攻下伊拉克,重蹈近八十年前的覆轍:在一九二零年的夏天,英國軍方承受極大的壓力,必須鎮壓遍布全國的反抗軍,找到了一位合適的代理人卻沒有達成他們的期望。到一九五零年代為止,伊拉克一直都是英國影響圈之內一個重要的問題。事實上,英美聯盟當時用了二戰時佔領德國和日本的歷史,完全選錯了案例。
作者的結論總結是:當公民們無法了解當前發生的事情,或是對過去歷史所知甚少時,很容易聽信別人說的故事(筆者:這道理應該全球通用?)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歷史很常被用來強化向心力(通常會犧牲個人利益)、為自己錯待他人的行為辯護、用來支持特定的政策或舉動等等。若能對歷史有清楚的認知,將能幫我們挑戰教條式的宣言及普及論,不再人云亦云。
作者認為:總結這些歷史戰爭的教訓,美國對外決策應該要目標明確、才能火力全開! 要對目標明確的敵人開戰,但是不要對意識形態宣戰。美國不應該參與開放式的衝突,讓武力平白流失,並使得國內出現反對聲浪。因為入侵及佔領伊拉克這項錯誤,美國正拋棄自己過往建構的歷史,就是追求與他人的合作以建立世界秩序,以及長久以來反對帝國主義的歷史。
別忘了,美國可是作為他國殖民地的獨立戰爭而出身的,作者認為這正是一項不能再多的諷刺。阿布格萊布監獄虐囚事件和關塔那摩灣拘押中心的虐囚事件所顯示影響的,更是削弱他們自己對法律規範的尊敬之心。
歷史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這個複雜的世界,但是若認為看待事情的方法只有一種,或是以為只能採取某項行動,這些看法都是危險的(註3.)。
總結來看,作者認為歷史可以教導我們質疑領袖、謙卑、反思自己。因為領袖們並非永遠都是正確的,事實上正好相反。一八九三年,英國的海軍中將喬治.特賴恩決定私自下達夏季海軍調動指令。當他要求兩排平行的戰艦向後轉時,他的軍官指出這可能會讓兩艘船艦相撞。但是他拒絕相信部屬的判斷,當他搭乘的船隻維多利亞號被坎伯當號相撞了,他認為情況不遭因此指示附近船隻不要來救援。結果維多利亞號沉沒了,並奪走了他與另外三百五十七位海軍人員的姓名。
作者引用英國學者約翰.卡瑞(John Carey)所說的:「歷史最有用的任務之一,就是誠實的告訴我們,過去人們所追求的目標,現在看起來有多麼錯謬和不恰當。」奴隸制度不僅行之有年還有支持者。想想過去太陽與地球相對位置的爭議。維多利亞時代,許多人認為人類種族有高低等之區別。一百年前的國族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是家常便飯,幾十年前主流輿論甚至不相信黑人跟女性可以成為傑出的工程師或醫生。
因此,盲目追隨主流意見並相信自己這麼做絕對性的正確或偉大,也許日後看起來都是一件蠢事。倒不如謙卑為好。
「過去就像是一個外國世界,他們做事的方法與我們不同。」英國小說家哈特利曾如此寫道。作者以自己文化背景舉例:如果我們能了解到羅馬人家庭組成份子和現代西方的核心家庭很不一樣!那麼了解其他社會組成方式和價值觀的差異便會簡單許多。想當然耳,所有的價值觀都有相對性好壞的比較,並無絕對的高下之別。作者認為我們更應該經常檢視自己持有的價值觀,不要單純認為自己的觀點是絕對的好(這倒是讓筆者想起《想像的共同體》作者班納迪克的想法,他認為了解一個文化最矛盾的相對兩點才算是真正的研究。)。
作者樂觀的認為:檢視任何證據與解釋,認真看待所謂的宣稱與發現。只要歷史能讓我們學會謙卑、存疑、反思自我,那麼歷史就還稱得上是一門有用的科目。並沒有任何過時或是被任何新發明取代的問題。
歷史,可以借用當下,亦能享受其中。只要,別忘了謹慎處理。
(註1.):不斷對外戰鬥的背後,俄羅斯人心中著惦記著什麼樣的憂患意識?
(註2.):阿拉伯的勞倫斯
(註3.):可以參考單一故事的危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