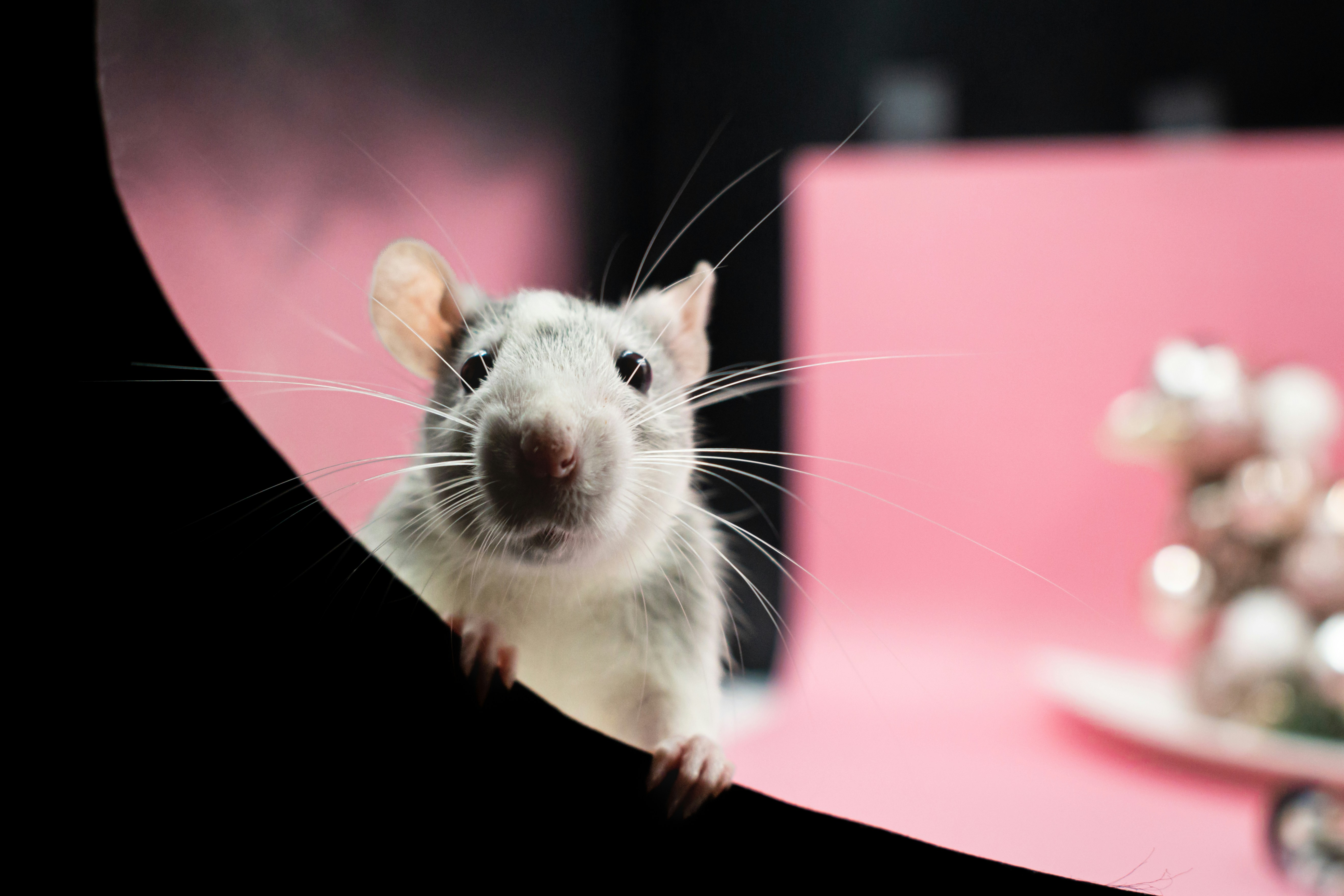2013年春,我搬進緊鄰校區後門,離文學院有點小遠的研究室。
研究室所在的老大樓,較高的多數樓層是才剛整新的學生宿舍,低樓層則是分配給文院系所當辦公室與師生研究室。有別於整新過的宿舍,作為文院系所的空間,設備基本上就比較有歷史。
例如室內的鐵製書櫃,大概是我讀中學時期,進出行政處室常看見的那種標配款。另外,空調也不是現在理所當然的分離式或變頻,而是懷舊的中央空調出風口,想吹冷氣,還得墊椅子上去扭開關。人家理科的教研館舍都是以棟來算,我們文科總是一棟裡的某一層,某一層的某幾間,而且總是撿人家搬走之後空出來的。
甚麼飄來飄去的都市傳說,我體質沒那麼特殊,看不見也別介意了。很感謝系上給博士候選人優先抽選後門的研究室,我在這裡讀書、工作、放空,生出一本不成熟的學位論文,也曾因為「那個人」的家暴威脅,暫時逃到這裡避風頭。總之,是個有很多回憶的地方,包括,這。裡。的。老。鼠。
當老鼠摸清我在研究室的作息,開始用肉眼可見的足跡,毫不掩飾的宣告,牠們這裡的遊憩與覓食權。每隔兩三天,桌上就會出現精美的腳印。書生原本不想與鼠爭個輸贏,進來研究室先用酒精擦拭桌椅,再讀書或工作;垃圾不在研究室過夜,尤其盛裝食物的免洗器皿或自己的環保碗筷,都是用餐過後立即丟棄,或馬上清洗,這些已成研究生活的日常程序。
只是,鼠群的跋扈超出我的預期。
踏著鐵馬,去前一個母校的城區部上日文課的某個傍晚,忘了帶走暫放在研究桌右側抽屜裡,同學捐贈的零食,悲劇就這樣發生了。一來抽屜沒甚麼值錢的物品,上鎖顯得有點多餘,二來我也不認為,老鼠有開抽屜的能耐。
原來我錯了,老鼠是會開抽屜的。
原來我錯了,老鼠是會開抽屜的。
原來我錯了,老鼠是會開抽屜的。
隔天踏進研究室,詭異的氣味撲鼻而來。並排整齊的書,有幾本倒了;擺放零食的中間抽屜,呈現半開的狀態。
「靠北喔!」
近距離直擊抽屜裡的悲劇,不自覺的罵出聲。零食被老鼠吃個精光,只剩外包裝不說,還屎尿橫流,一包才剛使用的抽取式衛生紙,則吸滿了老鼠製造的液體。

趕緊到一樓的便利店買了手套,捲起衣袖,來收拾老鼠開趴之後的殘局。卸下抽屜徹底清理,只要是老鼠可能爬過的平面,都用酒精噴好噴滿,擦拭乾淨,直到嗅覺不再聞得出鼠類排泄物的腥臭味為止。
「老鼠居然打開抽屜,吃掉你給我的零食耶!」
大清掃之後精神的耗損還未恢復,下午打開臉書訊息,跟同期玩伴傾訴我的崩潰。
「老鼠很聰明呢!其實文學院很多老師的研究室也出現過老鼠。」
「我知道,但沒聽說開趴開到屎尿亂噴這麼誇張,一家子就是把春風抽取式衛生紙當成廁所。」
「那你準備怎麼辦?跟系辦反映嗎?」
「嘿嘿嘿!系辦連自己的鼠患都很難處理了,不是嗎?」
自此之後,抽屜也不得不上鎖了。被惡鼠家族這麼一搞,完全不想再對這幫傢伙繼續溫良恭儉讓。我想到了有一種叫做「黏鼠板」的東西,準備來計畫一場反擊。
還沒用過黏鼠板呢!上網做了一點功課,有不同的廠牌、口味跟尺寸。最後決定買大尺寸,而且是花生糖口味的板子。不過,我幾乎天天會進研究室,還有個不常進來使用這個空間的室友,這個反擊的構想還需要一點天時跟人和。
室友是個大我一屆的學姐,剛好在抽屜悲劇事件發生之後來過一次,那天也聽我說了這件事。順著這個話題,聊到我接下來要執行的計畫。
「我六月初要去日本十天,想麻煩你那十天先不要過來,我準備…….」
拿出了購入不久,尚未開封的黏鼠板,努力用肢體語言,跟室友表達我的想法。據說,老鼠會聽見你想用甚麼東西對付牠們,所以關鍵字通通都要馬賽克。
「也太香了吧!」
出國前一天傍晚,我拆封了共計六片的黏鼠板,整個研究室滿溢著花生糖的氣味。小心翼翼的不讓自己被黏到,在板子的中間又撒上點心麵,分別將之鋪設在鐵櫃頂端和地板的邊緣。
「Have Fun!」
關上燈,關上門,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鼠板。
六月初的日本東北,仍在白晝舒適微汗,夜晚涼爽的氣候。返回台北之際,時序已進入六月中,蟬都掛在枝頭喊著靠北熱了。距離研究室大約10公尺的電梯一打開,就隱約飄散著一股怪味。
腳步越接近,答案就更呼之欲出,是我研究室飄出的氣味無誤。疫情之前,我就有騎車戴口罩遮擋髒空氣的習慣,隔著門板,口罩尚未取下,仍難抵擋屍臭味,可想而知房內的慘烈景象。
要是我再晚個幾天回來,左鄰右舍的研究生跟老師,大概以為又有博士生寫論文遇到瓶頸,覺得生無可戀。
倒數十秒,鼓起勇氣打開門,終於真相大白。
鐵櫃上的黏鼠板全數滑落,其中兩片各黏著一隻巴掌大的鼠屍,因為掙脫不了大尺寸的粘板,只能等死。不過,黏板邊緣的木框,被啃食得破碎不堪,推測是有別的同類,試圖想要搶救這兩個落難的傢伙,總之就是沒有救援成功,可能還吃到一嘴膠,那就祝福牠們無法張嘴進食吧!

這種兇案現場就不用麻煩沉睡小五郎模擬事發經過了,光腐屍氣味跟蒼蠅橫行的程度,可以確定陳屍一周以上無誤。或許在開啟鼠板的那天,牠們已經聞到花生糖的味道,當晚潛進來就被黏得一塌糊塗。
「噁心死了!下輩子選哈姆太郎他家投胎啦!」
戴上雙層手套,連板帶鼠投入垃圾袋,死到一個連湯汁都流出來的狀態,當然是先棄屍再說。
打開門窗,試圖散去屍臭的穢氣,也希望滿屋子飛的蒼蠅能識趣的離開,不過,眷戀的多,離去的少,只好捲起回收的廢紙,見一隻打一隻。人參真的好難!
這回我可是連地板都卯起來拖了三次,陳屍的周圍也狂噴酒精,更別說桌面還是鐵櫃,只要是身體可能觸碰到的地方都不放過。清理就緒,已經沒有太多力氣工作。
通常從日本走跳回來,補眠是第一要務,特別是我人到了名古屋,居然還發燒,大概是東北日夜溫差大著了涼,好險只是感冒,不是當時新聞一直放送的禽流感,退燒之後大致無礙,沒有因為過熱在國門被攔下。
回到台北,連眠都沒先補,就先跑來研究室收拾兇案現場。當下只想盡速清理完畢,沒那種閒情逸致拍照,打算留著以後噁心別人,所以,這是個沒圖沒真相的故事。
撲殺事件過後,惡鼠一族收斂了不少。我家近期也飽受非法居留的鼠類侵擾,連帶回憶起這段過往,與惡鼠再度交手的崩潰日後再說。
本篇最初發表於Mat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