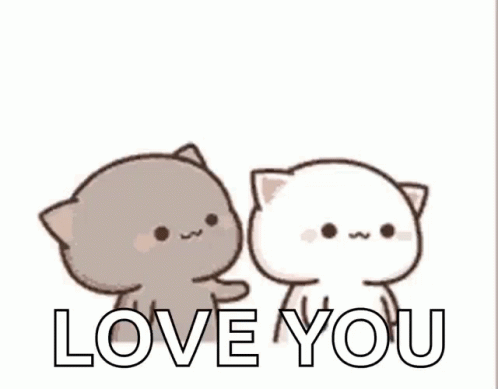仁傑在返回高雄火車站的交通車上,聽到了他錯過那一晚的談天內容,不過他心裡只想著,這次離開,大概很難再見到這個人了。接下來他會繼續讀大學或是做其他什麼,橫豎都離他很遠很遠。
窗外的風景不停變換,從幾近荒蕪的道路景觀,漸漸回到城市街路,他帶著滿懷的伴手禮,雖然還要在高雄朋友家待上一晚,心卻無比安靜。在小琉球的中心他喪失了病狂的自己,而那股失落感,要在很久很久以後才會湧上。
他在烏鬼洞風景區的涼亭,迎向狂亂的海風,唱宋冬野的《莉莉安》,
在離這很遠的地方 有一片海灘/孤獨的人他就在海上 撐著船帆
如果你看到他 回到海岸/就請你告訴他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
莉莉安
姚恩佐饒富興味地一同唱著,覺得他的歌聲,倒也沒有趙大強說的可怕。
然後無預警地,留仁傑說他想大叫,接著就馬上「呃啊——」一聲聲嘶力竭地叫了出來。姚恩佐嚇了一跳,但很冷靜地說「你這樣會嚇到下面的人吧。」指的是涼亭下面崖邊過路的人。可又有誰呢。
酒吧裡、民宿的夜晚,把酒言歡或是吃著章魚燒,靜謐的時光裡,生命的過客在持續增加,即使留仁傑深深記住了這些人,或是多少覺得彼此有些特別的印象,時間都會沖淡關係,距離也會使緣分崩離。
留仁傑站在公司大樓頂,和當初讓他借住高雄家的大學朋友聊天,說起小琉球的舊事,無奈地笑笑。
朋友告訴他,他那時候不知道哪來的瘋勁,半夜話說個不停,看他要睡了還不罷休,打電話給別人繼續聊,還隨便跟通話的對象告白。留仁傑都記得。但他也說不了什麼,現在他是不會再做那些了,反而有些寂寞。
大學第二年吧,留仁傑第一次出國,到一個西班牙語母語系國家教英文,也不知道哪來的勇氣,明明只會說些自我介紹和廁所在哪之類簡單的詞句,就不管不顧費了好一頓功夫,把自己送到國外虐。他告訴那時候的學生,他有一個暗戀的對象,好像是在講「crush」的時候,例子舉著舉著就說到身上來了。學生十分感興趣,還鼓勵他告白。然後一個班的學生告訴另一個班的學生,弄得他十分無語。回國後他確實告白了,但在一個非常詭異的時機用了對方不會喜歡的方式,而對方聽了也沒有特別說什麼,就是拒絕了吧。
雖然想著這些,仁傑其實卻是提起別的,他呵呵笑,說:「大便那件事你還記得嗎?」
朋友沒說話,看來是被突如其來的大便給震懾,留仁傑接著補充,就是在你家大便,我關在廁所裡邊哭這事唄。
「哦……,是有印象。」話筒傳來的聲音,幽幽的。
那時候我跟你說了什麼你還記得嗎?
「應該就是,關於你很想死之類的事吧。」
那你怎麼跟我說?
「大概回答你,我也曾經經歷過一樣的狀況,或是其實我還在那裡面,但是有個人把我拉著吧。」
哦,就是到現在還在一起的那位吧,跟你說「我不希望你死掉,所以會盡最大努力讓你想要活著,但如果你覺得死掉比較快樂,我會送你的」那位。
「虧你還背下來。」
因為是重要的人說的重要的話嘛……是說邊大便邊哭得不成人形一邊還要跟別人說自己的問題,你知道這有多困難嗎?超不舒暢。
「那種事我哪會知道,哈哈哈。」
希望你能繼續笑著生活。
「什麼?」
沒啦,只是想起了很久以前,我還在認真寫小說的時候。曾經把一篇半成品拿給一個教授看,結果他誤以為我寫的小標題是結局。「希望你能繼續笑著生活」。他後來在我畢業的時候,也拿這句話來祝福我。
「……彷彿咒語呢。」
是啊,也許在某一天,我能告訴那個自以為愛的人都離開的人,一切都只是彷彿吧。又或許,事實才是最虛幻的。
「你才虛幻吧。」
對啊,我最虛幻,你也不是第一個這麼說的人。說不定哪一天,我就會像泡泡一樣消失。
再見再見,在,也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