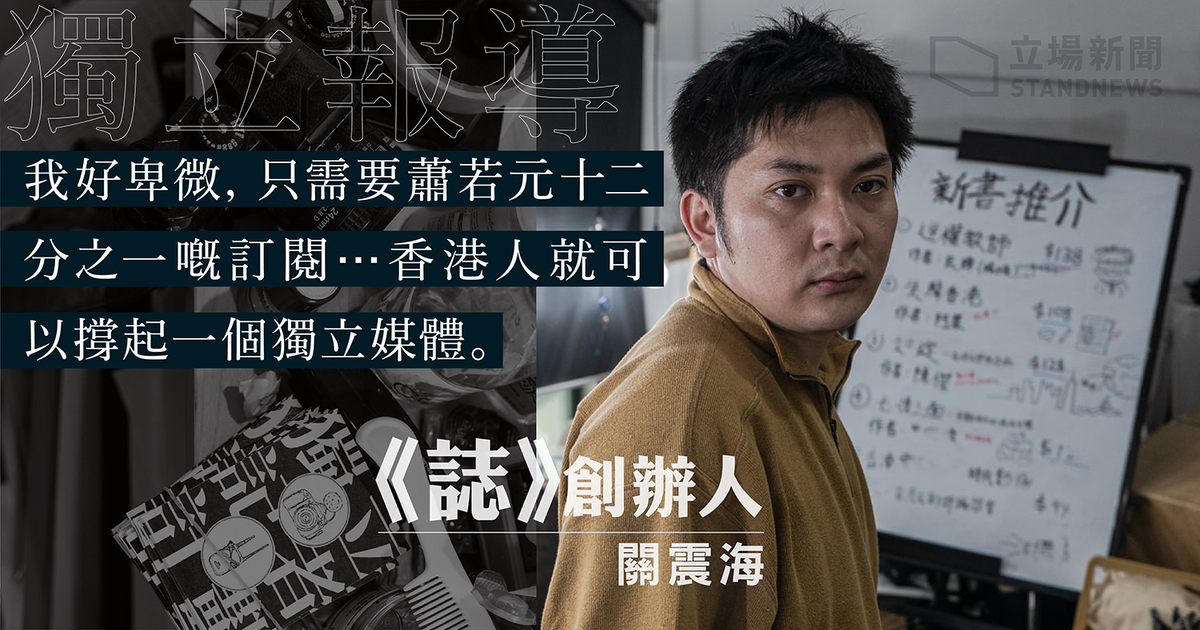作者/李庭芝

新聞是什麼樣子的?
想像中做新聞的樣子,也許是去採訪,去挖掘不為人知的事情。去問那些簡單的生活瑣事,溫情的故事,沒有意義的故事,想辦法把這些小得沒有傳播價值的事情,當成天大的事情記錄下來,試著找出主題,下一個充滿深度的結論,安慰自己再渺小的事、再渺小的人,都有被知道的價值。
沒有人會告訴你,一則新聞的產生,有可能不是走訪調查的結果,而是與某些人有了交情後,得到餵養產生的,尤其是那些牽涉到國家體制的訊息。至於新聞的中立性?在交情前面,還是先等等吧。互利共生的媒體與檢警
冤案救援的宣傳往往充滿困難,大眾沒有興趣知道關進去的那個人是不是真兇,而更樂於豪飲受害者家屬的淚水與哭喊。也許正是因為如此,新聞常常把兩者並陳,美其名曰平衡報導,但實際上卻多是挑起讀者的激情和憤怒。
不過讀者的注意力是決定新聞報導方式的唯一因素嗎?曾經製作過公視【紀錄觀點】節目和網路短片【我無罪,我是鄭性澤】的新台灣和平基金會執行長馮賢賢,在被問到為什麼冤案救援的宣傳總是充滿困難時,卻表示:「整個社會氛圍、大家的意識形態、長久固定的看法,其實是被政府、是被媒體所控制的。主流媒體中跑司法線的記者,都跟司法體制有著非常良好跟密切的關係,也因此他們很容易就變成是傳話或放話的工具,他們是認同體制的,到現在都是這樣。」
「我沒有辦法信任司法記者,為了要跑新聞,他們長久的習慣就是去跟體制同化,這樣子才能夠交到朋友、才能夠套到話,也因此他們常常就會變成放話的工具。尤其是檢察官體系,因為他們要讓他們的起訴被整個社會接受,鞏固他們自己正義的位置,媒體的配合是關鍵。」
曾經擔任過《自立早報》司法記者、拍攝過【島國殺人紀事】系列紀錄片的導演蔡崇隆,談起當年的經驗,則說:「我去當司法記者是因為我念法律系,然後他們就叫我先去跑司法(新聞),對我來講也是一個全新的經驗。那我會發現說,這些記者跟檢察官、法官的關係非常好,這是很明顯的,都是稱兄道弟這樣。」
「我其實印象比較深刻的是,一種很封建的氣氛在這一群人裡面。」
「以前記者就有點像串門子那樣,我在1992、1993年的時候。我們可能去到記者室,他們會放一些新聞稿,會有一些判決書、起訴書放在那邊,你可以在那邊翻,如果有什麼有趣的東西,有人就直接在那邊抄、直接寫。然後如果說有一些比較爭議性、比較大的案子出來,可能幾個媒體的記者就會講好說,欸我們可能幾點去找誰,我們這種小報就跟著去,如果覺得那個沒興趣就不跟。」
偵查不公開,只是原則
「那因為有時候還是有可能沒有新聞嘛!你光那個也沒什麼好抄的。然後就會有人變成是,個別去串門子,那完全就靠自己的人脈了,如果說關係好的話,你怎麼串都可以。」
「為什麼這樣串門子?你就可以理解有一種文化就是說,你還是可以講共生啦!就是,好來好去這樣子,基本上檢方、院方也會把我們記者當朋友,服務一些很特別的情况。也許有一、兩個記者,會寫一些比較自由派的或有點批判性的,但其實他們用字遣詞也很小心。」
蔡崇隆提到,現在如果想要重現【島國殺人紀事】當時的拍攝手法,已經不太可能了,因為這個紀錄片的出現,打破檢察官、法官與司法記者之間的良好關係,讓他們對攝影機更加謹慎。但是在當時,沒有人預料到會有記者洩漏出司法蠻橫的一面,主流媒體不可能這樣做。
也不意外當時的司法人員有恃無恐,當問到如果得罪司法人員會發生什麼事情時,蔡老師說:「你可以想像啊!是不會沒有工作,但是你就不會有獨家了,跑新聞獨家最重要了。」
但是這樣四處串門子,讓記者與自己泡茶聊天的行為,感覺違反了偵查不公開的原則。我問蔡崇隆,是以前對這個原則執行得比較不嚴格嗎?對此,蔡崇隆說:「我其實沒辦法去說是以前還是現在比較嚴格,但是我會有一個感覺是,其實常常都是記者在拿捏(偵查不公開的界線)。我們只講檢察官好了,基本上會有一些默契就是說,我告訴你這些東西,但是哪些可以寫、哪些不能寫,你要幫我拿捏那個東西。或者更敏感的,可能檢察官在聊的時候,就會說什麼東西不要寫出來。」
「這個有時候會講出來,有時候就是一種默契。那這個分寸拿捏好的話,你就可以確保跟那個檢察官的關係。他有東西,可能會私下跟你調,或者你來問他,他會跟你講。」
要是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的話,會有相關罰則嗎?蔡老師說:「就是一直沒有啊!因為如果有的話,當然就不可能會這樣。」不過他也說,真的要罰的話,認定的工作實務上也是相當困難,「因為一方面很難證實他的消息怎麼來的,你要處罰你也要有證據嘛!記者不可能洩漏說是哪個檢察官告訴我的,因為這個是新聞倫理嘛。記者如果不講的話,你要處罰誰?因為記者不能講嘛!除非他的關係完全不要了,而且人家覺得你這個記者信用破產,你違反了你的基本倫理嘛。所以你不會有人證說到底是哪個檢察官洩漏的,你處罰不到這個洩漏的人,那你要處罰記者嗎?記者可以說是新聞自由。」
跟體制站在一起
從蘇案到鄭案,整體的社會氛圍已經有了不少改變,但仍然有一些過往的痕跡殘餘,馮賢賢將司法記者慣常的工作方式,與台灣戒嚴時期的氛圍連結起來:「妳問說為什麼(蘇案)那個時候,要說服那麼困難?是因為剛剛解嚴,蘇案是發生在剛剛解嚴之後,那時候的警察氣焰還是非常的囂張,而檢察官等於是默許警察用刑求的方式逼共,做出一個大案來破案,大家都可以拿業績獎金,大家都可以升官,在這樣的一種氛圍之下,然後媒體又配合。」
「我記得蘇案,非常清楚,因為蘇案纏訟這麼多年,你可以去查,差不多前十年的,所有的媒體的報導,當年的大報,你去看那些司法記者怎麼報導。不管我們這邊怎麼樣拿出證據,怎麼說破嘴,怎麼樣說唯一的證據就是自白,然後自白是刑求逼供的結果,他們記者的筆鋒常帶感情,言下之意都還是懷疑他們,然後還是認定他們不應該這麼好狗運,可以被放走的。」
她認為雖然現在媒體的做法已經跟過去不同,畢竟在多次刑求逼供導致的冤案被揭發後,即便媒體、記者願意認同體制,也不得不更謹慎面對事證,但是這並不表示他們沒有跟體制站在一起,「你看像鄭性澤案的報導,譬如說,我記得台中高分院宣判那一天的新聞,有講到警政署請了兩個律師替受害者家屬辯護,然後說無不代表冤枉。」
「這一次難得法官跟檢察官有同樣的認定,而警政署站在對立面。這是什麼意思?你記者不可以各打五十大板,兩邊各報一下,然後新聞就結束了,你必須檢視這裡面的意義!是不是因為警政署長久的包庇警察用刑求的方式逼供、取得自白,然後造成這麼多,還有更多我們不知道的冤案以及已經執行的死刑冤案,記者都迴避這些問題啊!你認為他們程度真的這麼差嗎?」
「他可以把新聞報導就停留在兩邊各打五十大板,告訴你法官說了什麼、警政署的律師說了什麼,然後就結束了嗎?你告訴我,你的觀點是什麼、你怎麼看,因為你在最前線啊!我認為一個好的新聞報導,其實在這裡就有了新聞點,我們就應該檢視警政署的立場,因為那個讓人不寒而慄,那讓我推論說,你警政署到現在還沒有針對刑求做任何的檢討跟反省。我可以信任這樣的警政署跟這樣的警察系統嗎?」
戒嚴延長賽
馮賢賢接著說:「我一直說這是戒嚴延長賽,就是說,因為我們長期戒嚴,我們所有的公共機制都不正常。我們的法院不正常、我們的警察跟檢察體系也都不正常,他們都是統治者的鷹犬,媒體也是啊!你覺得全部都正常化了嗎?沒有啊!媒體也是他們政治控制的一環,他長久就是必須要認同體制,跟他們同化,才能夠攀交情、套訊息,然後檢察官透過他們的嘴裡放話,我今天放你獨家,明天放他獨家。當年就是報紙獨大的時候,他們用這種輪流放獨家的方式,去餵養所有媒體的記者,讓他輪流享受獨家,大家在自己報社裡都好混。」
就在將近三十年前,我們還是沒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國家。在當時所留下的行事習慣,至今仍殘留在各個領域中。就像平衡報導的指針,在碰到體制的時候,往往就巧妙地轉向了。至今我們仍未看到有人以檢視疑犯的力道,去檢視刑求、冤獄、濫訴等問題,也對偵查不公開等原則輕輕放過。我們國家的正常化,還有很長一段路得走。
原載於《人本教育札記》第 34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