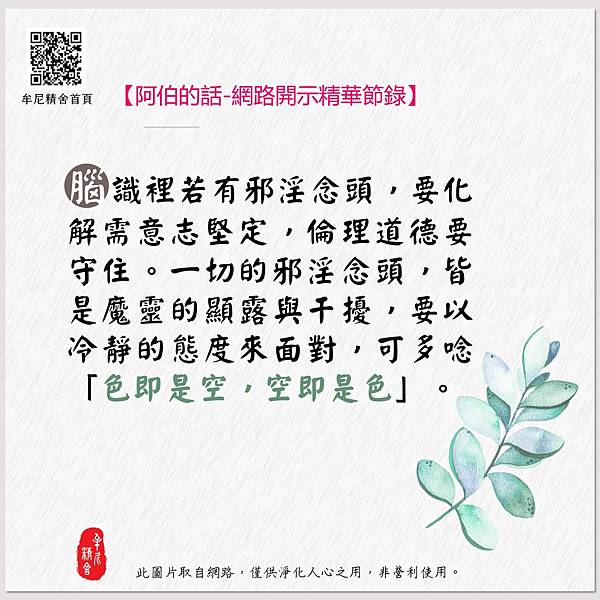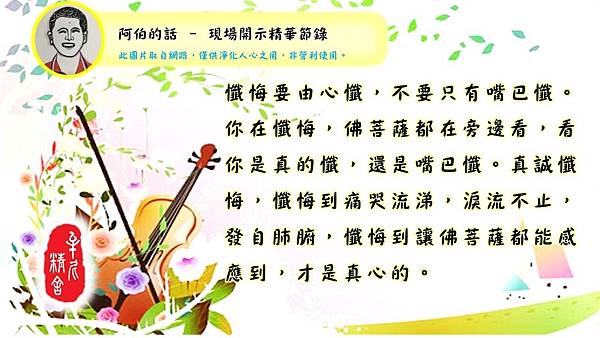大學畢業後,為了「弘法」,曾與友人辦了一個「中心」。
1985年左右,陳健民上師有緣到台灣演講,中心請他在僑光堂講了一輪「淨土五經會通」,結了善緣。陳上師後來發起印經、放生、超幽等活動,中心也參與協辦;陳師返美後,就由中心繼續接辦。
一、 放生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莊子
放生目前已引發許多討論,這是生態觀念的普及,也是對生命的尊重,不應再隨便放生;不過,在30幾年前,這樣的議題還沒有討論到如此普遍、如此深入。那時我們經常到不同的菜市場去「搜尋」,搶救許多魚蛙鱉鰻鳥蛇之類,載到山林野地、池塘湖泊放生。*
大概有人會好奇,「你們也放蛇?」其實只放過一次,還是專程跑到華西街的蛇店去搜刮的哪!一家一家買,買到老闆跟店裡夥伴大喊:「不要再拿出來賣了,我們還要做生意哪!」
放蛇是很難得而奇特的經驗。我一輩子沒有摸過蛇,碰都不敢碰,遑論將蛇放生。
記得是到木柵某處山上,大家先將一布袋一布袋的蛇放在地上,小心的將開口略略鬆開,然後就開始進行一些放生的「儀式」,包括告訴牠們生為畜牲的不幸,應該求生極樂世界,或下輩子可以投胎為人,好好修行,度化眾生…等等;再為牠們念三皈依,讓牠們與佛有緣;接著就開始念佛,念了一陣之後,在佛號聲中,將牠們一一放生。
說也奇怪,經過這樣一番儀式性的運作之後,「忽然」不再怕蛇了,且還多了些親近的感覺。
我們將袋口完全打開,那些大大小小的蛇慢慢鑽了出來,四散到附近的草叢裡。有些蛇反應較遲頓,出來後當場愣了半天,似乎還摸不清情況;更有許多蛇硬是躲在袋子裡,「說不出來就不出來」,我們只好動「手」,將手伸入袋中,碰到軟涼滑手的蛇身,不覺身體跟著一涼;但在眾人念佛聲中,恐懼之感已逐漸淡去。
輕輕地托著蛇身,牠不會反抗,反倒順著你,柔柔地依在你手中;靠近草堆時,只消將手靜靜擺著,蛇很自然地自你手中緩緩向前滑去,偶爾中途稍停,迴首四望,似不願離去,又似在聽佛號聲;隔了一會,才完全滑出,進入草叢。
這樣的感覺真好,人與動物,人與自然,這個時候彷彿合一了,人的世界、蛇的世界,野外的自然世界,都在靜靜的佛號與放生動作中,化為一個世界;感覺上,蛇已成為我們很親近的朋友了。
雖然放生留下許多爭議,但方法可以研究。人在放生的過程中,心思多少有所轉變,對生命、對自然、對自己,必然都有感受;尤其前一天才去華西街採購,親眼目睹現場宰殺,被活生生剝皮、取膽的慘狀,對照現在悠遊回到野地的生趣,實在是極大的反差。這是很好的生命教育課程。
二、 超幽
野草蒼蒼,白霧迷茫;
似有家人,在彼一方。
──改自「在水一方」

以前沒有聽說過超幽,佛經上倒有鼓勵人到「尸陀林」去修行的。「尸陀林」就是「墓仔埔」,也就是「夜總會」。常到這種地方,容易生起道心,較不會對世上的是非有太多掛懷。「好了歌」不就在說這樣的心境嗎!
陳上師為「超幽」擬出了一套儀式,希望度化「尸陀林」的「眾生」。
首先他會啟請三寶加持,為「尸陀林」眾位好兄弟、好姐妹懺悔、授皈依;然後念佛加持白米,一方面施食、一方面作為度亡的橋樑。參與超幽的同修就各拿了些米,四散到眾墳之間,沿路邊念佛邊向各墳撒米,達到普渡的目的。
有一次,我們到六張犁公墓去超幽。這時陳上師已經返回美國,我們用上師的錄音帶做例行的儀式。在儀式末段,上師為白米加持的時候,通常會高呼三聲「呸!」
我在聽到第一聲「呸」字時,頗覺震撼,我的下半身不見了。當然不是身體不見,而是對身體的感覺中,少掉了下半段。那個時期,我還算精進,偶爾在走路之間,感覺不到身體的「重量」,身體是很輕的;而在一「呸」之下,連這種輕的感覺也沒有了。*這才相信密法的厲害,一聲「呸」的確可能令人開悟;也可見修行人的物品還是很有些力量的,千萬不可小覷。
接著同修四散,念佛撒米。這處公墓佔地頗廣,雜草叢生,連小徑都給掩沒了。一夥人各走各的路,各做各的功課,走得不見人影,我也越走越深,逐漸看不到去路,也找不著來時路;涼風襲來,加重心中的寒意。
正「微微生起害怕」之際,忽聽得前面草叢中傳來呼喚我的聲音,且是叫我的小名,「阿霖!」頗似媽媽在喚我的聲音,既熟悉又親切。不自覺向草叢更深處走去,越走越遠,卻找不到任何人。天陰陰的,在廣大的天空下,我卻彷彿被一片野草吞沒了,略覺驚慌,倉皇中急急念佛,一邊忙著撥草尋路,手都被草刮傷了,褲管也帶上許多泥痕枯枝,一雙鞋更完全沾滿了泥巴。好不容易找到小徑,回到集合地點,只見同修陸續撒了米返來。
回程時,我猶頻頻回首張望。希望找到什麼呢?我也答不上來,但那是很奇怪的感覺,有個呼喚,留在遠遠的野草荒墳堆中,遙遙地仍在耳邊迴盪。依稀、彷彿,難以忘懷。
三、雲端上的老人
大一時,也有一次類似的經驗,當時住12宿舍,位在大操場邊(現已拆除,當地變成一座小巨蛋)。一晚睡下,夢見一座通往「上頭」的迴旋梯,雖僅約莫三層樓高,卻已沒入雲端,不見盡頭。有一老人背影,正不斷往上走去。老人身著白汗衫,望去頗似先父;我很自然地跟著上梯,不斷往上走,不知怎的老追不上;眼看老人已入白雲深處,我同樣有種迷路的感覺,正不知如何,上頭雲霧中,卻傳來老父熟悉的呼喚聲,一急之下,竟大哭起來。
「幹嘛!睡覺不睡覺,在哭什麼?」把室友全吵醒了。在男生宿舍哭醒,實在是有點……
後來聽到李恕權唱「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都有種特別的感覺。
在墓仔埔聽到有人喚我,大約是先母過世後不久;男生宿舍那一次,先父已去世4年了。誰在喚我?我是誰?
附記
*陳上師一再強調,買放生物類,不可到固定的市場、攤子去買,不可預訂,不可令店家有所預備;臨時去,看到什麼就買什麼,這才如法。
*後來想想,許是錄音機放在地上,所以,「呸」字出來時只「旁及」下半身;當時應該擺高一些,可能整個「我」都給「呸」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