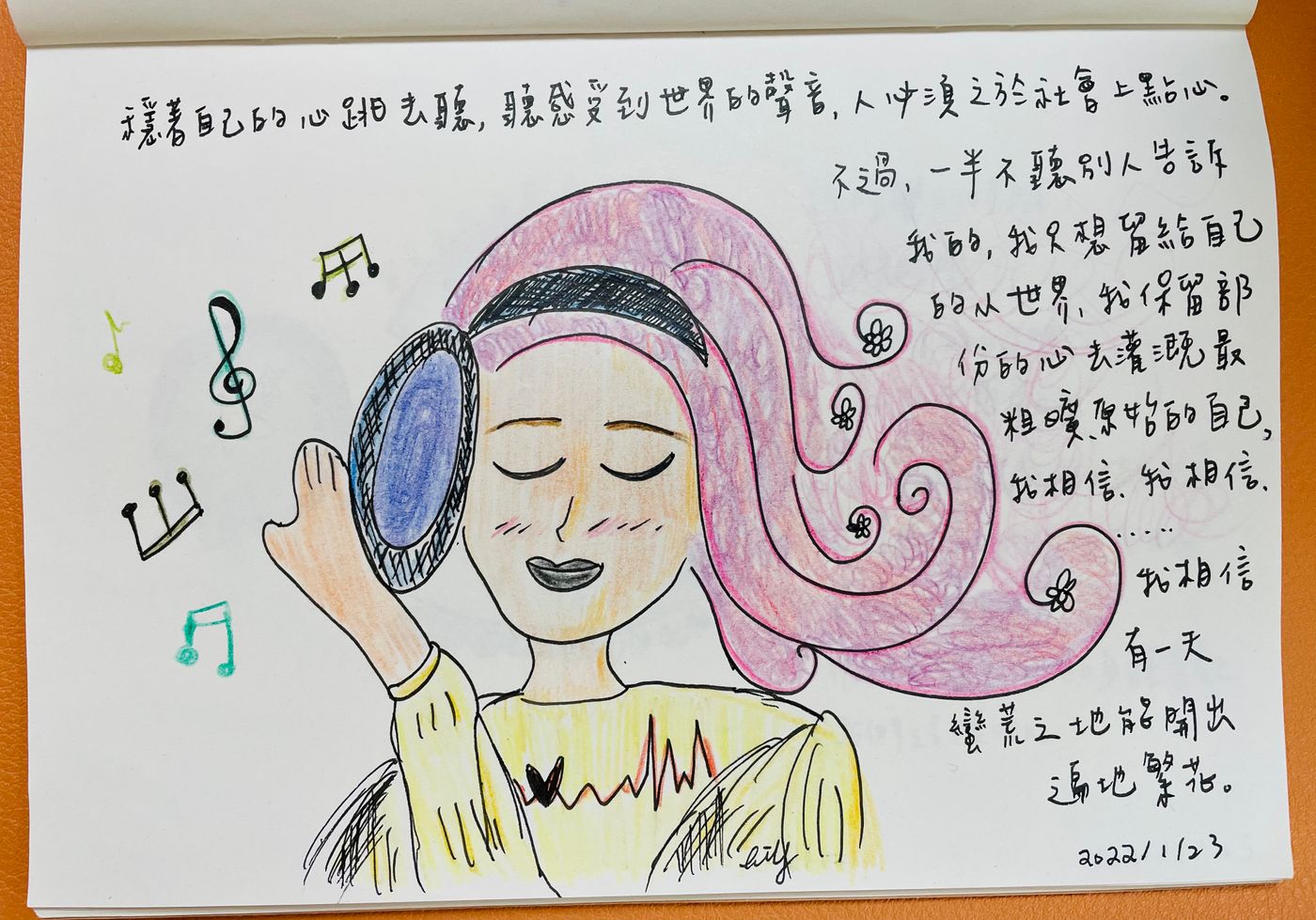雨一直下。清晨的草地上,骤然冒出一只蘑菇,圆滚滚的,一副膀大腰圆、吃饱喝足的样子。
朋友喜欢拍蘑菇和花草,奇形怪状,色彩缤纷,可爱且美。她还喜欢拍各种食物,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香味氤氲,充满烟火气息。一朵花、一棵草,一石食,一豆羹的快乐并非任何人都能轻易感知,比如我。
在很年轻的时候,工作的缘故,开始关注巨大而沉重,本无须关注的事件,思维习惯由此定型。心就总是沉甸甸的,不停地问,为什么,为什么?曾经感觉累了,试图让自己放松,不要看,不要听,不要想,但会持续地做很奇怪的梦:很暗、很冷,很多僵尸摇摇摆摆地蹒跚着,大脑腐烂了,空空的,手臂淌着腐化的黑色液体,要抓住每一个人,撕咬、吞噬,或变成他们。
事实证明,我做不了演员,轻松地岁月静好,已经绝无可能。
看看那朵生机勃勃的蘑菇,信马由缰,也想到我们的来处。
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人类的终极问题。基督教的神创论认为人类是由神照着自己的形像所造的。佛教的光音天降世说认为一切皆因缘起,人类及其他欲界有情众生,都是从光音天降生欲界的。科学家则普遍认为,人类及所有的动物都是进化而来的。
三者相比,在宗教的解释中,人都拥有高于其他生命的特殊地位,而科学家的理论则有低到尘埃里的谦卑。然而现实之中,有宗教约束的人群,对包括非我族类的世间万物,尚有一份敬畏之心,可以和谐共生。而纯粹的科学主义者或口头科学主义者组成的人群,则秉承丛林法则,对其他物种有着获胜者之于奴隶的优越感,或者不断侵蚀动物植物微生物的领地,直至赶尽杀绝,或者用钢筋水泥将自己包裹起来,与其他物种隔开。
以上理论孰是孰非,哪一种更有道理,早已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作为科学盲和仍未有信仰者,我不必证实或证伪,反而有了旁观者的释然。
就个人体验而言,我不喜欢密不透风的林立的高楼、摩肩擦踵的逼仄的街道,更希望看到绿色,看到蘑菇,希望看到即便人群嘈杂的街头,小鸟或小猫、小狗也能不惊不惧,悠闲地散步。我想,很多人与我有相似的感觉。那么,理论的证实或证伪已经不重要了。
据说,即便最贫瘠、最干涸、最寒冷的地方也有植物生长。只要有一粒种子,总会坚韧地生根发芽。据说种子还会蛰伏,可以长久地等待,一旦得到雨水,或者只是得到几滴露水,种子就会迅速复苏、萌芽。据说有些沙漠植物还懂得迁徙。极度干涸时,风滚草会将枝叶簇拥在一起,成为一个枯黄的轻飘飘的草球,被风或沙尘暴带向远方,寻找更适合生长的土地。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对人而言,种子就是信仰吧。毕竟除了一日三餐之外,大脑总还有些余量思考与食物无关的问题。如果信仰是一粒粒种子,大概也拥有蛰伏和迁徙的本领。
依旧愿意相信,即便一片荒芜死寂、万马齐喑之地,也并非只有僵尸。那些封印着生命的种子依旧存在,只是遇到了严酷的旱季,被迫暂时蛰伏。只要遇到一场雨或者一滴露水,种子就会悄悄萌发。也许轰的一声,就会染成一片绿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