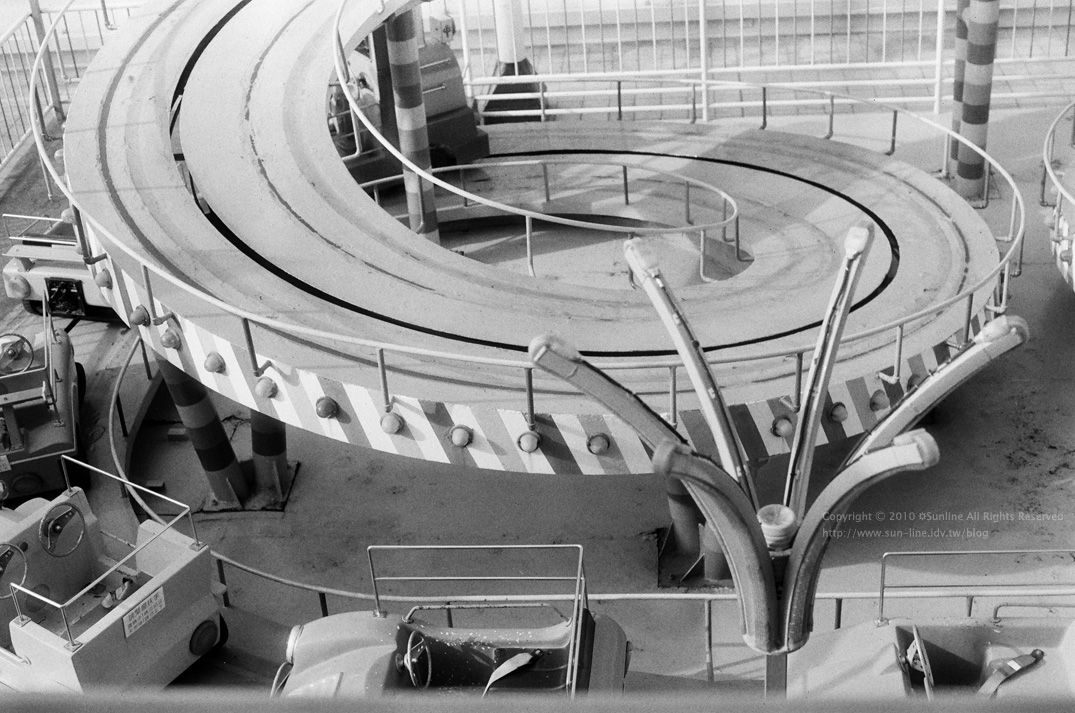過去曾在中和「將就居」上課,阿盛寫作私淑班。當年老師對寫作的諸多提點言猶在耳:「散文的『散』是自由。主張自由,也就強調生活經驗與真實情感的表達。」「放心下筆大是好,寫出真正的『我』」。其中「寫作是認真的遊戲」一句,不僅觸及寫作的態度,猶有一股在嚴肅專注中優游的餘裕,那暨是創作精神的內核(藝術追求往往帶有玩耍的性質),也是獨立自由的個體面對生命熱愛,那時刻投入、奉獻與享受的信念。

於是盛夏約訪阿盛老師這天,從他慈祥的說話,連結作品閱讀的感發,即使訪談過程,餐廳門外湧動著車流人潮鬧騰喧囂,這身在紅塵市井中滾熱的親切,一股活跳跳的生命力,竟也隱隱然與他描寫世俗人文的情調呼應,因此生出熟悉而且平實的喜悅。
鄉村與紅塵都可以是精神的桃花源
老師對所有文學的分類存疑,包含所謂「鄉土」文學的定義。區分文學類型,大概只是方便法門;界定、和框架都該屬於後來研究的範疇,而走在前方的創作,永遠無須被某些標準侷限。
閱讀阿盛散文,無論素材來自鄉野或都市,那些故土、人情在泛黃歲月,都已成為永恆的依戀。「定心回首時,才驚覺被時代的巨輪輾失的諸多人事物景將永遠不得再見。於是,提筆追想比對今昔,用文字記錄曾經與現在。」敘事緬懷,字裡行間汩汩流淌著對逝去的戀慕,戀慕中寄託著一個理想世界,藉細細描摹的文字呈現可想望卻再也無能觸及的精神的烏托邦。
童年阿盛聽家鄉耆老講古,是生活裡的遊戲日常。一則則鄉野傳奇,來自歲月的提煉,富含人情義理。說故事的老人幾乎都是清朝人,在〈黃昏的故鄉〉顯影:「年紀大了,諸事交給兒孫,樹下廟庭講古,童少青年圍著,熟眼的親和熱鬧緊密,自己小時就是這樣呀,自家父祖曾高玄想當然也是這樣呀;再且,自己還記得老老代講的故事,眾小輩肯定一樣會記得自己講的故事,想當然也會再講給更小輩聽。」
那些口耳相傳的故事串聯一代又一代生命,輾轉述說的語言經過漫長時間不斷錘鍊,老人雖不識字,但出言文雅,包含諺語、民謠、地方戲曲等各種素材,耳濡目染、生成化育,不但滋長了孩童的獵奇幻想,故事裡那些敦厚的情義、典雅的語彙,在在影響後來的少年阿盛,從高中階段遂逐步將成長中的見聞奇想發而為文。
個人陳述的記憶,往往能為一個時代造像。阿盛像是以文字不斷確認,心中永恆追念的他方淨土,藉此在漂泊無依的紅塵行路中慰藉生命的寂寥;也彷彿是以文字重新定義回不去的時空,逝去的化作春泥滋養守護,而今往後的旅程,便有了新生的價值。
走在〈夜燕相思燈〉的文字阡陌,有那麼一時半刻,錯覺阿盛似也化身傳講故事的長者。敘事者偶爾擔任旁白,運鏡、串場,引領讀者進入以文字織就的江湖市集;一忽而化身跑南北碼頭的打拳武師,對觀眾吆喝賣藥;一忽而是懵懂小童,不意窺見賣藝乞討人悲涼的生活。故事中的鄉情、人情凝聚純真年代對世界的全部認知,打開了一個人的心眼,刻劃青春生命的啟蒙、感動和思索,如斯種種驅動著文青阿盛將街頭里巷的成長記憶,以文字娓娓說給他的讀者聽。

老師常說,文學其實就是日常生活,不必刻意標舉崇高的意義。文學的藝術性在於文字描述,而非生活的內涵。作家致力以文字藝術將平凡的生活提煉,或聚焦人性困境,和超脫的奮鬥,或描摹家常人情,那些牆縫裡的求生掙扎。《詩經・國風》部分內容甚至粗鄙,但粗鄙也是生活的真實,現實生活本就不盡然高雅,一如月亮光華面和凹凸暗面各自依存,誠屬自然。
書寫鄉土不盡然只能是故鄉新營的還魂,阿盛的鄉土還表現在人與環境的深刻連結,包含對都市生活的觀察感悟。居處附近著意為燕子築巢的牙醫,見錢而殷勤問暖的銀行員,福和橋下賣老盆栽的獨身老人,都是阿盛深情凝視的人文風采。「鄉土」至此已不僅是一個地理的概念,猶可以涵納精神、與情感的空間。
「住中和已十六年,我還是有飄萍的感覺。然,萍聚也是有緣,我衷心惜緣。在這裡與許多讓我開顏或頭痛的十二生肖談文學,在這裡把一千二百四十八公克的早產女兒養到會用文言文跟我頂嘴,在這裡寫了七本書,在這裡結交無數好朋友……。」
〈萍聚瓦窯溝〉談中和將就居一帶或騎車或步行的世情洞察,文中暗暗鑲嵌陶淵明〈桃花源記〉若干警句。雖則老師常嗟嘆「種樹務必在土地上,而非根植於盆栽」的都市生活,然而不得已蝸居市井煙塵,在中和將就居談文說藝,與同樣飄零至此的四方朋友萍聚,隨遇而安、暫得寧謐的日子,或許也可以算是亂世裡難得的一方淨土,聊以自況。
無論是現實中無法抵達的舊時故鄉,或是塵世裡迅速變遷的複雜人情,都讓阿盛以簡淨、古雅的文字封存,一個精神的桃花源,待翻開書頁躍然於紙上。
是浪漫淘氣的藝術家,也是冷峻睿智的哲學家
從來沒有寫作計畫的阿盛,因為命定、由衷喜歡,年復一年筆耕不輟。〈文青都馬調〉談起從鳳凰花得來的精神感召:「究竟為什麼喜歡寫呢?實在說不出來。得閒就到新營神社坐在鳳凰樹下思考。鳳凰花開起來簡直是不要命,幾天內就豁出來幾千朵,每掉落幾十百朵就再幾十百朵補足,直到力氣燃燒殆盡為止。文青從中悟出,人生一世,就該這樣開花,才對得起老天賜予的稟賦。」
他相信俗諺「三歲定終生」,自覺是天生文青,從小對古老的、美的事物著迷,將就居中玉石古物累累陳列,都是長年的收藏。回首曲折過往,發現命運再怎麼崎嶇,仍走到寫作的路途。中學曾被安排去工廠勞作,但少年阿盛不願意,閱讀、寫作一直是心頭縈繞不去的念想。
自陳《綠袖紅塵》、《十殿閻君》,到《夜燕相思燈》、《海角相思雨》四本散文標誌著風格歷經的變革。《海角相思雨》呈現暮年心境,人生至此無罣礙。而《夜燕相思燈》文字運用刻意不著一字「我」,形式帶動內容產生變化,文意表達更顯精簡內斂,吐露後中年尤其深刻的曉悟。
即使老師認為語言文字有其侷限,包括遣詞造句之前,寫作者不免存在個人領會與思考的有限。再者,文字作為一種表達的媒介,並不足以完全形容內心的複雜多元。但是當面對限制,勇於創新的創作者亦有不願重複、尋求改變的嘗試,以遊戲的好奇心、認真的藝術追求,將文字揉捏、壓縮、延展,持續創造各種新的可能。
「漁村總是緊貼著天之涯,小,寂寥,草尖搖,風到處跑,沒見幾隻鳥,魚乾吊掛不少,門壁油漆起皺了,樹葉總有些黃褐焦,雞鴨遠近高低聲啼叫,入耳盡是洪洪洪的海潮,安安靜靜被遺忘在地之角。」這是〈海角相思雨〉中一段文字展演,完全實踐老師所謂「寫作是認真的遊戲」。
聽覺與視覺的文字交響,一個遺世獨立的小漁村在層次繁複的節奏感、畫面構圖中,鮮活明朗。從一句一字遞增為一句十一個字,兼具意義、趣味與藝術性,盡顯遊興與詩意。遊興是好奇、玩耍的遊戲精神,詩意是寫作的藝術呈現。88

老師戀慕大海,總愛去海邊。對海洋懷抱的執迷,有一種樸實、直見性情的浪漫:「美,可以美到令人想跳海,然而若強加文字去形容,還不如乾脆直接縱身跳入海。」也不僅只能是感性的抒發,面對大海,尚能冷眼思考,自粼粼波光中閃現哲思:「危機總是潛伏於平靜祥和底下,觀海者岸釣者都須牢記這句話。」「人該常去觀海或偶爾參與海釣,讓海的溫柔軟化那已被現實砥礪出來的硬心腸,讓海的暴虐作為借鑒映照那殘酷的過激言行,讓海的大度啟發那久受科技文明冰鎮的原生情懷,讓海風吹掉壞念頭,讓海水洗掉壞脾氣。」大海若強以為象徵,或許可以擬作阿盛精神的原鄉,一個抒情智性兼容、大度自由的理想世界。「歲月走過,在我自省的時候。我的個性兼有沉穩與浪漫,正如同我的作品。」
在許多作品中可見老師以戲謔、諷諭口吻陳述世情,風趣有之,辛辣有之。詩人向陽如是說「阿盛將諷諭轉為手段,藉以刻繪價值混淆的人世生活。」
例如〈急水溪事件〉一段:「小城居民縱使世面見得不廣,天性裡倒有某一點與大埠裡的飛車黨相近似,那就是即使眼見路上出車禍,頂多也是心跳三幾分鐘,減速十來公里,脈搏恢復正常躍動之後,該怎麼踩油門還是怎麼踩油門。」直指人性的自私善忘,無法避免一再重複的人間悲劇。他冷眼調侃,幽默中映現智慧,促使讀者於會心一笑中豁然感悟,洞見人性的缺陷。
應是極冷的眼,極熱的衷腸,以至於一針見血,要這樣苦口婆心。早已經練達人情,洞明世事,所以無須再論義道理,儘管真情流露,以本色做人做事做文章,有赤子好玩的淘氣,也有長者睿智的冷靜。阿盛作品中超越善惡評價的真,文字簡練的力與美,在實踐藝術性的同時,也以見識經歷淬煉出深刻思索,完成了作品,也完成了自己。

訪談中聽老師說話,遇餐廳大門開開闔闔,有時飄進垃圾車的音樂,頓時我像個無助少女暗暗祈禱誰來快快掩上那門扉,以免市聲街況嘈雜擾人;有時是路口工程正在施作的轟然巨響,夾帶車流背景音,乍聽見不免心生煩躁。起初我感到困擾,擔心噪音影響採訪的品質,後來又覺得是巧妙的安排,感到眼前情境不正恰恰呼應老師口中筆下的眾生相、浮世繪,那麼真實自然、直接應景,充滿盎然生機的人間。
訪談結束互道再見的時候,陣雨稍歇,老師一貫瀟灑的微笑、擺手,轉身走向將就居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