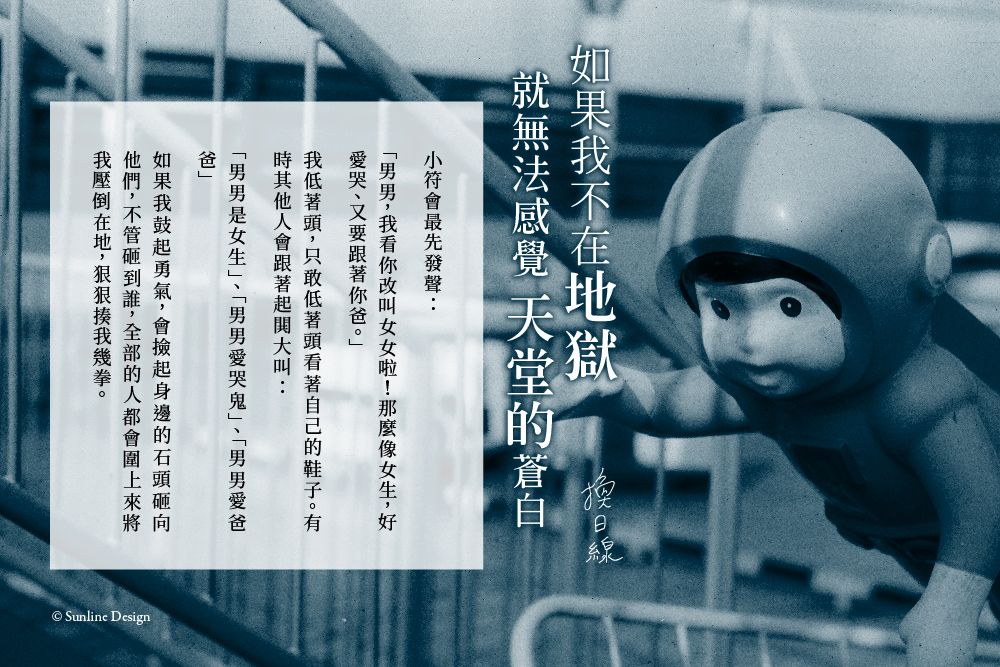應當還是二十七,或二十八,或更多
呢,勢必是更久的。
他一直不覺得那段分離的時間有這麼
長,也許數週,也許不過幾個月,所
以當他見到對方抱著一個襁褓嬰兒,
他莫名地有些怔了。
「哥,這我的。」
怎麼會?
他手裡本來拿著的行李一時間忍不住
鬆了手,不是說好要再一起走走看看
每個同袍的家鄉?
還說了,活著的要看,死去的也要看
……
對方沒察覺,逕自歡喜著:「你來得
正好,娃兒才剛落地幾天,哥,你學
問好,你幫她起個名字?是個女娃娃
,你瞧,跟她娘一個樣。」
他強撐住自己的表情,努力不讓自己
的笑看起來太慘:「怎麼沒聽你說過
?」
「一回到家家裡就開始操辦了,本來
就是個娃娃親,我之前都在戰場上,
能不能活下也說不準,都不知道對方
怎麼打算的,提什麼呢?
不過……」他看向了屋裡忙碌的影子
:「她倒是個心眼實的,一直等著我
。」
「哥,停戰了,我覺得挺好的,我想
就這樣,好好過日子。」
聽著這些話的時候,他感覺自己分成
了兩個人,一個笑著祝福恭喜,還為
孩子取了名字:「安平好嗎?平平安
安的,無恙無憂。」
而另一個他,只能隨著對方的話語,
被追打到牆邊的角落,只要他想伸出
手做些什麼,對方的聲音就像會像一
陣陣的雷擊,打在他手上,腿上,臉
上,打在任何可以被看見的地方,於
是他只能愈縮愈小,愈縮愈小。
他覺得自己縮到只剩下一顆心,可是
就連這顆心,也沒有人想要。
●●●
三十。
他並未再踏足對方的生活,只是安靜
地待在宅子裡。在他離家的那幾年,
母親終於死了,雖然是戰時不比往常
,但家裡還是盡可能妥善地安排了一
切,父親平常不住這兒,而是與姨太
太住在外頭的小公館,所以大部份的
僕人也都被遣散了,只留下最基本的
維護。
他找到父親時,父親說宅子本來就是
母親的嫁妝,是外祖父家傳下來的,
母親死的時候,只說宅子歸他,父親
點頭了。
他在父親的小公館裡坐了一會兒,父
親在這兒養了鳥,就掛在靠陽台的窗
邊,鳥兒吱吱喳喳的,就像屋裡頭轉
啊轉的阿姨,他懂了為什麼父親會選
擇她。
他跟父親聽了一輩子的醫生宣判,每
天都在為母親的剩餘時光算著日子,
就連他坐在母親床邊的時候,他也覺
得自己彷彿正守著一塊墓碑。
只要能讓他感覺到生命的流動,或許
他都會不顧尊嚴地跪倒在對方腳底,
請求汲取一些什麼吧,什麼都好,什
麼都行。
●●●
三十一。
對方來了,抱著孩子,說真是沒辦法
了,孩子病了,是大病,家裡沒這麼
多錢。
他什麼都沒問就塞了一筆錢進到對方
包裡,要他好好照顧孩子,錢是小事
,先把孩子的身體顧好,其他再說。
對方哭哭啼啼地走了,萬分感謝地,
說孩子好了以後再過來拜訪,他說,
他真是沒辦法了,只能找他。
看著對方離去的背影,他想著,光是
從他嘴裡聽到這句話,他就覺得值了
。
●●●
三十三。
對方陸續來過幾次,有時抱著孩子,
有時一個人來,大都是類似的理由,
錢還過一些,但總歸欠得更多,每次
他拿錢給對方的時候,對方都會說:
「哥,謝謝你了,我沒你真不行。」
他也探問過幾次孩子的身體還有家裡
人其他的狀況,說是親家母病重,老
婆回娘家照顧,偶爾才會回來看一下
。
他隱約知道有些不對勁,說到底,他
其實並不在乎那些錢,他在乎的是對
方眼底偶爾會出現的僥幸,可是他沒
有繼續問下去的勇氣。
他不知道他是怕什麼?
怕是戳破那張紙,對方就不再來?
還是怕戳破了,他一樣渴求見到他?
他察覺到自己是這樣的,愈是心心念
念一個人,就愈容易感覺到自己的下
賤。
●●●
三十五。
最後一次,當對方再帶著孩子來的時
候,他聽著對方對孩子的囑託:「叔
叔幫我們很多啊,你要很有禮貌。」
他看向那個孩子,多年前他為她取名
做安平,五、六歲的孩子已經懂事了
,她抬頭看向他,兩隻眼睛平靜無波
,就像多年前他遇見的那座深深池潭
。
「叔叔好。」
孩子的眼睛就像一面鏡子,如實地反
射出所有真相,他頓時感到無所適從
,說到底,他也分不清他究竟是在幫
,還是在買。
等孩子離開後,他告訴他以後不要來
了,欠的錢就當給孩子的禮物,以後
別來了。
對方沉默了一會兒,一度想說些什麼
,但最後只說了一句:「哥,我是真
謝謝你,可……也就到這裡了。」
他明白了,他,什.麼.都.知.道
。
一股憤怒莫名地升起,他已經覺得難
堪了,可是當一切攤開成如此,他只
覺得,這一切都太過下作,他與他,
太過下作。
--我以為只有我在買,殊不知,他
也在賣。
自己的夢,好像真的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