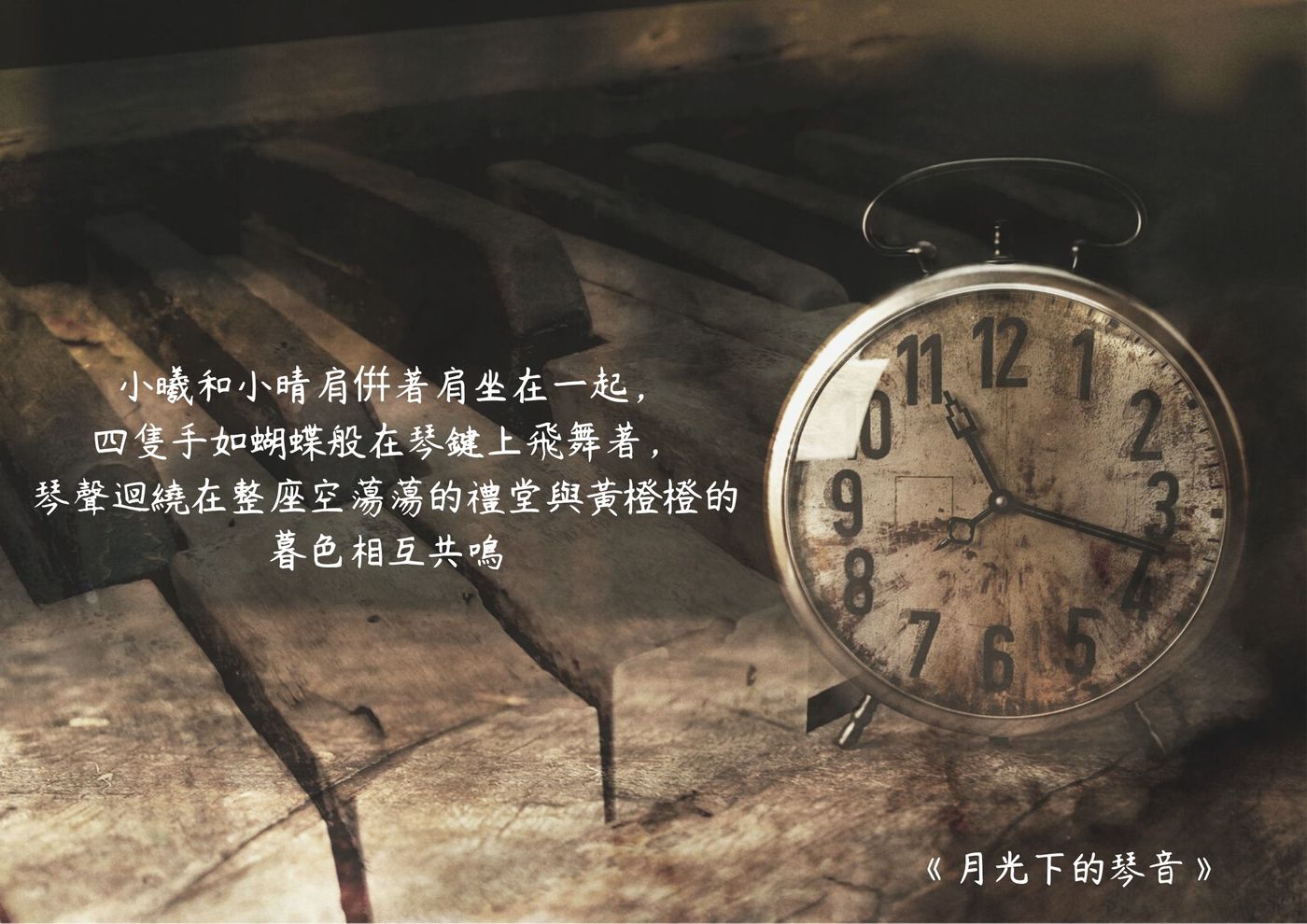社區中有個非正式的教會,禮拜天很多人參加禮拜。信仰,不是小孩關心的事,聽故事、做勞作、吃點心才是重點。我加入的是兒童主日學。背經卡、外國卡片、糖果餅乾,將我深深的吸住於彼。她是被另外的小朋友帶來到我們中間,懷著好奇,打量一切活動,並詫異我在其中。我們暗地較勁兒,看誰得的卡片多,別的小朋友拿了卡片就丟了,我們總是每星期都帶著過去的卡片,用橡皮筋箍著,比賽誰厚。她資質好,總勝我一籌,但感到我們之間並不是真的在競爭,而是更多的接近。或許是家中父母拜佛,不贊成她到教會,過了一年,她就不再出現了。
五年級時,有幾天沒見她來上課。聽同學輾轉傳述
「她有位哥哥,在報社當記者,因著挖掘一則社會新聞,觸怒了黑道,意外被殺!」那是一個治安良好,民風淳樸的時代,這樣的事可是不得了的。但在學校師生中也未掀起波瀾,小小社區也沒什麼動靜,可能是因發生在外地吧!我心中想:她會如何難過呢?!但我無法體會想像。之後她上學了,眼神之中,看不到過去發生了什麼事。小小年紀,就經歷了這種慘事,外表看似堅強,只不知心內壓抑多少悲傷恐懼,有無宣洩的地方,也無法了解;只是當時我和其他同學沒兩樣,不多打擾她就好了。
九年義務教育剛開始,考私立學校,仍是當時的主流。我進入所著名的「和尚」學校(全部是男生);她,則進入了尼姑學校,兩校距離不遠。相同的是:我們都是離鄉背井,住在學校,並且都是天主教辦的學校。在清晨,或在黃昏,我會走到學校牆邊的高處,在那兒可望見她們的學校部份建築。我那時的心思,就是:她在哪棟樓內?現在在做什麼?課業壓力,沒能讓我天天這麼浪漫,但到牆邊的次數,絕對需要高深的數學公式來算的。沒電話,沒手機,沒信鴿,盼的,是寒暑假快些來到,回鄉下社區就容易見著面了。
寒假過大年,小社區還有團拜的習俗,左鄰右舍到集會中心互道恭喜,或者三五成群到家中嗑牙,或者親朋好友至郊外走走。我到了她家附近轉轉,看看是不是有好機會;不料。真的看到她和父母正從外邊返家,她看到了我,只是輕輕點了個頭。是囉!大人在旁,當然不好就開口講話啦!一來她父母不認識我,二來女孩大了,言行可不能隨便。我頷首而過,想大概就是這樣見面了事,唉!豁地間,她回頭跑到我身邊,「下午三點到公園石亭子」她這麼沒頭沒腦說完就離開了。
在約定的時間,我帶著傻瓜相機,到了公園。天氣暖和著,藍天飄著雲絲,泛黃的草坪也露出些許的綠,似乎要開春了。她已立在亭子石階上,鵝黃的緊身毛衣,及到腳踝的白長裙,若不是留著學生頭,就看不出仍是少女。
「寒假作業多不多?」我笨拙地開口。
「還好,馬馬虎虎!」回答的也不經意。
有一搭沒一搭的聊著,想照張相了,就停一下,然後信歩繼續走。在一顆棗樹下,我覺得背景還不錯。
「在這裡照一張吧。」我說。
她坐下,身子靠著樹幹,把裙子理了理,
「可以嗎?」她問到。
「臉稍微背著光,對,這樣就好。頭也稍微仰起,看著天,對對對。欸,右手撐著地,左手放膝蓋上,好!」
從觀景器中,固定的框架裡,她就坐在那兒。柔和的陽光,灑在她清秀的臉龐。她是瓜子臉,不具深擴的線條,生來就是甜甜的。雙眼皮,接近傳統中國的鳳眼美,但不那麼細,應該說適中的弧度,呈現了溫柔親切。鼻子輕巧得像漫畫中可愛少女,俏皮地襯托其他,微測的角度看去,就像萬千表情的休止符。
「好了沒有?」她輕聲問著。
那雙唇充滿生氣的紅潤,似乎是用了淡色桃紅的口紅,卻是天然地勾勒著蛾眉月的嘴型,不輕薄,也不厚重,這時微笑著,安逸於等候中。
我不願立刻按下快門,真是少有機會如此靜靜的觀察她。向後稍微退了一下,好讓她全身入鏡。看著她勻稱的身材,心中絕無非分之想,反倒是,如果自己有一雙繪畫的手,我一定要像林布蘭一樣將她畫下來(林布蘭是經過好久才知道的)。感到的是:「她真是西施般的美啊!」(雖然我沒見過西施長相,但透過文字的想像,有了自己的定論)要是當時看過《魔戒》電影的話,我會像第三集後面,山姆提到夏爾的蘿拉「如果我要娶一位美嬌娘,那一定是她!」
「到底好了沒?人家都要笑僵了!」她有些怨。
「喀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