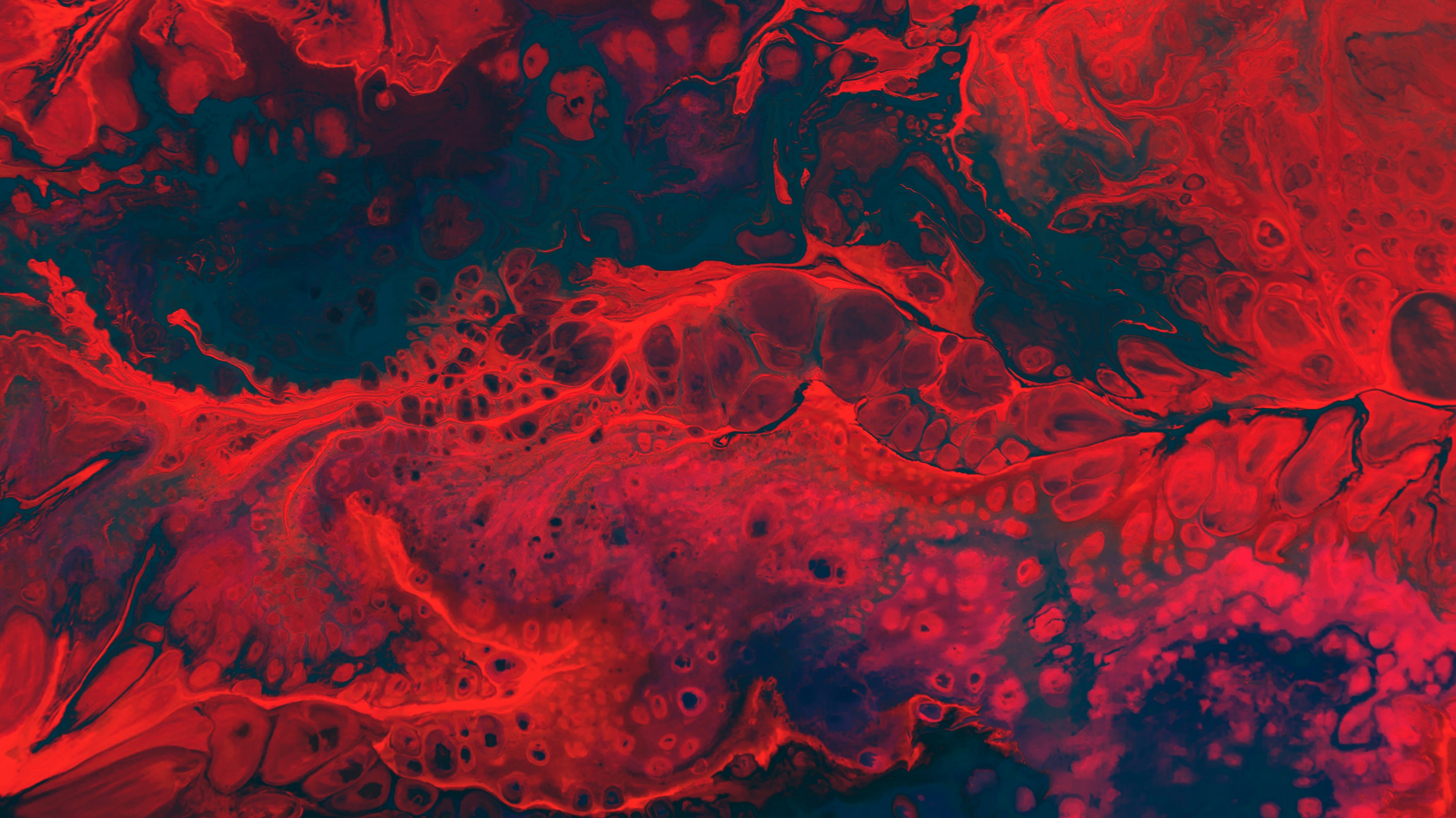「是看了太多書的緣故。」婦人說,話裡有敵意。
像是書本與文字就是他們最大的敵人。
「是看了太多書,你才會變成這樣。」「怎麼樣?」
「想太多,不快樂。」
「也有可能你是倒果為因了。」
短髮女子推了推眼鏡,操場上的照明強光打在鏡片上。
像個福爾摩斯。
「你以前很快樂的。」
「你說得是多久的以前?」短髮女子説。
聽起來很真誠,沒有挑戰的意思。
婦人想了想,「還在附小的時候。」
「那真的很小。」短髮女子說。
「你那時比較快樂。」
「誰不是這樣?」短髮女子詫異地說:「我那時甚至生理期都還沒來。」
「你又來了。」婦人說:「不是每件事情都跟生理期有關。」
「你生理期時不會不舒服嗎?」
「我們以前誰管我們。」
「所以你有沒有不舒服?」
「沒有。我身體很好。」
「不可能。」
「我的身體,你會比我還清楚?」
「你年輕的時候虛弱成那樣,一天到晚生病,生理期不可能沒感覺。」
「就是沒有感覺啊。」婦人奇怪道:「你這個人怎麼那麼奇怪。」
「隨便你。反正,我不會說我以前比較快樂。」短髮女子說。
「那是怎樣?」
「附小那時候,我是靠本能在過日子的。」
婦人的臉上出現茫然之色。
「本能有什麼不好?那時候你比較快樂。」
「因為那時候,我覺得只要讓你快樂就好。」
我聞到一股濃煙的氣味。
唉,就算屬實,這依舊是非常勝之不武的話。
以下只是我的個人觀點啦——
在整座山林焚燒起來的時候,精神分析的確可能用來滅火。
但如果不是森林大火等級的災難,精神分析本身就是帶著毀滅性的火源。
簡單講就是,大可不必如此。
但我在這裡,畢竟沒辦法阻止他說下去。
「你喜歡我考好成績、有好人緣、多才多藝。」
「所以我就,考好成績、有好人緣、多才多藝。」
哎呀哎呀,糟了。糟、糟、糟。
婦人覺得很糟。但他大概不會知道這具體而言有多糟。
說出這些話,說出來,這對女子而言是糟的。
「後來我發現自己根本不在乎這些。」
「很多事情,我好像根本一點都不在乎。」
此人麻煩,我聽到現在,常常分不清楚他到底講真的講假的。
一個這樣不日常的、像個謎語的人很難去要求別人怎樣的。
要怎樣?他自己都不知道啊!(氣)
有一種可能,短髮女子就只是一個很需要別人走到他面前。
然後明確地給他關愛。
要明確「關愛是給你喔」so special 這樣,
他才願意接受。一個小可憐蟲。
一個渴望神恩的小可憐蟲。
誰不偷偷都是,自我中心的小可憐蟲。
而這居然是最好的情況:
讓我們假設他講的話都只是情緒性發言。
有些東西不能去深究。
顯然,
那同樣可憐又無助的婦人也是這麼想。
「那我也沒辦法。」婦人說。
「我捫心自問,我跟你爸,我們兩個很努力了。」
「你看看周圍,有誰像我們做到這樣?」
「什麼意思?」
「給你那麼多空間跟自由!」婦人再次抬高音量。
「你就是太自由了,整天不知道在想什麼。」
看上去已經三十歲的短髮女子沉默很長一段時間。
就在我以為這即將變成反祖少女時代跟母親大吵一架時,
他聽起來非常好奇地問:
「先不講實際怎麼樣。你覺得,空間跟自由,是要我心懷感激來接受的東西嗎?」
不日常。
「你到底在說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