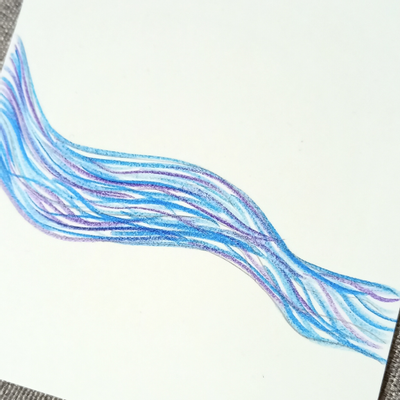整件事從一開始就不太對勁——可笑的是,他竟然直到她消失後才後知後覺!
出院前一天,她一如往常地陪他散步、削水果、收拾餐具、帶他復健、替他刮鬍梳髮,把他打理得整整齊齊、清爽利落,像一幅剛擦亮的畫。
他坐在床沿,目光追著她轉,看她微微俯身時衣領滑落一寸,露出一截白皙的頸線;看她指尖輕巧地剝開橘子瓣,再把果肉遞到他掌心時,指尖與他的不經意相觸——那一瞬,他幾乎忘了呼吸。
而興奮的腦子早已跑遠,一路飛奔到出院後的日日夜夜——那時,他們會比現在更熟絡。
他將為她用心營造一個尋常的約會——
捧一朵還沾著露水的白玫瑰,站在她大學門口,假裝只是路過;
沿著她常走的小徑漫無目的地閒晃,直到她踩著夕陽出現;
在她最愛的小餐館角落坐下,點一份她愛吃的梅乾菜扣肉,微笑看她吃得津津有味;
黃昏時,牽起她的手爬上城郊的山丘,並肩坐在那塊被風磨平的大石上,看落日熔金,把天邊染成一片橘紅。
若風恰好捲起一葉枯黃,輕飄飄落在她肩頭——
他會伸出手,極輕、極柔地拂去,然後趁她怔忡的剎那,低頭在她頸側印下一個短促而灼熱的吻。
再抬起眼,直視她驚愕的瞳孔,輕聲說:「我喜歡你。」
一次不行?那就十次。
一百次他也願意。
可現實永遠比幻想殘酷。
那天午後,她收拾完病房,站起身,像是要告別。
夕陽斜照,把她的眼鏡鍍上一層暖金。
她嘴角噙著一絲笑,眼底卻藏著他讀不懂的感傷。
「祝你早日康復,」她說,聲音輕得像一縷煙,「再見。」
他點了點頭,沒說「別走」,也沒問「會再見嗎?」
自那日起,她就像融入夢裡的幻影,無聲無息,無跡可尋。
沒想到她那聲「再見」,再見竟是七年。
冉炫出發瘋似地找她,但一無所獲。
他翻遍她提過的社福機構名單,卻查無此處——或許是她隨口胡謅,或許是他記錯。
他跑遍福市所有大學,站在大門口察看每一張路過的臉,妄想從中辨認出熟悉的輪廓;聯繫帳號早已註銷,頭像灰暗如死寂。
他一個學生,想憑運氣在茫茫人海中撈起一個刻意隱藏的人?
最後他只能苦笑:原來,她從來就沒打算讓他找到。
可她為什麼來?又為何走?
他們素昧平生,毫無交集。
除非——這一切背後,藏著他被蒙在鼓裡的某種聯繫。
但真相如何,他其實不在乎。
他是懊悔!
他懊悔的,是那天沒能多問一句話。
「你住哪?」
「我們還能見面嗎?」
「……我能不能,要你的電話?」
就因為太笨,太猶豫,只敢偷偷看她。
她不忙時,總靜靜望著窗外。
都怪自己!
就光顧著癡癡盯著她的側臉和鬢髮偷看——
看她耳邊那縷細軟微捲的鬢髮被風撩起,像蝴蝶振翅,細捲柔長,煞是迷人,迷得他一時忘了言語,連她髮梢被風掀起的弧度,都能讓他心跳漏半拍。
看她低頭讀那本索然無味的《道德箴言錄》時,睫毛在鏡片後輕輕顫動,擾得他心潮湧動;看她戴著口罩,露出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而他,腦子裡風暴肆虐。
在那之下,有著一張柔軟粉嫩的唇吧。
他想吻她。
不是禮貌的、溫柔的吻——
是毫無道德、不顧後果、只想把她壓進懷裡狠狠吞下的那種吻。
多年後他勸自己:那不過是年少時期的躁動,荷爾蒙作祟,一場虛妄的迷戀。
不該再留戀!
可七年過去,卻再也沒有一個人,能讓他起了佔有對方的衝動、能讓他心臟為之炸到轟天。
她成了他心底一個難以啟齒的秘密。
連提起她,胸口也會跳得跟戰鼓一樣,錘得他慌亂挫敗。
如果那天,他叫住她呢?
如果他攥住她的手腕,盯著她的眼睛,儘管突兀也要拋棄羞恥,啞聲問:「可以吻你嗎?」
哪怕被拒絕,也比現在——這無止境的臆想與遺憾,強上千倍萬倍。
他那時太年輕,以為青春長得望不到盡頭。
殊不知,有些機會,錯過一瞬,便是半生。
其實她第一眼並不驚豔。
粗框眼鏡、素色口罩,針織衫配長裙,帆布鞋洗得發白,馬尾隨意一綁,連髮圈都褪了色。
和那些穿短裙、化全妝的女大生比起來,她土得理直氣壯。
可她皮膚白得透光,笑起來眼睛彎成月牙,就這麼安安靜靜地坐在那兒,讓他像被雷劈中——心臟狂跳,手心冒汗,腦子一片空白。
這大概就是一見鍾情吧!
土歸土,在他眼裡卻亮如星辰。
回想起來,他簡直像個癡漢。
毫無道理地,瘋狂地,無法自拔地喜歡上一個連全臉都沒見過的女孩。
他分析不了這份感情。
他是試圖分析過自己這份莫名襲來的愛意,但分析不出個頭緒;分析不出頭緒就無法對症下藥;無法對症下藥就只能任憑愛意流竄、泛濫成災。
就像無法阻止春天開花、海水漲潮。
這份愛意如洪流,而他只能任其淹沒,溺斃其中。
住院時,每天醒來第一件事,就是等她推門而入。
她扶他坐進輪椅時,掌心托住他胳膊,溫熱透過衣料竄進骨髓,令他心神蕩漾;她推他散步時,後頸飄來淡淡的皂香,混著一點陽光曬過的暖意——足以讓他某個不可言說的部位瞬間「立正」。
但他咬牙忍住。
男人對真正喜歡的人,得有敬意。
發乎情,止乎禮。
生理反應他管不住,行為卻能守住底線。
頂多,夜深人靜時,在腦子裡把她吻個遍。
除了那縷鬢髮,他最愛她的眼睛。
鏡片後的瞳孔又黑又亮,像夜空墜入的流星;睫毛長而微翹,眨眼時彷彿在撩撥他的理智。
他總幻想:若她摘下眼鏡、拉下口罩,那張藏了兩個月的臉,會不會讓他當場失語?
可惜,他一直沒等到那天。
**
而現在——她就在眼前。
沒有眼鏡,沒有口罩,長髮披散在肩上,睡得安靜又深沉。
月光滲入,輕柔地覆在她臉上,睫毛依舊又彎又長,唇瓣柔軟如花瓣,微微張著,彷彿在等誰來吻。
冉炫出屏住呼吸,緩緩伸出手。
指尖在離她唇邊一毫米處懸停,猶豫、顫抖,最終還是——極輕地,點了一下。
像觸到高壓電,他猛地抽回手,整個人僵在原地。
心臟在胸腔裡擂鼓,咚、咚、咚——震得他耳膜發麻。
這感覺……騙不了人。
他一手按住胸口,喉結滾動,眼眶竟有些發熱:
『一樣……
和七年前,一模一樣!』
他忽然笑了,笑得眼尾微濕,嘴角卻揚得極高。
那笑裡有釋然,有狂喜,有柔情,有積壓七年的澎湃思念,轟然潰堤。
他關掉手機燈,螢幕暗下。
房間沉入柔柔的月色裡,像回到他們初識的那個病房。
他終於再見到她。
那個讓他心軟、讓他心繫、讓他七年不敢動情的可人兒——
此刻,就躺在他伸手可及的地方。
呼吸可聞,溫度可感。
而這一次,他絕不再放她走。
#小說 #原創小說 #輕小說 #都市言情
#第11件蕁麻衣 #鑲涵 #平行架空世界
〈小說〉第11件蕁麻衣
〈作者〉鑲涵
〈簡介〉發生在平行架空世界「稷下國」的故事。
精神科醫師葉凡樂、律師冉炫出、霸總范得義——
聯手「羞羞紅臉戲劇社」的荒誕、「趙錢孫李小分隊」的醋海、「常出汗自律兄弟會」的笑淚,在瘋狂世界裡,用溫柔守護平凡,以幽默化解傷痛。
就算人心深不可測,就算醫學測量不出動機與善惡。
他們還是選擇為心點燃溫熱的燭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