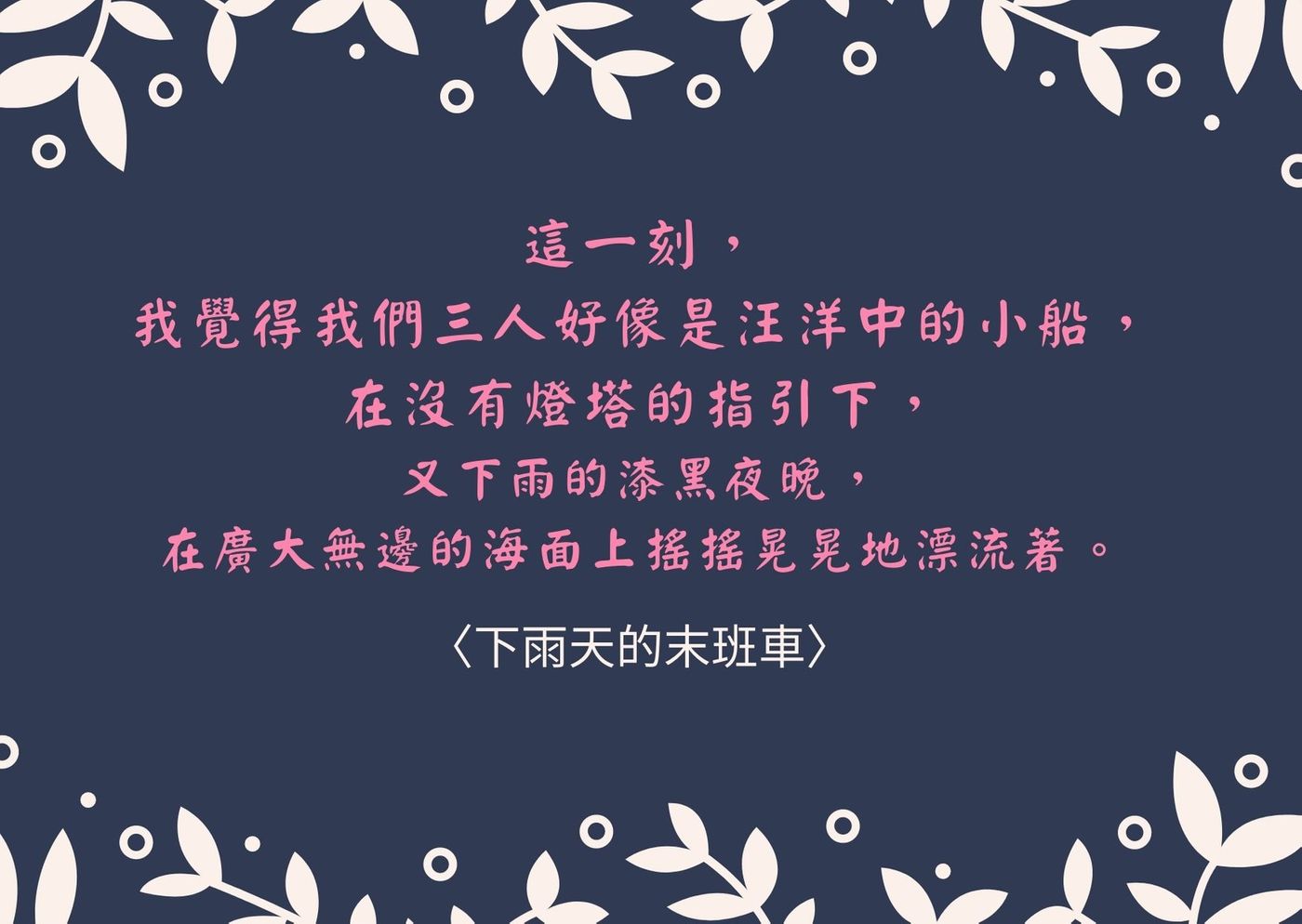在新北投地熱谷拍下照片時,我媽媽恰是二十歲。
照片中四人一字站立,大阿姨和外婆穿著同色異款的粉橘套裝,深色絲襪,白色粗跟露趾涼鞋,外婆帶著白珍珠色耳環,無多首飾;舅舅戴一隻錶,微微遮住鞋面的喇叭褲襯托出他的挺拔,小阿姨蹲立,和我媽媽著姊妹裝,一色及肩短髮,臉頰是未退去的稚嫩。
我的媽媽是相片中唯一沒有看向鏡頭的人,穿著八O年代俐落咖啡色長褲套裝,襯衫的領子外翻,紮的白色皮帶時髦地在腰上畫成一個結,媽媽的眼神高高地眺過相機,半笑著,好像遠方有熟識的人,她準備要打招呼的,二十歲的我媽媽,凍結在這樣的畫面之中。我必須如此細微的說明他們的服飾與姿態,因為那是唯一一張,我所看過的外婆的照片;也是唯一一張,媽媽在家裡擁有和外婆的合照。
地熱谷的旅行,是媽媽成年後,全家僅有的一次旅行。彼時舅舅從馬祖做三年兵退伍,小阿姨剛考上台北學校,四人自台東北上,齊聚在大阿姨與媽媽租賃的公寓,準備展開新的生活。十月底,小阿姨的新學期開始不久,外婆向工廠告假,偕外公一起到台北看兒女位於新北投的居所,是在探望之餘,全家穿上最好的衣服,到郊外踏青,留下地熱谷的照片。
所有人都走出了那張照片,每一天接續著每一天,接續著老去,也接續著命運。
時間若是數字,按指推算是容易的,所有的推移不過是兩位數之間的移動。二十歲的媽媽,半個月後喪母,八年後結婚,再過兩年,她的第一個孩子出世,再三年,誕下龍鳳胎我的弟弟妹妹。媽媽四十九歲時,我突然和她特別親密——四十九歲是外婆停止向前的年歲,我異樣小心謹慎,隱約知道死是不能重複的,但是恐懼卻是無常。
地熱谷假期將盡,外婆與外公準備返回台東,外婆堅持不讓子女們送行,媽媽和我形容那層公寓,是在馬路邊間四樓,底下就是公車牌。固執的外婆,拒絕他們到樓下站牌一起等車,她一邊拽著行李一邊哭著推擠,不要出來,不要相送,不要看著他們離去的背影。她和外公兩人並肩站在路旁等公車來,高高的外公貼著嬌小的外婆,我的媽媽和她的兄姊與妹妹,在四樓遙望揮手。外婆看向很遠的地方,從沒有仰頭回望,頭髮因而很柔順的,固定在回憶裡的鏡頭。
半個月後,進入冬夜的下班時刻,外婆在家裡巷口被高速飆行的摩托車撞倒。訊息傳到台北,夜間沒有火車,四人包車奔回台東,坐在後座的三姊妹與兄長,輪流說著母親的好,車程飛快卻追不上長夜之慢,他們時笑時哭,醒睡之間,日頭將亮,東台灣獨有清晨的曙光仍然來了,家到了,外婆早已離開。我不能想像在蜿蜒陡峭的山路上,途經宜蘭九彎十八拐,花蓮的海與山,穿過四人小時一起成長的長濱,他們還能經歷過什麼風景,所有嘔吐與暈眩,壓縮成遲緩的悲傷。
如果記憶只有畫面,這是我對於外婆最深的印記,公車站牌拒絕回望的外婆,成為了自己的鹽柱。
我成年後,媽媽一部分鬆解不再執意只做我的媽媽了,因而可以和我說出自己媽媽的故事。她曾在飯後只有我們兩人時,和我重現那天場景,最後一次看見自己的媽媽,她說,那天外婆哭得好傷心,哭得彷彿知道後來如我們所知道的結局。
我的媽媽總是說,如果我認識了外婆,一定會很幸福,外婆疼愛小孩出名,溫柔又能幹,外婆是職業婦女,在很大的鳳梨工廠上班,雖然沒有高學歷,卻一路做到工廠的核心;外婆整理家務,也養豬養兔子種菜,和外公合力拉拔四個小孩長大。說這些話時候的媽媽,好像也變成了一個小孩,眼神充滿我所沒有見過的愛,而那樣的愛總是伴隨著淚水。小時頑皮,我愛看媽媽哭,因為在認知裡頭,媽媽是大人,大人是不會哭的,可是只要我一講起外婆,哪怕只是僅僅「外婆」兩個字,無論是在看電視或做家務的媽媽,眼眶總會立刻漲滿淚水,好像一句魔咒,小孩子的我和大人的媽媽顛倒了,我掌控住弱點,變成一個更像大人的大人,呼喊外婆,讓媽媽進入了我所不能踏入的房間——我的媽媽有自己的媽媽,我的媽媽和她的媽媽,有著我所不知道的祕密。我殘酷地反覆刮搔媽媽的痛,想要得到一點親近,痛是溫暖的,而痛的本身,我也能夠感受得到。
彷彿透過媽媽講述自己的媽媽時,能讓我們能夠處在一間比較擁擠卻舒適,名為「外婆」的房間——那種說不得清楚的對於媽媽的愛,我和我媽媽一樣明白,一樣渴望。
地熱谷的照片,是我認識的媽媽與她的媽媽起點。它常年擺放在媽媽臥房的電視櫃上,與婚紗照相對,穿著白紗的媽媽,這次的眼神直直地定向鏡頭,穿越時光陰暗的井,沒有看著媽媽成家的外婆,必定也在鏡頭之外吧,看著她牽起另外一個人的手,婚紗照裡的媽媽是笑的,她將成為我的媽媽。
│原文刊登於《幼獅文藝》06月號/2017 第762期,Her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