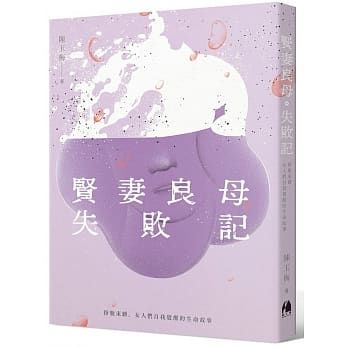過年前短暫的幾天裡,「徐州生八孩母親」的新聞在中國引起關注,倒是推特上的反應更應該稱得上是軒然大波了。首先,在中文社交媒體這位受害者長時間被稱為「徐州八孩母親」,雖然有懷疑受害者是一個從四川被拐來的女孩叫李瑩。這樣的稱謂實在令人心痛。如果她真的是李瑩,難以想像她父母、從前的朋友、同學認出她後如何自處,太痛了。她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失去了自由,失去了牙齒,成了性奴,侵害人還被各種當局和當局者保護著,不忍猝讀。其次,由她掀起的爭論到了國外媒體,視頻也得以傳播。可是,為什麼很多知識分子還在討論這件事究竟該屬於女權還是人權的範疇呢?看到視頻,我只覺得憤怒和悲傷,到了2022年,那片土地上依舊有著這樣的罪惡,系統性的罪惡,並且不能說、不能道,因為要歡歡喜喜過年。虎年,倒不如山中的老虎🐯一下衝出來,咬死該死的人。
這一悲慘的事件觸痛了好多人內心的好多地方。過年的「催婚」和「催生」算其一,女權一直為之抗爭的父權的壓迫算其二。於是,我放下手中這本《男言之癮》,我想起了一月間讀的兩本女權書籍。
之前提到尼日利亞籍女作家Chimamanda Ngozi Adichie是在文章《夾在溫哥華和香港之間的「家」》,但是更加令她出名的應該是經常在火車站書店看到的那本小冊子——《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s》(我們都應該成為女權)。自然,這是一本關於女權的書,不過我更喜歡她的另一本關於女權的書——《Dear Ijeawele, or a Feminist Manifesto in Fifteen Suggestions 》,將會在稍後的「虎讀不食子」裡介紹。這兩本書分析了女權,也談到了父權社會的系統性問題。《我們都應該成為女權》裡比較喜歡的兩個觀點:
一、語言的角色
“The language of marriage is often a language of ownership, not a language of partnership.”「嫁」和「娶」這兩個字就是如此。娶字聽起來就感覺是fetch一樣,是根植於語言中的ownership感,倒不如marry。沒錯,如何措辭也是很重要的。因為語言在後天習得時變得越來越自然,很多時候我們不去想這個語言背後給人產生的感覺。比如,媽媽對女兒在「催生」的時候會這樣說,「我還等著妳給我生一個大外孫呢!」或者「變相催婚」時說:「我倒要看看妳能不能給我找一個這麼帥的女婿回來!」這裡的「給」實際上最令人不舒服。我知道很多父母都這樣說話,而我們聽多了也「習慣成自然」,其實不然,「給」字直接剝離了女兒作為一個(女)人的感覺,女兒所做的事情,諸如「生孩子」或者「結婚」都統統變成了「給她生外孫」和「給她找女婿」,還有一種說法是「某某女性給某某男性生了一個兒子」(好像兒子不是這個女人的呢?),女性有直接被工具化或者忽視其個人性的感覺。說「我倒是期待妳將來的孩子啊,那就是我的外孫」諸如此類可能更好些。徐州性奴案中同樣,她所受的遭遇、非人的虐待一再不提,轉而關注「她是八個孩子的母親」,而強姦、囚禁犯則是「八個孩子的父親」,其twist程度已經難以形容了。
二、女權與人權之爭
“Feminism is, of course, part of human rights in general—but to choose to use the vague expression human rights is to deny the specific and particular problem of gender. It would be a way of pretending that it was not women who have, for centuries, been excluded."這一爭執類似面對Black Live Matters反而說All Life Matters的情況。任何一個國家的女人都無法否認在幾千年的人類歷史下,女性所受到的壓迫,而這也是人權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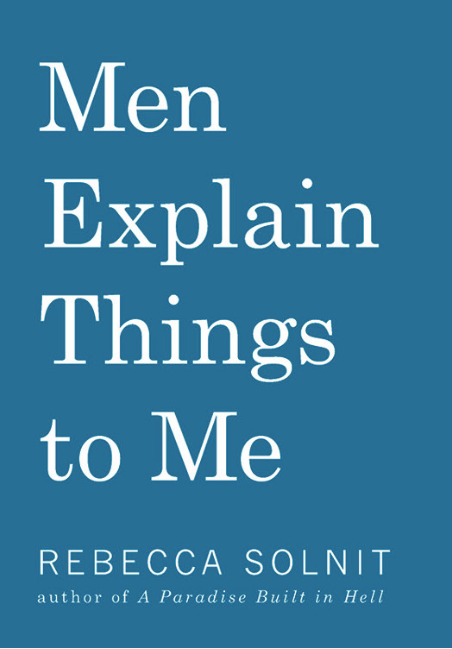
而《男言之癮》🤣這本書叫做《Men Explain Things to Me》,讀了讓人非常鬱悶的一本書。從第一章「The Longest War」開始就講到古今中外各種對於女性的壓迫和凌虐、強姦。在作者列舉出的那個數量下思索女性千百年來面對的暴力是具有挑戰性的,更重要的是,這不是哪個制度或者時代獨有的,而是一直都是這樣。讀著就一股淒涼感、無力感。
當第二章提到婚姻平權的時候,作者談到了她認為的婚姻平權的阻力。很多保守派其實更贊同的是婚姻中不平等的男女雙方關係,而同性婚姻將以「partner」的方式打破男女千百年來維持的這一「平衡」,這在很多既得利益人眼中是不可容忍的改變,也因此,很多人一定要給同性戀人之間冠上「誰扮演男人誰扮演女人」角色的設定,彷彿這樣才能理解。
我並不是特別喜歡這本書給人的感覺,或許是我自己的不是,讀到這樣多針對女性的壓迫、暴力心裡還是難以承受,忽然覺得自己好幸運但是又覺得這樣的感覺本來就是問題所在,所以無所適從。直到作者談到了伍爾芙和蘇珊•桑塔格才緩和了些許。伍爾夫在她作品中的思考令女性為之振奮,在《殺死房中的天使》裡她最後寫道桌邊的一個年輕女性和一瓶墨水,當這位年輕女性摒棄了強加在自己身上的所有謊言、虛偽之後,她就可以跟自己完全接觸了。可是,終究「她自己」是什麼?「女人」又是什麼呢?我不知道,你肯定也不知道⋯⋯這或許就是女性的困境吧,從那些強加的符號、角色、身份、功能中抽離出來以後,剩下什麼呢?有誰知道?
因為一直以來的捐助收到這樣一封信,標題是「女人的武器」——那個小女孩手裡真握著一隻鉛筆。是象徵吧,象徵著能寫的手、能說的嘴,握著的拳頭是自由與empowering!可是,真的是這樣的嗎?其實還有太長的一段路要走。她們需要我們的支持,同時,也需要我們的筆觸及那個黑暗、漫長、所謂「傳統」而看似不可挑戰的領域。
最後,摘這段話是為記。
“Feminism is an endeavor to change something very old, widespread, and deeply rooted in many, perhaps most, cultures around the world, innumerable institutions, and most households on Earth—and in our minds, where it all begins and ends.”女權主義是改變一直非常陳舊、普遍且在許多或是世界上大部分文化、數不清的機構和地球上多數家庭中根深蒂固的觀念的努力。這觀念起於我們的腦海,也將終於此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