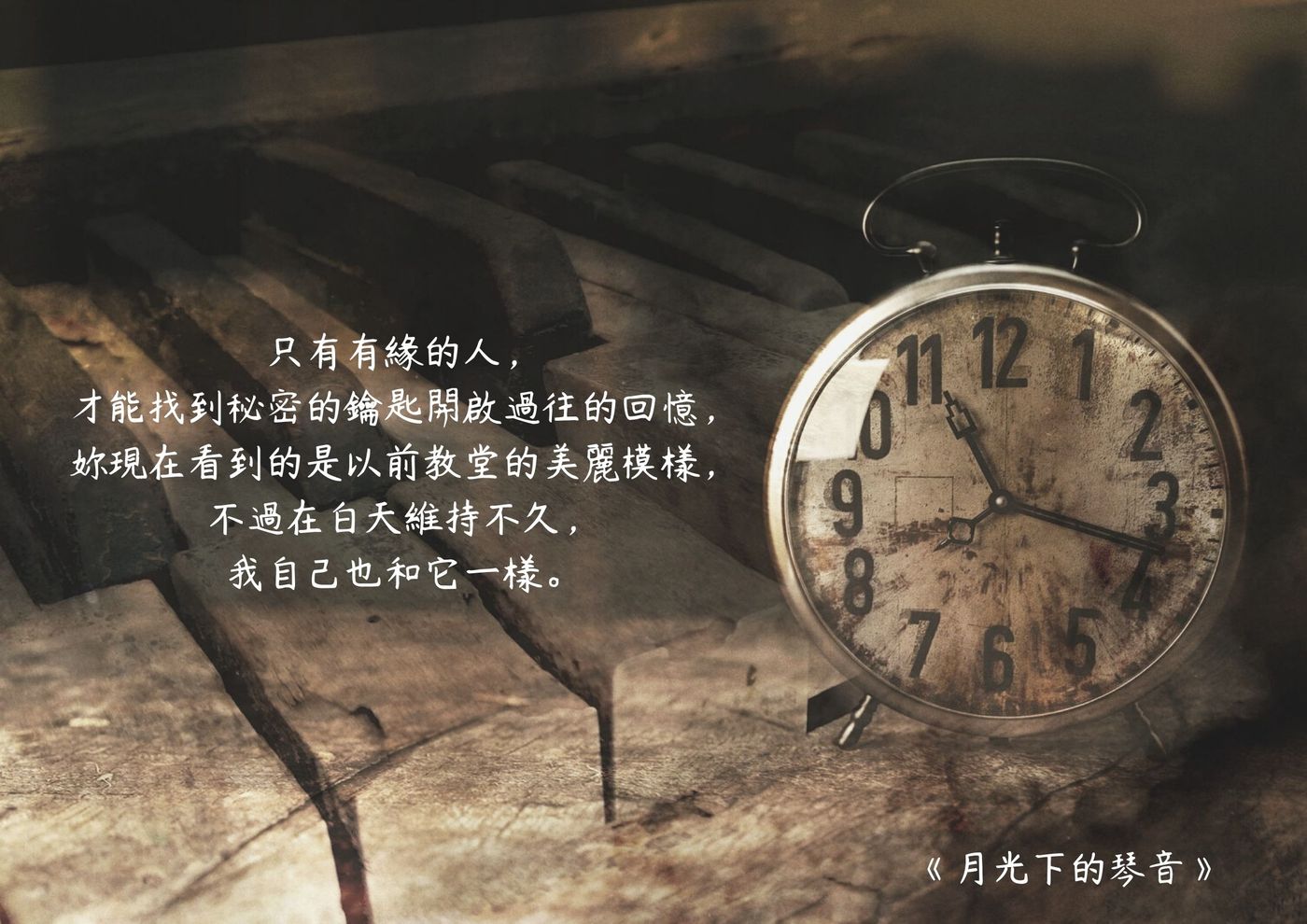《消逝的鐘聲》-史鐵生
在台階上張望那條小街的時候,我大約兩歲多。
我記事早。我記事早的一個標記,是史達林的死。有一天父親把一個黑色鏡框掛在牆上,奶奶抱著我走近看,說:史達林死了。鏡框中是一個陌生的老頭兒,突出的特點是鬍子都集中在上唇。在奶奶的涿州口音中,“斯”讀三聲。我心想,既如此還有什麼好說,這個“大林”當然是死的呀?我不斷重複奶奶的話,把“斯”讀成三聲,覺得有趣,覺得別人竟然都沒有發現這一點可真是奇怪。多年以後我才知道,那是1953年,那年我兩歲。
終於有一天奶奶領我走下台階,走向小街的東端。我一直猜想那兒就是地的盡頭,世界將在那兒陷落、消失--因為太陽從那兒爬上來的時候,它的背後好象什麼也沒有。誰料,那兒更像是一個喧鬧的世界的開端。那兒交叉著另一條小街,那街上有酒館,有雜貨鋪,有油坊、糧店和小吃攤;因為有小吃攤,那兒成為我多年之中最嚮往的去處。那兒還有從城外走來的駱駝隊。「什麼呀,奶奶?」「啊,駱駝。」「幹嘛呢,它們?」「馱煤。」「馱到哪兒去呀?」「馱進城裡。」駝鈴一路叮玲鐺琅叮玲鐺琅地響,駱駝的大腳趟起塵土,昂首挺胸目空一切,七八頭駱駝不緊不慢招搖過市,行人和車馬都給它讓路。我望著駱駝來的方向問:「那兒是哪兒?」奶奶說:「再往北就出城啦。」「出城了是哪兒呀?」「是城外。」「城外什麼樣兒?」「行了,別問啦!」我很想去看看城外,可奶奶領我朝另一個方向走。我說「不,我想去城外」,我說「奶奶我想去城外看看」,我不走了,蹲在地上不起來。奶奶拉起我往前走,我就哭。「帶你去個更好玩兒的地方不好嗎?那兒有好些小朋友……」我不聽,一路哭。越走越有些荒疏了,房屋零亂,住戶也漸漸稀少。沿一道灰色的磚牆走了好一會兒,進了一個大門。啊,大門裡豁然開朗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大片大片寂靜的樹林,碎石小路蜿蜒其間。滿地的敗葉在風中滾動,踩上去吱吱作響。麻雀和灰喜鵲在林中草地上蹦蹦跳跳,坦然覓食。我止住哭聲。我平生第一次看見了教堂,細密如煙的樹枝後面,夕陽正染紅了它的尖頂。
我跟著奶奶進了一座拱門,穿過長廊,走進一間寬大的房子。那兒有很多孩子,他們坐在高大的桌子後面只能露出臉。他們在唱歌。一個穿長袍的大鬍子老頭兒彈響風琴,琴聲飄蕩,滿屋子裡的陽光好象也隨之飛揚起來。奶奶拉著我退出去,退到門口。唱歌的孩子裡面有我的堂兄,他看見了我們但不走過來,惟努力地唱歌。那樣的琴聲和歌聲我從未聽過,寧靜又歡欣,一排排古舊的桌椅、沉暗的牆壁、高闊的屋頂也似都活潑起來,與窗外的晴空和樹林連成一氣。那一刻的感受我終生難忘,仿佛有一股溫柔又強勁的風吹透了我的身體,一下子鑽進我的心中。後來奶奶常對別人說:“琴聲一響,這孩子就傻了似地不哭也不鬧了。”我多么羨慕我的堂兄,羨慕所有那些孩子,羨慕那一刻的光線與聲音,有形與無形。我呆呆地站著,徒然地睜大眼睛,其實不能聽也不能看了,有個懵懂的東西第一次被驚動了——那也許就是靈魂吧。後來的事都記不大清了,好象那個大鬍子的老頭兒走過來摸了摸我的頭,然後光線就暗下去,屋子裡的孩子都沒有了,再後來我和奶奶又走在那片樹林裡了,還有我的堂兄。堂兄把一個紙袋撕開,掏出一個彩蛋和幾顆糖果,說是幼稚園給的聖誕禮物。
這時候,晚祈的鐘聲敲響了——唔,就是這聲音,就是他!這就是我曾聽到過的那種縹縹緲緲響在天空里的聲音啊!
「它在哪兒呀,奶奶?」
「什麼,你說什麼?」
「這聲音啊,奶奶,這聲音我聽見過。」
「鐘聲嗎?啊,就在那鐘樓的尖頂下面。」
這時我才知道,我一來到世上就聽到的那種聲音就是這教堂的鐘聲,就是從那尖頂下發出的。暮色濃重了,鐘樓的尖頂上已經沒有了陽光。風過樹林,帶走了麻雀和灰喜鵲的歡叫。鐘聲沉穩、悠揚、飄飄蕩蕩,連線起晚霞與初月,擴展到天的深處或地的盡頭……不知奶奶那天為什麼要帶我到那兒去,以及後來為什麼再也沒去過。
不知何時,天空中的鐘聲已經停止,並且在這塊土地上長久地消逝了。
多年以後我才知道,那教堂和幼稚園在我們去過之後不久便都拆除。我想,奶奶當年帶我到那兒去,必是想在那幼稚園也給我報個名,但未如願。
再次聽見那樣的鐘聲是在40年以後了。那年,我和妻子坐了八九個小時飛機,到了地球另一面,到了一座美麗的城市,一走進那座城市我就聽見了他。在清潔的空氣里,在透澈的陽光中和涌動的海浪上面,在安靜的小街,在那座城市的所有地方,隨時都聽見他在自由地飄蕩。我和妻子在那鐘聲中慢慢地走,認真地聽他,我好象一下子回到了童年,整個世界都好象回到了童年。對於故鄉,我忽然有了新的理解:人的故鄉,並不止於一塊特定的土地,而是一種遼闊無比的心情,不受空間和時間的限制;這心情一經喚起,就是你已經回到了故鄉。
這裡總有一篇屬於你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