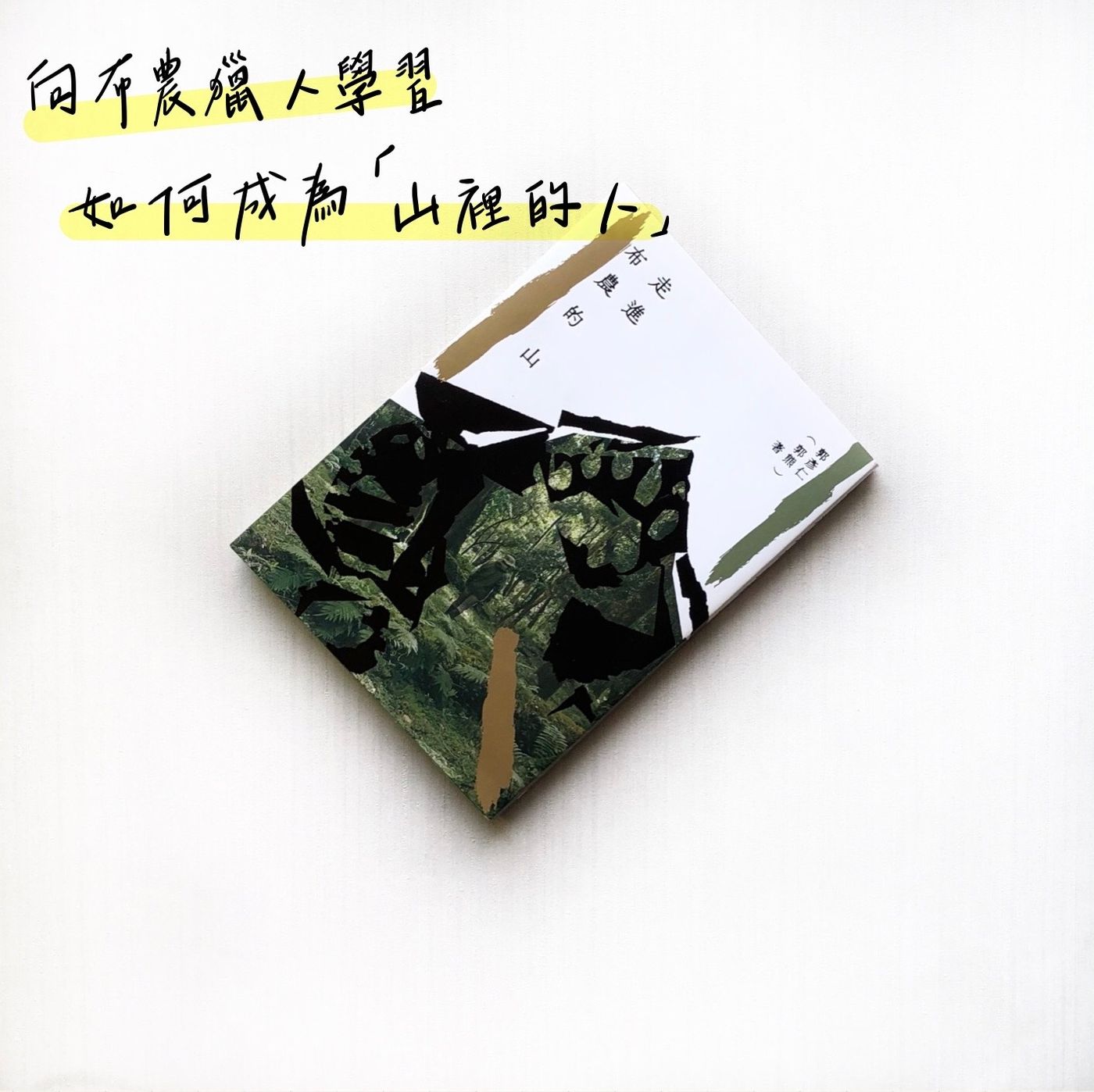4/22(五)晚間,「成為人的地方」——郭彥仁(郭熊)《走進布農的山》書友會
「山頂沒事我們不會過去,那邊是禁忌的地方」(頁一九六),這句話一語敲醒了快要讀完整本書的我,並且,就像是一個初入山、不理解山、也不知道到底為什麼要爬山的人般,我不知道什麼叫做「布農的山」,我只是想著,想要知道郭熊的經歷、想要知道他走過的山路、他的山林故事,但直到這句話,我才意識到,啊,這不是在談登山的書——以談登山來說,郭熊寫的入山經驗都太迷人了,但爬過山的人或許可以從中辨識出,那是因為熟練才能帶來的「舒適度」,甚至,現實裡可能離「舒適」的距離還很遙遠,但郭熊讓我感受到的是,他,彷彿,回到了家。「對你們來說,這是在登山。但是,對我來說,你所謂的登山,就像是我走進家裡一樣。」(頁一九七)這是郭熊引述布農族人關於登山的認知。所以,不存在著登頂這件事,那麼,回家是什麼意思?回家是舒坦的、有沙發可睡、有乾淨的水可飲,儲存著可以供足你溫飽的食物,是你熟悉的場所、讓你放鬆的場所,你會悉心保護、不讓人隨便破壞的場所。
我們較為熟悉的「登山」模式是,帶有一種「有毒的男子氣概」去登山:是要征服、要把山踩在腳下、從山頂滿足地俯瞰大地;無法攻頂是失敗的、山頂是挑戰神的領域;當然也有另一種面向,要尊敬山、從山裡不帶走不留下東西——那麼,登山/入山是為了什麼?體驗?觀賞?如果說,登山是「回家」這件事首先提醒了我,布農人與山的關係與我對於山的認知不同,那麼,在最後章節郭熊寫到的狩獵行動與現場,讓我全盤、徹底翻新人與山的關係,那不只「回家」,而是與「家」的關係的重新盤整。
家不是予以與求的場所,而是取/還之間的平衡,你從家裡帶什麼走,那麼你也要有還什麼給這個家的認知;家是生長你的場所,是讓你成為人的地方。
郭熊沒有寫到這些話,但是他每一章節平實的、穩定的、逐步讓讀者跟著他熟悉這個山林所在的動物、植物,都在傳達人與山林萬物之間的關係,不是人與「物」,而是人與生命。你有你的故事,而存在於這個山裡的萬物,也有他們的故事。人為之取名,是帶著「認識」命名,這個認識不是數字、不是分類,而是取名的人,與這個物種之間的關係、對他的認識。
譬如,談到赤楊這個植物。
赤楊,布農族語裡叫做「海諾南」。從網路上的植物資料裡可以找到,赤楊是一種先驅植物,原住民過往在休耕期焚地之後,先長出來的植物就是赤楊。赤楊同時也是很好的生火材,「如果上山碰到下雨,只要找到赤楊樹,就不怕沒有營火。即使是用活的赤楊木,也容易燃燒。」(頁一九九)這樣的知識,或許對於山林熟悉的人也會有,不過,郭熊接下來轉述了布農族人關於赤楊的一則傳說:
「其實海諾南是會走路的樹人。從前,老人家可以跟大地萬物溝通,只要家裡沒有木頭,就對著窗外,大喊『海諾南,沒有木頭了』。赤楊聽到呼喚,緩緩走進家中,然後抖動身體,枯枝就掉落在地上,因此無需辛苦蒐集木材。」(頁一九九)
這太美了。也是在同一刻,我意識到,有多少類似這樣的故事,已經消逝在歷史之中。
在最後一章〈祖靈的禮物〉裡,郭熊花了一些篇幅寫入山狩獵的事。這件事,我想要留給現場來談。在每一章節裡,多多少少我都感受到、或者因而觸發關於當代對於山林的諸種議題的面向,但是,郭熊雖然沒有著力去談議題,但我也從中獲得了許多的啟發——譬如他談到原住民的登山,與現代人用GPS定位、等標線來登山的模式不同,他們從地景、獸徑、環境跡象來認路,山林在族人眼裡,處處是富含文化意義的地理資訊,不是數字、標高與方位。因此,郭熊也提到,在一九九〇年代,台灣開始有學者嘗試用『部落地圖』的概念,去建構每支族群的文化、生態和傳統智慧」(頁一九六);或者,書裡大量談到的黑熊之事(郭熊長年跟著黃美秀老師做黑熊研究)、布農族的生活、禮儀,身為獵人與獵物之間的關係......等等,儼如一條又一條敞開的山徑,令我著迷與驚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