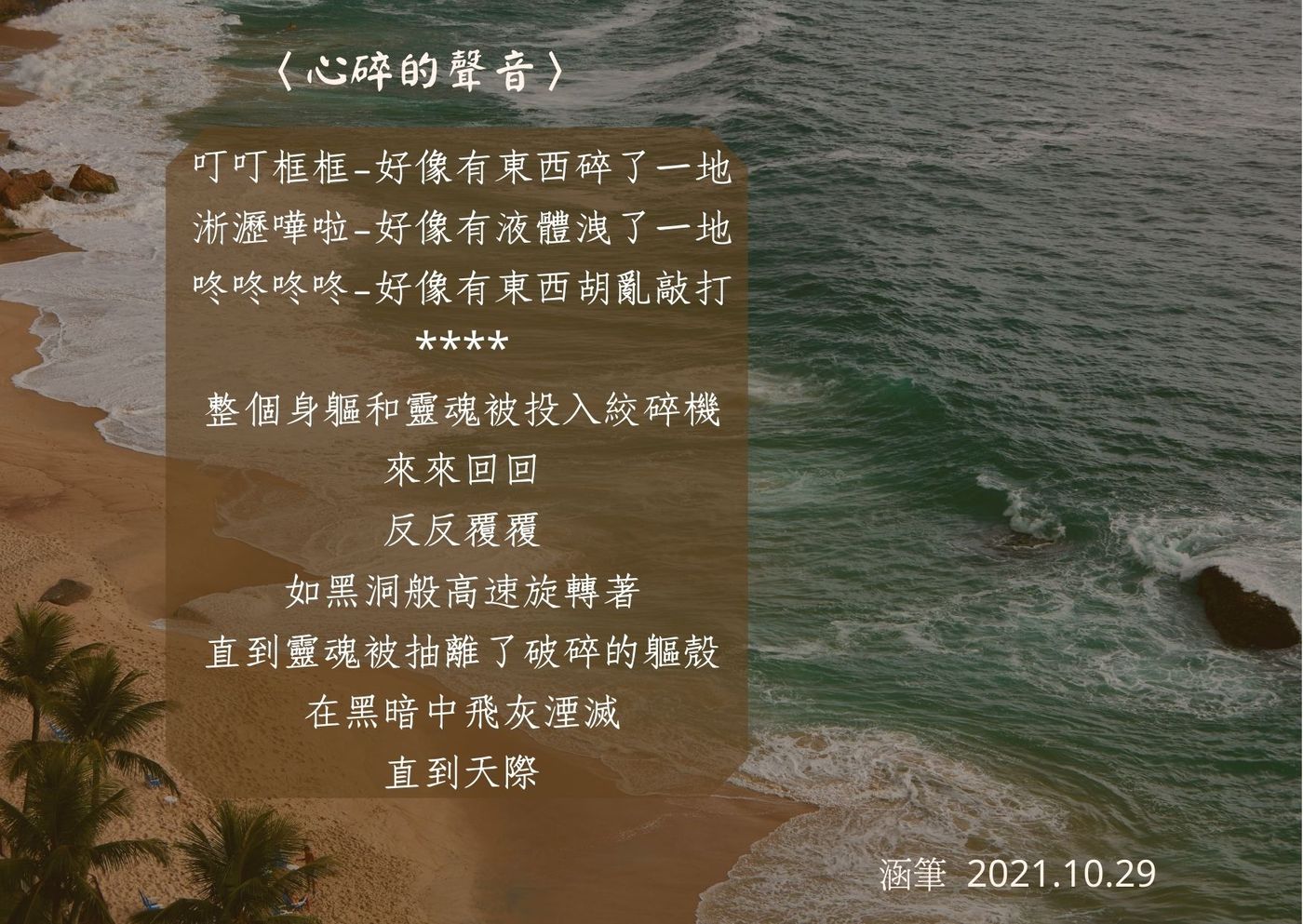朋友引介了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輾轉遠道而來,說想要和我聊一聊他的人類圖。我有些異樣的感應,說不上來是甚麼。以我二爻的孤拐,八竿子打不著邊際的人,我通常會推託自己技藝不精,還是另找高明吧。但我竟然說好,請他跟我聯絡。
對方是個客氣有禮的人,他的職業寸秒寸金,在我面前卻一派從容、彷彿隨我揮霍。我由衷感激他給予我這種極度奢侈又不知從而起的付託。
約好時間聊了十幾分鐘,我感覺他始終不在狀況內,不是因為他心不在焉,相反地,他極為專注。然而那種專注,莫名讓我聯想到包袱。伴隨著拼命忍耐、而且忍耐了好久的負重感。我直截了當地問,你還好嗎?是不是有別的話想說?不聊人類圖也完全沒關係喔。
他沉默了。我說,如果還沒準備好,不用勉強。那我放一首歌給你聽好了。聽完了你還不想說,就讓你去忙或去休息。
我不是甚麼音樂精靈,我看不懂五線譜,對於音樂鑑賞的能力很通俗。我放了電影<Piano>的主題曲《The Heart Asks Pleasure First》,每當我覺得自己負重前行,委屈得說不出話來,沒有人能夠接受、沒有任何人可以理解,我就會聽這首鋼琴配樂。讓混亂跳動的心在同樣澎派的音律中得到片刻穩定。
音樂聽完,他用水般清澈的聲音也不再沉寂,最近遇見了一個特別的人,沒有想過會在此時遇到。是soulmate。但是、但是、我已經not available。
清澈的水被偶然的礁石濺起浪濤,最後的那一句not available,聽起來很破碎。想要佯裝完整無波地回到原本的水道之中,卻再也去除不掉曾經滄海的翻騰洶湧。
我覺得自己混帳,應該要放棄卻這麼不甘心。應該要更專心可是我很難控制自己的心。
故事終結在這裡,沒有再說下去。我想,他終究是個溫柔與明白的人啊,沒有冀望從陌生人這裡攫取解答。他只卑微索求聆聽。
我回想起一開始還沒聯繫上時的異樣感,就是這個吧,我這裡也不會有答案,但我有個故事可以說給你聽,使你暫時喘息,然後有一天,你能坦然面對被自己握在手裡的答案,不再覺得自己混帳。
都快五十歲的歐巴桑相信soulmate嗎?當然啊。相信的程度一如未經世事的青少女。只是我並沒有把這個角色框限起來,覺得只能是伴侶或情緣關係。我也沒有奢想單一而傳統的結局。在一起不是唯一。
十幾年前吧,我處在一份煎熬又糾纏的感情關係裡,但那時並不覺得錯誤,心裡想,如果我再努力一點、再多愛對方一點,就能讓狂暴的他平靜下來,然後我們都會獲得幸福。
那陣子我哭得很多,哭一哭就又會有力氣、去努力多愛對方一點。台北的雨也下得特別多,我們總在傾盆大雨中迅雷不及掩耳地爭吵,甚麼都能吵,任何小事都會讓他大發雷霆。吵過了他會慣常地拂袖而去,就這樣落下還沒熄火的摩托車,以及還不會騎車的我。數不清有多少次,我使盡吃奶的力氣拖著那台機車走遍大街小巷、上橋下橋,一開始會抱持著最卑微的希望,也許走到下個路口,就能剛好遇上已經氣消的他。但每一次,就連這麼卑微的希望也落空。
最後,我只能用所剩不多的力氣,把摩托車停靠在離我家最近的小巷停車場。雨早就停了,我全身上下還濕漉漉的,冷得發抖。
在我連疲累都感受不到、只強烈感覺到羞恥的時候,我聽到背後有聲音在說,「妳的排氣管都浸水了,這樣下次會發不動的喔。」
我回頭,說話的人是一名黑手。他的店就開在我家巷子口。他時常看我來回牽車,以為我遇到了拋錨事故。我沒有力氣解釋這不是我的車、我根本不會騎車、我和車子都被半路丟包不只一次了你是看不出來嗎。有哪個正常的男人會這麼做、又有哪個正常的女人會一次一次長途跋涉、把不屬於自己的車牽回家裡來。
委屈與憤怒不打一處來。我居然又哭了。黑手張皇失措地漲紅了臉,走開一會兒又回來,「那個,我可以幫妳看一下車子的狀況。有甚麼狀況都可以解決。妳不用哭啦。」我哭得更響了。那我到底甚麼狀況,為什麼無法解決。
黑手最後幫我把車子拖去修,原來不只有排氣管的問題,細細拆開來千瘡百孔。就像我和他的關係。黑手問我,「妳還要修嗎?可能換一台比較快吧。喂,妳不要再哭了哦。我保證算你便宜。」我不知道再執拗下去有甚麼意義,心裡想,也許把車子修好了,我們也會跟著起死回生。有愛就有救。我是那麼相信,愛可以救治與修復一切。
黑手不理解。看著我視死如歸的模樣,只能照做。那是一台老車,許多零件得東調西湊,有時好不容易組合上去了,又會出現新的問題。如此周而復始地過了一整個夏天與秋天。
我和他之間,沒有太大的變化,吵吵好好,日子過得極端而沒有盡頭。看到小說上的一句描述,「她覺得來到世界的邊緣,而且已經踏出最不該踏的那一步。」,不禁為之顫慄。為了證明自己不是想要和主角一樣粉身碎骨,我時不時就會去黑手的店裡,關注一下那台車修得怎麼樣。
黑手曾跟我說,自己沒有讀過甚麼書,聽不懂我太多感觸。但他給過我的盼望與鼓舞,卻反而是受過高級教育的人所吝嗇、所不能給予的。
他把零碎的物件攤了一地,然後示範著如何組裝成一台車子主要的核心動力,我聽著聽著就發起呆來,直到聽見引擎發出威武的嘶吼聲。「妳看,車子就是這樣,一點點都沒有辦法馬虎。所有的東西都對了,才會活起來」。
他的手總是很髒,即使在水龍頭底下沖洗過很多次也還是一樣。「我有跟妳說過嗎?我哥哥是醫生,我們一樣每天都要刷手。可是,哈哈,妳看我的手,差很多厚。」黑手的手布滿了厚繭,還有些新傷隱藏在肌膚的皺褶處,我問他會羨慕哥哥的手嗎,乾淨而無傷。黑手說,「有甚麼好羨慕,他的手壓力有多大。是救命的手。可我的手也不差喔。等把妳這台破車修好那天,妳就知道了。」
黑手很喜歡聽台語歌。甚麼惜別的海岸、返來我身邊、愛我三分鐘,對我而言簡直天外之音。唱到忘情之處,黑手把螺絲起子抄到我嘴邊,「感情的世界愈跌愈深,希望你對我疼會落心,你愛的敢是東門町西門町,彼款現代女性…接下來那段換妳嘿!預備喔!」
我用含糊的台語跟著唱,「感情的變化看矓末清,舊年的咒詛敢通相信,是不是愛我三分鐘五分鐘,過後就冷冰冰。」江蕙的歌聲好像有一種魔力,明明哀怨也能唱得輕俏。我忽然很想隨著伴奏的鈴鼓擺動一下。
我們在擠滿新車與舊車的縫隙間跳起滑稽的恰恰。我是個很糟的舞者,好幾次同手同腳,卻是長久以來第一次,我感受到活著,原來是這麼輕鬆的一件事。不需要牽就對方的拍子、不需要擔心對方會不會不開心。
我像個蠢蛋一樣地笑著。呆呆地笑出了眼淚。
車子終於修好的那天,冬天也快過完了。黑手已經知道這台破爛車的所有破爛事,而絕口不提勸慰或寬解的話,一昧笑得燦爛,「妳們是這樣講嗎?甚麼杵甚麼針的。」
我笑得前仰後合,「是鐵杵磨成繡花針。你的手果然厲害,我要送你四個字,妙手回春。」
黑手回頭把車子牽到我手中,經過這一段時間,我大概能夠掌握騎車的技巧,終於可以緩慢地騎上路、騎去對方那裡、就算一言不合,也用不著再苦情牽車了。我看見黑手自作主張幫我在車體下緣貼上的反光貼,「妳這樣安全一點。晚上妳就慢慢騎。然後,要哭就不能騎車。妳的技術還沒好到那種程度。」
我覺得好笑,其實大部分的時候我並不是這麼軟弱的女生。但想想好像沒甚麼說服力。我騎著妙手回春的車,真能跨越冬天,說服對方上車、和我一起到達春天嗎?還是做為一個堅強的女生,我應該逕自揚長而去,去尋找自己的春天呢?
我忐忑著沒有起步。黑手鑽進鑽出,不知從哪裡摸出一枚透亮的蘋果,放到我手中。「給你,行車平安。不用怕。車子摔了我再給妳修好。我妙手回春。」
許多許多年後,我依然記得那只紅蘋果。光鮮奪目地棲息在油汙滿布的手掌中,紅與黑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那隻給的手,從不因為懸殊而退縮,他技藝精湛修好了早該報廢的車,以原始的純良、毫無所求地對待我,如同珍貴的紅蘋果。使我相信,我值得陽光、空氣、雨露。如果春天遲遲不來,我不用傻等、苦求,只要自己還在,便是好天。
聽到這裡,銀幕那頭的男人問我,後來怎麼樣了。
後來,我把車子順順地騎到對方樓下,停在他能找到的老地方。然後我慢慢沿路走回去,每往回走一步,過往的末日感就褪去一些。最後我發現,我平安回到家了。
黑手沒有繼續開店,那年年底,他必須回鄉接手父親的農田,他孝順得沒有心眼,不像我老愛跟家裡討價還價。他拍拍我的肩,「算了,兩個兒子總要挑一個來接吧,那就妙手回春的來接。該救人的讓他去救人。」逢年過節,黑手都會寄給我田裡的農作,有時也有蘋果。這幾年我們紛紛成家,聯繫疏落,然而包裹總是準時寄達,我知道他仍在嘉南平原一隅當妙手回春伯。因而替他感到開心。
我跟男人說,我能明白、也深信soulmate所帶來的衝擊。它們來得意外,給你巨大的收穫。因為太想佔得又不可得,所以苦痛。
不過,我覺得soulmate並不一定是用來長伴此生的。若能和soulmate結合固然可喜可賀,若不能,知道soulmate存在,而你們能遇見,不也很好嗎?soulmate的出現,何妨當成是生命給予的另面鏡射,慾望有幾多,匱乏就有幾多。恐懼有幾多,得失和代價也有幾多。
你可有想過,這些匱乏,是可以鼓起勇氣向關係中的另一半要求的?或者你也可以改變些甚麼?若始終無法如願,你是否足夠勇氣終結既有關係,而不先落入嗔癡糾纏。以及,soulmate能夠給予的滿足感,我們能不能先給予自己?若連自己也無法滿足,何以奢求談愛。
The Heart Asks Pleasure First,直白地來翻譯,是說,我心渴求快樂。但聽了這首歌這麼這麼多年,它在我心中已經徘徊出更深層的意思,渴求之前,先問問自己是否快樂,先努力讓自己快樂。
表達對於一個人的珍惜,何必朝朝暮暮。讓對方看見、也知道,你會如同珍惜對方一樣,來珍惜自己。如此,才不辜負soulm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