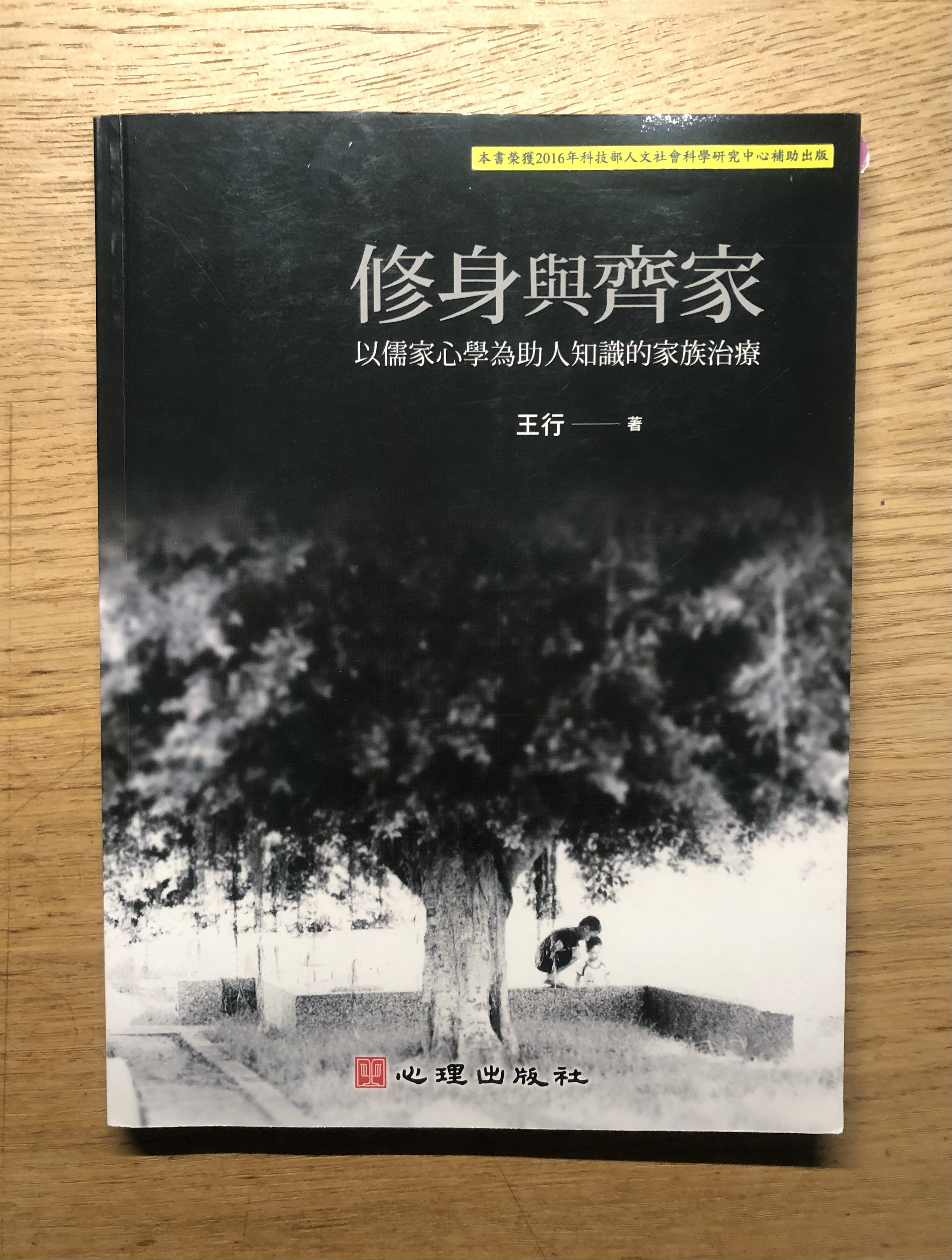性之善、惡論關乎教育方式
關於古人非常重視的「性善/性惡」討論,早已不是今日的主流議題,不是一般人所關注的話題了。時至今日,已經淪為只要遇到不好的事情,人們便說是人性本惡;遇到好人好事,便說是人性本善,成為一種帶著消遣與玩忽態度的說法了。其實嚴肅說來,討論性善性惡?看似不關乎今人興趣的論題,其實關乎著教育方式,關係到每個人在成長過程中所受到的養成教育、人格形塑的品格教育方式。簡單地說,「性善」說主張每個人與生俱來、內在自足的美好德性,其所對應的教育方式是擴充德性,使美德發揚光大,即孟子說:「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而「性惡」說也不是主張人性為惡,它是強調客觀規範對於人的形塑作用,主張通過禮教規範以使人的行為合乎理性標準。當禮教形成內化以後,就是一種「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的狀態,即使是柔弱的蓬草,只要種在堅挺的麻田中,自然能夠長得挺直。至於我們試圖了解古聖先賢,並不是復古,也不是老古板或古董玩意兒;而是為了能夠站在巨人肩膀上看得更高更遠,是要藉古鑑今、古為今用。只有理解了歷史與古人的思想,我們才能知道自己的思想從哪裡來、人與人之間為什麼會有民族差異性?並得力於古人的經驗與智慧。因為在任何時代,品格教育都是美善社會所不可或缺的。
漢代哲學強調師法教化
在我國哲學史上,相對來說,主張天人同構、強調氣化宇宙論的漢代哲學是受到冷遇的。它不像宋明理學作為儒家道德學主流、並長期主宰科舉般受重視。甚至,很多天人同構的說法長期來被斥為迷信,認為不能挺立人文價值。並且因其天人宇宙論圖式,很受歷來學界貶抑,說是「儒學一大沒落」、「中國哲學之衰亂期」;不過,這樣的思維在民間卻是綿延不絕、至今不衰的,就如同沒有人看過鬼神卻也不能否定一樣。
董仲舒作為漢代氣化宇宙論的代表人物,強調「天人感應」說,可是在今天,他也不是一個被討論的熱門對象。實則董仲舒在漢代說「天人感應」的天人觀有其特殊歷史背景:秦朝太短,短到不足以建立起一己的思想體系;到了漢朝,同樣延續秦朝的大一統局面,所以從秦到漢,已經迥別先秦時期的天下分裂局勢了,試問,此時民何所逃於天地之間?或說普天之下還有什麼權勢力量大過皇權嗎?這樣的皇權一家獨大與號令天下,還能有什麼制衡的力量嗎?當我們在理解漢代司馬遷為什麼也突出天人感應,說:「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日變脩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肯定日、月、星辰的變化與人事現象的聯結,並以此說明為什麼要占卜的原因,以及董仲舒何以據《春秋》一書以觀天人之際、說陰陽災變,他說:「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降怪異以驚恐之;尚不知變,而後傷敗乃至。」他把災變視為上天的譴告,是上天對於德政的要求與示警。如果我們對於漢儒試圖在君權之上再加上能夠制衡的神權,能夠參酌這樣的社會背景與心理結構,或許就能有更多的同情與理解。
性善、性惡爭什麼?
再回到性善、性惡說,以下所要敘述的董仲舒性論思想,正是立足在此一社會基礎上,提出他獨到的、切合時代需求而強調王道教化之人性論主張。不過因理論背景的需要,這裡要先敘述孟子、荀子的性論思想不同,並梳理這兩大儒學流派在我國後世的不同際遇發展,希望能有助於今人認識「我」的思想究竟從哪裡來。
由於孟子「性善」說後來獲得宋明理學的發揚,尤其南宋朱熹《四書集注》從元代起得到科舉建制的主宰仕進優勢,長期來始終穩居儒學正宗;反之,荀子「性惡」一說被從孟子的對立面看待,像今人勞思光《中國哲學史》便稱荀子為「失敗之儒者」、「儒學之歧途」,甚至認為秦漢以後中國文化精神之弱敝,「內在樞紐,皆由荀學之病。」歷史上相對來說,逮及清儒才比較看重荀學,比較能夠肯定荀子的傳經之功。如汪中肯定「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傳之。」直以禮樂之教、傳經之功歸諸荀子。劉師培也說荀子「是為漢學之祖。」
孟、荀「性善/性惡」說的判教究竟為何呢?其實他們爭論的焦點,在於「善」到底是不是我們天生所本有?還是後天的外向學習?超越的道德本心是否人性固有?道德創造性是否根源自我們的人性?――所以他們不是在爭「性」之善、惡;而是論「善」之內在本有、抑或外向學習?至於所謂「性惡」的說法,其實是荀子說人性充滿了欲望,若是沒有「禮」的規範與節制,便極有可能會流入於惡,他所要強調的,實是「禮」即禮教的外向學習與規範、人為的師法教化與學習。而荀子的〈性惡〉,就只是一個篇名的說法而已,並不可直解為人性是惡;他說的是:善非人性固有,是經過學習所呈現的結果,用孟子的話說,就叫做「外鑠」,是故荀子隆「禮」而勸「學」。
孟、荀的「性」論定義不同
這裡面涉及了一個很重要的、孟荀對「性」的定義不同問題,也就是他們兩人對於「“性”究竟是什麼?」的定義與邏輯範疇很不相同。
孟子從「人性」來定義「性」,荀子則從「天性」來看待「性」,並由此導致「德性/氣性」的進路殊異:
孟子談的是性論範疇中的「人之所以為人」,即一個人為什麼是人而不是禽獸?所以必須著眼於「人、禽之別」,也就是人和禽獸不同的部分;必須是在吃喝拉撒睡以外的部分,他認為這才是「人性」,所以孟子的性論會導向以「德性」論性。然而荀子是從天生自然的「天性」角度來看待「性」,因此會突出其好惡,譬如:「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動物都是餓了想吃、冷了要保暖、累了要休息的,也都是充滿耳目口鼻等種種情性欲望,「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的,這是導向「人、禽所同」的天生本性。這是因為荀子認為「性」就是指天生自然,「凡性者,天之就也」,是未經後天人為雕琢、未經學習與人事作為,「不可學,不可事」的;至於人和禽獸的不同,乃在於人的智性可以接受後天的師法教化、禮義學習,禮義法度是出於聖人所創制,並非生於人之天性。所以對荀子而言,「性」是先天的,「生而有欲」是人禽所同的;人禽之別,在於智性的後天學習,所以他的「性」論是以「生而有耳目之欲」的氣稟之性立說。
董仲舒以「本質義/歷程義」說「善質」與「善」
至於我們說的,所謂的「善」,那必須是指落實實踐的結果而言。即連孟子的「性善」說,如果未經擴充存養,也不能必然地保證「善」能被實踐,所以孟子也說仁義禮智等四端之善,「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如果不能充分擴充善端的話,即使個人的立身處世與侍奉父母,恐怕也都會出現問題。然而要落實實踐經驗界的善,必須是有歷程的,並不是只要具備了善端、善性,就一定能夠在現實的生活世界中完成「善」的實踐。以此,董仲舒用睡覺的「醒覺睜眼才能見物」來說明「善」。雖然我們有眼睛,但是當我們睡覺時閉著眼睛,那是看不見東西的――「性有似目,目臥幽而瞑,待覺而後見。」當我們還沒有醒覺時,我們只能說是具備了「可以見」的本質,卻不能稱之為「見」――「可謂有見質,而不可謂見。」於此可知一個人具備了什麼本質和已經能夠充分實踐,兩者之間存在著「本質義/歷程義」的極大差距。因此人之性,如果只是「有其質而未能覺」,那麼就好比「瞑者待覺」一般,必須要「教之然後善」。當其還是處於「未覺」狀態時,那就「可謂有質而不可謂善。」因此董仲舒所凸顯的,正是王道教化對於「善」之實踐具有助成的重要性。
就此而論,在性論思想關於「性」的定義上,董仲舒是親近荀子的,他也認為「性」指向先天、而「善」之實踐是後天的,「善」必須依賴「王教之化」才能被實現――「性之名,非生與?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他強調天生的自然之資就是「性」。但是於此,他同時也說:「性者,質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換言之,就「性」的本質內容而言,他認同「善質」是天生內具的,只是他說的是「質」的具備,而不是已經通過實踐歷程的完成義,這裡,則他和荀子之反對善性是天生固有,又有其距離。荀子說的是,「其善者,偽也。」偽的意思是外在人為,指「可學而能,可事而成」,其與今日多指虛偽的用法不同。也就是說,關於「善」的實踐,荀子純任後天的外向學習;董仲舒則認同必須結合先天的「善質」和後天的「王教之化」,才能完成實踐,那麼就善質之內具而言,則他又親近孟子。可知他對於孟、荀性論,各有分合與調和。
再者,董仲舒曾以「善如米,性如禾」,來譬喻「性」與「善」。他說整棵的稻禾並不都是米,它還包括了其他部位的根、莖、葉、稻花、稻穗、糠殼……;須是經過提煉後的最後精華,才是可以供給人們食用的米粒。這就如同董仲舒從自然氣稟說「性」,而性有仁、貪,所以雖然「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善」是完成道德實踐後的結果,是必須結合內在的「善質」和外在的「王教之化」,在內具本質的基礎上再加上後天的努力,才能落實實踐的。所以他又說:「以米為飯,以性為善,此皆聖人所繼天而進也,非情性質樸之能至也。」善的實踐,要有內在本質再加上聖人禮教陶鑄的「繼天而進」努力,所以此時已經不是天生的本性了,而是整體社會通過聖人制教的一起努力結果。
因此最後我們就可以回到董仲舒在漢代為什麼如此強調王教思想,以及我們在今日說性論思想與教育方式的關聯性上了。在太平盛世的大一統時代中,致力於儒學的道德教化,是「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想要涵養品格、形塑人格的最佳途徑。即使在漢代君權至上、無可與之抗衡的時代中,教化仍是可以讓我們的社會臻於「明明德」、「止於至善」的不二法門,這才是漢代哲學凸顯「天人同構」背後所深蘊的理想主義。而立足在「性善」說上,我們應該擴充德性、光大美德;理解「性惡」思想,則我們也要肯定禮教內化對於品格的陶鑄作用,二者相輔相成。同時我們極力呼籲:不論在任何時代,品格教育都是美善社會所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