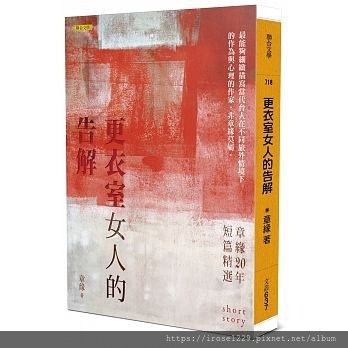章七十五
「盧、盧、盧、盧、盧啊──」四方喧嘩鼓振耳膜,安奉良手執三枚成疊的紅棋,行至終點。
這是杭州城內的一間小賭坊,賭坊沒有名字,僅在屋外的牆壁大書花俏的「博」字,門面不怎樣,裡頭卻一點都不馬虎,時下流行的博弈樣樣不缺,簡單的擲骰猜點比大小,難一點的如樗蒲、雙陸、彈棋等等,賭運氣也賭技術,甚是趣味。
安奉良玩的是樗蒲,是一種擲采行棋的遊戲。下棋者有二,各執六枚棋子,稱為「馬」,棋子圓扁可疊。手擲的「采」則是五塊由樗木削製,形狀如梭的骰子,一采分黑白兩面,當中三木的黑面會分別刻上「犢塔」、「犢塞」、「撅」,其白面則刻「雉禿」、「雉梟」、「開」,搖杯而擲,依采面決定棋子要走的步數。五采全黑叫「盧」,可前進十六格,二雉三黑是「雉」,可行十四格,兩犢三白則為「犢」,走十格,全數為白行八格。若單擲出犢塞、犢塔或撅,其餘盡白,是為「塞」、「塔」、「撅」,分進十一格、五格及三格,單擲出雉禿、雉梟、開,剩下全黑,分為「禿」、「梟」、「開」,走四格、二格和十二格。
樗蒲的棋盤寬約一尺,長四尺有餘,棋盤上排列著一百二十根細矢,矢間為落子的棋位,細矢分成三聚,一聚四十根細矢,聚與聚的間隔稍大,為「關」。棋子會先並列棋盤長邊的一側作起點,另一側為終點,以六子全數抵達終點為勝。棋子過「關」時,須擲出「貴采」,亦即盧、雉、犢、白四采,才能過關越至下一聚,擲出貴采以外的便是雜采,最多只可陷於關的前一個棋位「坑」等待,須擲得貴采,方可繼續走棋。若己棋在同個棋位,可堆成棋疊一起行進,最好玩的莫過於行棋恰好落至敵棋處時,棋疊數量若多於敵棋,可將之打回起點,反之則換己棋回到起點重新開始,疊數相等則無事。過程緊張刺激,對棋的二人步步為營,圍觀的看客們同樣熱絡喧鬧,盼望支持的棋手能奪得勝籌。
「叩啦叩啦叩啦……」輪到安奉良的對手搖杯擲采,他的局勢大好,二疊棋僅差五個棋位便要到終點,另外四疊棋則差了十個棋位,安奉良雖只剩三疊棋,然離終點尚距遙遙三十一個棋位。
「叩啦叩啦叩啦……叩!」搖了許久,采杯總算大力叩桌,揭杯一瞧,一木犢塔四木白,是塔采,行五格。對手將四疊棋行到二疊棋處,堆成六疊棋,距離終點還差五格,可說是勝券在握。
「叩啦、叩啦。」安奉良擲采揭杯,是盧采,雖能行最多棋位,然行完仍有十五格要走,贏面很小。
「小兄弟,你手氣蠻旺的,連得兩次盧采,卻不幸碰上我──樗蒲界的霸主,再好的運氣到我面前,通通無用!」那人搖杯嘻笑:「讓你瞧瞧本霸主的厲害,盧啊──呃……」
是禿采,僅可走四,離終點就差一格。
「沒關係,沒關係,不過是奪勝前的一點小波折而已。」那人仍舊神態洋洋,由於此局是安奉良先手,他若沒在這一回合擲得盧采,先過終點,那麼輪至對手時,縱然是擲出步數最少的梟采,亦得搶先抵達終點,贏下這一局。
「盧、盧、盧、盧、盧……」觀眾熱情地替安奉良吶喊助威,然則盧采哪有這麼好擲?況且他已接連擲出盧采,想再擲得第三次?難吶!
身處熱烈的叫喊聲中,賭徒不慌不忙,悠悠執杯搖之,叩啦叩啦三五下後,叩杯於桌,眾人屏息以待,他卻不急於揭曉,而是道:「大哥,我想加注。」
那人捻鬚嗤笑:「加甚麼注啊?小兄弟,你前兩回擲出過盧采,氣數已盡,別浪費在這局了,留點運氣和賭金給下一局用,方有翻本之機……只要對手不是我的話,哈哈哈哈哈……」
「你怎知我今日的氣數是多少?」哆的一聲,十枚黃籌散落賭盤,一枚黃色籌碼為百文銅錢,十個就是千文,等同於一貫。安奉良右手壓著采杯,左手靠著憑几,雙腿一盤一屈地欹坐,姿態頗為狂妄:「你賭不賭?」
旁人見著賭注議論紛紛,心中均道哪裡來凱子,生得俊,錢又多,可惜傻不隆咚的。那人被激起賭性,舔唇道:「賭就賭!」欲將籌碼盡數下至賭盤,然數量不足,正要叫隨從再多換些籌碼來,安奉良卻言:「慢著,我想賭點別的東西。」
那人眨眨眼:「甚麼東西?」「那個。」安奉良指著他腳邊的小竹籠。來這兒的人大多把目光投在賭桌上,鮮少注意不相關的物什,有些人現在才發現竹籠,籠裡關著某種禽畜,咕咕咯咯地叫個不停。
「喔!你說這隻畜生啊!」他屈指勾起竹籠,在眾目前搖來晃去,驚得籠裡的小獸上跳下竄,驚惶失措地打轉,那人卻不為所動,炫耀嚷嚷:「這是紫貂,是我託人從關外帶來的,牠們的毛皮極其珍貴,剝來做帽子最顯華麗……」「我知道牠是紫貂。」安奉良笑得燦爛,卻字字挑釁:「你沒膽賭就說,別磨磨蹭蹭的。」
「哼!」不理籠子裡的驚叫,將竹籠扔給隨從後,他道:「莫說千文銅錢,千兩黃金老子都賭得!」然後手一揚,「揭杯,我看財神爺能眷顧你幾次。」
杯緣遠開桌面,杯下五木盡黑,盧。
「哇──好生了得啊!連擲三個盧采啊!」在歡呼與讚嘆的簇擁中,安奉良收好籌碼,提起竹籠,經過呆若木雞的對手時,噙笑低聲:「看來財神爺很喜歡我。」隨即撩起門簾,走到隔壁的酒肆。
這兩間房子是由一對姐弟買下,內部打通後,姐姐經營酒肆,弟弟管理賭坊。不得不說這兩姐弟很會做生意,賭客進賭坊前,先付十文錢的入場費,拿到一瓶摻水的黃酒當招待,不只吸引愛賭成性的賓客,一些酒癮重的客人也會來解饞,順便玩兩把。賭博和肚裡的酒蟲一般,愈賭愈沉迷,越喝越起勁,一瓶不夠喝,就到隔壁再買幾瓶,順帶點兩道下酒小菜,賭得累的客人亦會至酒肆稍作歇憩,精神好些後,又回賭坊呼盧喝雉,反覆循環,曾有人於此流連三日,揮金如土,後來家裡人看不下去,讓家丁打昏抬離。
「你硬是拖我們入來,就為了牠啊!」夏時鳴取過竹籠,舉至齊眉端詳,紫貂和黃鼠狼很像,但牠的毛色黑到發亮,窗外的陽光照至其身時,隱約可見毛尖泛紫,非常漂亮,難怪原主會不遠千里地帶回。
寧澈坐在夏時鳴與桓古尋間,他道:「時已暮春,剝牠的皮來做氈帽是不是太晚了?而且……他還未長大吧?」此貂的體型稍小,圓圓的大眼透著好奇與恐懼,四肢行動間帶著笨拙,不似成獸靈活敏捷。
「我是那麼殘忍的人嗎?」安奉良落座後,斟酒自飲,「生死有命,這隻小貂會被製成氈帽還是皮裘,我都沒意見。我只是看不慣那人輕踐禽畜的態度,禽畜提供骨肉毛皮給咱們,咱們應心懷感激,物盡其用,而非粗魯地對待牠們。何況江南不似關外嚴寒,貂皮大衣不過是穿好看的,既不實用,亦白白犧牲一命,徒增殺業。」
夏時鳴問:「貂是你的了,你打算怎麼辦?」「養囉。」安奉良簡答。
夏時鳴再問:「江南與關外的天候迥然,牠受得住嗎?」安奉良又喝一口酒,回說:「夏天會難受些,好佳再杭州多水,可以帶牠去游泳,或多吃涼食解熱。」
夏時鳴三問:「牠能夠活多久?」安奉良夾了滷豆乾入嘴,邊嚼邊道:「我沒養過,不太清楚。」
夏時鳴四問:「牠能長到多大?」安奉良想了想,答:「我想同黃鼠狼般,至多一尺半。」
夏時鳴五問:「牠都吃甚麼?」「啪。」安奉良忽然放下筷箸,玩味地笑:「鳴,你替牠取個名吧!」
「唔……咳!」夏時鳴偏開臉,吸著碗裡的冬粉,「你養是養在我家,問兩句有何不妥?」
「子謐。」寧澈促狹笑道:「你先把籠子放好,不然怎麼吃?」
夏時鳴這才發覺自己正緊緊揣著竹籠不放,登時雙頰燥熱。安奉良用一塊布蓋住竹籠,笑著接來,「等會兒去買隻雞,小傢伙絕對吃得停不下嘴。」
寧澈道:「我瞧牠戒心很重,得花些時日與牠親近,令牠接納人類。」後覷右邊的桓古尋始終無語,兩眼發愣,食不知味,便為他倒酒,「進叔這麼做自有他的道理,無須掛懷。」
「就算如此!」桓古尋驀地拍桌控訴:「也不該只講一句:『不錯喔。』,然後甚麼都不說,要我去猜他的心思,我要猜幾年啊?」一口乾完酒,續又抱怨:「我在和螞蟻一樣多的船隻裡找著他,還把晉淵莊趕出太湖,後再暗殺三個都督……我的功勞雖不是最大,但能做到這些事也不容易,他猶嫌不足,那我何時能獲得他的認可,拿回狼齒?」聽其言詞,合該是向夏進討要狼齒失敗,大為不滿。
生怕人口不擇言,寧澈忙塞一隻滷雞腿進他的嘴裡,「你又不趕時間,急甚麼?」
夏時鳴亦言:「爹親對我也是如此,他從不明講我該做甚麼,任我思考判斷,往往得經多番碰壁後,才稍微提點兩句。」
「以我對進叔的瞭解……」吹涼筷間的米血糕,安奉良咬食入嘴,「你得先弄清進叔究竟要你理解甚麼,否則你再做成十件大事亦是枉然。」
桓古尋煩躁地抓耳撓腮,甚感苦惱。
「這事暫且按下不表。」寧澈另開話題:「晉淵莊的事,才剛起頭呢!」
安奉良鼻息一重:「如你所言,他們就像斷了線的紙鳶,找都找不著。」
寧澈問:「太湖如今的情勢如何?」夏時鳴答:「咱們登晷丘島的那晚,爹親就派人刺殺程寅達,人已死了。吳蛟幫現由戴成琦及薛尚善把持。」
尖銳的犬齒撕咬腿肉,桓古尋聞言哼了一聲:「他們倆真是好運,平白撿了個大便宜。早知當初揍薛尚善那一拳,我該揍得再大力些。」念及他們利用己方武力殺掉原本三個渠頭,又間接除去程寅達,攬住太湖的話事權,不免忿忿不平。
「他們很有自知之明,不強爭出頭,不輕易樹敵,雖然手段不太磊落,終是隔山觀虎鬥,坐收漁翁利。」寧澈啜飲黃酒,道:「讓戴薛二人治理太湖,總比衝動無腦的烏有義,或是受制於人的程寅達好,進叔亦是基於相同的理由,助他們一臂之力。」
「那兩人承了爹親的人情,有助於禹航會在太湖行事。」夏時鳴喝完一杯酒,續:「然晉淵莊不會就此善罷干休……我有預感,下次將是他們主動出擊。」
安奉良手指捲著頭髮,「在此之前,只能守株待兔嗎?」
正啃著雞腿的桓古尋忽道:「或者去一趟常州。」
「常州?」寧澈問:「是因為武伯信的那封家書?這和晉淵莊有關?」
夏時鳴撇撇嘴:「武伯信姓武,怎會勾結叛黨?」
「不是勾結叛黨,是調查叛黨。」桓古尋說:「我很在意他信中的一句話──面天踞床。」
安奉良和夏時鳴猶自納罕,寧澈已言:「你認為這句話指的是面具。」
「面具?」安奉良訝然:「霽泉面具嗎?你怎生推知此句另有所指?」
「不是推知,是一種直覺。」啃完雞腿,他意猶未盡地吮著雞骨,「太湖一戰鬧得這麼大,朝廷不會不聞不問……咱們很久沒見到潘文雙了。」
「那個上官舍人的得力助手?」夏時鳴轉著酒杯,「她眼下過來,恐會大失所望,咱們又沒查到甚麼。」
「沒錯,而她也知悉。」鳳眸逐漸深邃,「是以她沒來找我們,說不定她另有消息。」寧澈蹙眉考慮:「去一趟常州也無妨,遇著她就能探聽情報,可是……」
「照這個找法,你得走遍江南上千個城鎮。」夏時鳴直言:「別忘了你最初鎖定的目標是嘉興,你確定嘉興不是晉淵莊的老巢了?」
「所以我才一個頭兩個大。」寧澈左手撐頰,「我根本無從確定。」
右手梳過濃密的捲髮,安奉良道:「何不依進叔所說的,變換角度?」「譬如呢?」桓古尋問。
「譬如……那半株沒燒完的香草。」安奉良道:「咱們一直著重在香草從哪兒來的,但……那真的重要嗎?」
倨傲的眉角一軒,夏時鳴反問:「若不重要,柯昱揚何必特地差人回出江寺銷毀?」
「興許他不是要銷毀香草。」澄淨的玉瞳爍爍,沉聲而述:「我和小澈碰到那個鎮民時,他說柯昱揚僅要他把香草和香爐清理乾淨,沒有其它特別的囑咐。」
「對啊……」寧澈也憶起當時的情景:「清理乾淨這詞相當曖昧,倘使鎮民嫌麻煩,隨意丟棄香草,即便當下沒遇見我和阿尋,事後徹底搜查出江寺,仍能搜出那株香草,若真為銷毀而來,他該下達更明確的指令,例如燒掉它。」
安奉良道:「換句話說,香草給外人取走,他們亦無所謂。」夏時鳴說:「從香爐裡拿出香草就好嗎?這也太奇怪了!」
「不,不奇怪……」喃喃低語後,寧澈另問:「慧觀猶在出江寺嗎?」
「早就跑了。」夏時鳴應說:「陵叔查過,出江寺現今半隻貓也無。」「慧觀沒回去?」桓古尋納悶:「他設局下毒進叔,此後還裝作沒事的樣子在寺裡晃蕩,為甚麼現下不回去了?」
「或許是慧觀意識到出江寺不安全,或許是晉淵莊強行帶走他……不管是何種原因,假設是因出江寺無人,柯昱揚方清理香草,但香草本身並無特殊之處,那麼重點應不在香草,而在清理這個動作……」聰敏善思的頭腦驀然靈光一閃,挺胸直腰,「這是一個信號!」
「對,信號!」桓古尋跟著醒悟:「他是要通知某人,慧觀已離開出江寺!猶如吹號角或點烽火,讓遠方的人知曉發生甚麼事!」
安奉良問:「給誰的信號?」
寧澈旋即塌下腰背,仰天喟嘆:「事隔多日,想追也追不到。」
夏時鳴擰眉:「明明多次接觸對壘,依然如墜五里霧中……我甚至懷疑太湖那一仗他們是不是故意輸的。」
「有點耐心,比起在洛陽時,晉淵莊近來的舉措謹慎很多,如同兔子不吃窩邊草,表示咱們離得愈來愈近了。」紅舌探出唇廓,桓古尋道:「而老練的獵人,總能在一叢亂草中,翻出兔窩。」
*****
「船首方鬥浪,船底平坐灘……」彼者呼,此者應,和著木槌的敲打、刀鋸的切割,由東至西,猶似連綿起伏的山峰,依次放聲高歌,嘹亮而動聽,傳徹江岸:「船帆高使風,船舵寬馭流……」
禹航會船塢的會客室內,談皓眼觀茶壺上的題詩,耳聽屋子外的歌聲,兩相對應,豐潤的唇瓣微彎:「我只知禹航會的船結實不沉,卻不曉禹航會的人個個一副好歌喉。」
夏時鳴為客人斟好熱茶,道:「船工的工作勞心勞力,唱歌能排憂解悶,待會兒再送涼茶甜湯給他們喝,好應付繁重的體力活。」
謝追鴻讚道:「夏少主如斯體恤下屬,在你們家做事,真是福氣。」
「底下的人越開心,幹起活來就越勤奮。」然後少主切入正題:「貴派此行除了購買船隻,尚有我能幫忙的嗎?」談皓應道:「買船無非是為賺點外快,依您的眼光,可否為敝派指點一條明路呢?」
他答:「那就要看二位心屬何地何船了。」「哦?」謝追鴻道:「願聞其詳。」
「跑船買賣便是從外地捎來該地沒有的物事,從中賺取差價。」夏時鳴侃侃而談:「以杭州為例,因離貴派所在的洛陽較遠,我建議買艘大船,運送杭州的土產如藤紙、乾姜、木瓜到洛陽販賣。尤其是藤紙,洛陽貴為一國之都,聚集朝堂機要,文人書生,藤紙需求極大,在杭州裝載上船後,運到洛陽,再轉賣當地的紙鋪,即可獲利。」
「好!」謝追鴻撫掌盛讚:「賺錢這檔事,果然得討教夏少主,謝某不過是武夫,就沒這腦袋。」而後話鋒一轉,試探地問:「然而類似的買賣,相信不是僅只東滎派做得。」
料及他的顧慮,夏時鳴拋餌誘之:「放心。禹航會正欲新建造紙廠,恰逢貴派欲拓展財源,咱們互助協力。敝會以成本價加一成的價格,將紙張賣給貴派,貴派再轉運至洛陽,至於接收的紙鋪……依個人淺見,東滎派不妨自行開一家。畢竟肥水不落外人田,東滎派既能以最便宜的價格購入,何不再多花些人力物力,賺得最高的利潤?」
謝追鴻大喜過望:「如此甚好……」「夏少主若另有所求,可以爽快提出。」秋水瀲灩,微笑以對:「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對嗎?」
夏時鳴嘴角微微一勾:「我想拜託二位,聯繫潘大人。」「還有呢?」談皓問。
「既然雙方追求的是長遠的合作,自然不時得為彼此盡點棉薄之力。」少主慢悠悠地聞香品茗。
謝追鴻忙言:「這當然……」「這當然要再三思量。」談皓道:「夏少主,原諒吾等須離席再議,煩請您稍候片刻。」
「需要把房間讓給你們討論嗎?」夏時鳴貼心詢問。
「不用,我們到外邊。」不等自家師兄發話,談皓扯著謝追鴻的衣袖往外走。
到了外面走遠後,謝追鴻即言:「皓兒,你這樣顯得東滎派小家子氣,會給人家笑話的。」
談皓回道:「當前給人笑話,總好過日後遭人摒棄。」
謝追鴻又笑又氣:「你為何這等排斥當中間人?不是每個門派都能雙棲廟堂江湖,斡旋牽線,不好好把握機運,東滎派最終僅能黯然收場。」
「勞駕!」數名船工肩擔三人合抱粗的杉木路過,謝談二人側身讓開後,談皓壓低聲:「禹航會是欲借助我派在朝中的勢力,行個方便,朝堂的那些大人亦看在往日的交情,撥空相幫,如是一來二去沒甚麼,然長期以往,一旦用光那點微薄的情面,沒人會再多覷咱們一眼,那時該怎麼辦,繼續巴著別人,抑或找下一個看上咱們的人?」
「為甚麼不看得樂觀點?有越多人看見,東滎派就不會僅是區區一座小橋,天天擔心行人過河就拆。」謝追鴻試圖曉之以理:「東滎派只需成為那座撼動不得、替代不得的大橋,必能映入他人的眼中。」
談皓只道:「大橋小橋,終究僅為過道,既不在此岸,更到不了彼岸,終生立於原地,寸步難行。」謝追鴻聽了,閉目長喟,煩惱該怎地說服固執己見的師妹。
「船艙大游鯨,船板廣走馬……」一波聲浪乘著江風湧至,謝追鴻和談皓循聲望去,猶未搭起厚板的大船只有骨架和幾片隔艙板,長長的木製龍骨壓中置底,貫穿大船首尾。雖僅具雛形,然長逾十五丈,寬過三丈,未立桅桿便有兩層樓高,足見其雄偉,待船舶真正入水航行之時,可想見將是多麼壯觀。
由於水中無法施工,修船造船均需於江岸挖鑿大坑,大坑與江河有人工渠道相連,坑裡設有木樁橫梁。平時坑渠無水流動,若欲修建船隻,便開啟渠道的閘門,決水入坑,並將船牽引至坑中的木梁上,後關閉閘門,再用水車抽乾坑渠裡的江水,讓船舶高架於梁樁之上,船工便可施作,完工後復灌江水,待水漲船高,即能重返江河。修建期間,為避免日曬雨淋之患,會在四周築一幢大屋遮掩,是為藏船的船塢。
禹航會的船塢位於錢塘江與江南河交匯口,船工多達一千人,不計修葺的船隻,光是新造的船就有五大艘,每艘皆龐然如巨獸,盤踞江岸,規模之大,見者無不嘆服。
「船燈亮明夜,船人碌迎朝……」聆聽歌謠傳唱,男聲忽問:「你覺得禹航會的船大嗎?」
談皓不明白他為何忽有此問,但仍誠實以告:「不算軍艦,這裡的船一艘比一艘大,富麗堂皇,宛若江河上的宮樓。」
謝追鴻又問:「那你覺得他們家的船堅固嗎?」
「我不懂船舶,無法比較各家技藝的孰優孰劣。」談皓答說:「但我從沒聽過禹航會的船沉沒。」
接著他遙指一艘正在支起桅桿的大船,「再怎樣堅若磐石,巨如鯤鯨,船舶仍要揚帆借風,方能航行江河,必要時亦得見風轉舵,才不會桅倒船沉。縱是逆天風河水而上,也要巧妙操弄帆舵,之字前行,而非正面硬碰。」
而後謝追鴻面朝談皓,柔聲勸道:「這回就聽師兄的,到不到得了彼岸,確實取決於自個兒的才調,但於此同時,何不善用人脈,為咱家多謀出路呢?」
雙瞳翦水顫了顫,終於首肯:「潘大人近幾日似乎在蘇州,我去聯絡她。」
「那就有勞談姑娘了,我會再通知映塵此事。」不遠處,夏時鳴拱手朗聲。
見談皓和謝追鴻面色尷尬,款步接近的夏時鳴道:「我們家的工人大手大腳,粗野慣了,我怕會不小心衝撞二位,遂來找尋,恰好聽聞談姑娘欲面見潘大人。」謝談二人暗鬆一口氣,雖然心裡有數,他應已猜知東滎派的近況,但這等家務事給外人聽去,實在不光彩。
謝追鴻道:「就依夏少主的提議,買入貴會的藤紙,再由我方轉賣至洛陽,而運貨的貨船,勞煩您介紹。」
夏時鳴敞臂道:「回屋子裡談吧!請。」於是三人折回會客室。
三人商議一陣,便敲定貨船的樣式,不日開工,工期預估兩個月,最快仲夏時節,就能看見繡著東滎二字的旗幟飄揚河渠。
爾後夏時鳴遣來兩輛馬車,目送客人乘上第一輛,驅向杭州城下榻的旅店後,再坐另一輛返回自宅。
甫入大門,尚未邁過二門,即聞陣陣沉喝,以及揮舞破空之聲,該為爹親與陵叔實戰對練,人不是在龍曜堂內,便是在堂外的空地。
走進二門時,遮擋太陽的浮雲飄離,陽光灑落,彷若天降金龍,曜堂生輝。
空地無人,說明爹親在室內,夏時鳴抿了抿唇,推門而入。
「爹親、陵叔,午安。」少年郎行禮問候。
龍曜堂是練武的大堂,堂中央砌階而陷,為演武所用,四邊陳列十八般兵器,進門正對的那面牆上,掛著歷代夏家之主的肖像及卜字拐,一共七幅六雙。
兒子來了,夏進便向季陵道:「休息一會兒。」放下雙拐,接過僕役遞上的茶水毛巾,潤口擦汗,「吃過飯了嗎?」夏時鳴搖搖頭。
「那正好,趁灶房煮好你的午飯前,活動活動筋骨。」夏進落坐一旁的椅子,享用薄如書頁,剛出爐的雲片糕,「老陵,下手別太重。」
「那樣就沒意義了。」季陵手拿鐵鐧,神情嚴肅。
他平時就是這張別人欠他八百貫錢的表情,夏時鳴此刻卻越看越心虛,取出隨身雙拐,擺好架勢,含含糊糊地道:「陵叔,請賜教。」
抱拳回禮後,兩斤重、三尺長的四棱鐵鐧霍霍欺近!
鐵鐧與長劍橫刀差不多長,重量卻是它們的兩倍以上,揮揚之間不失靈巧,然又虎虎生風,打在身上肯定內傷吐血。見鐵鐧來勢洶洶,夏時鳴迅速拉遠,遊走鐵鐧所及的邊緣,不與之硬碰。
「霍!」鐵鐧一記橫劈,夏時鳴後撤半步,閃過這一擊,但季陵雙目一凝,招式未老,左腳速速踏前,發力一躍的同時朝右轉了一圈,蓄滿剛勁的鐧身對準前人側顱!
饒是夏時鳴趕忙舉臂格擋,鐵鐧仍力透拐棍手臂,直入顱腦,打得人頭暈目眩,未及恢復,烏黑的鐧身再次迫至眉睫!
下意識曲臂護在身前,「叩!」鐵鐧與木棍互擊,聲響不大,卻令棍下人踉蹌後倒,滾了一個筋斗。
「這麼快就沒力啦?」坐得老遠的夏進嘲諷:「灶房那邊米都還沒洗好呢!」
明知爹親使的是激將法,夏時鳴依舊騰地跳起,「陵叔,失禮了。」不待人回話,奔前搶攻。
他靠得極近,一連串的近身快打攻得季陵措手不及,暫時落了下風,鐵鐧守在身側,叩叩哆哆地防住拐棍的每一下敲擊,靜覓空檔,伺機還擊對手。
「哆!」又再擋下一擊後,季陵左腳一退,右手鐵鐧向前一掃,是次夏時鳴不躲不避,沉膝下閃後,欺至與敵半臂之距,左棍掄往側腹!
鐵鐧即時回防,豈料此乃虛招,緊接著右棍上竄,勾向季陵下顎!
「噗!」夏時鳴氣一岔,連連退了十來步,揉著胸口喘了好半晌,才緩過氣來。
遠邊的季陵放下腳,道:「鳴少爺,莫忘了屬下猶有腳。」
熟悉的聲音自龍曜堂的彼方傳來:「子謐,你若是不懂自身優勢在哪兒,今天就甭吃飯了。」
優勢?夏時鳴定下心神,仔細思索。
再度踏出右足,他猶然貼身快攻,不同的是,閃電般的十多回對招後,夏時鳴故現空門,誘使季陵直鐧一砸!「咭!」地板的石磚被砸得四分五裂,若非夏時鳴即時後跳,定然頭破血流!
鐵鐧甫離地,雙拐旋又迫近,咔咔叩叩四下來回,第五下拐棍突破防守,甩中面門!
「霍──」季陵忍住鈍痛,舉鐧一撩,又給對手逃走,他緊追其後,縱身躍起,鐵鐧對著腦勺當頭直下,然則夏時鳴早有所料,急停後反向一蹬,蹬至季陵背後,欲旋棍擊腰,卻被人反持鐵鐧架住,此擊不中,夏時鳴立時後退,季陵復追來。
兩人一邊打,一邊走,身距忽遠忽近,夏時鳴一招得手後,便會慢下拳腳,引誘鐵鐧出招,他再掐準時機閃避,來往數回合後,季陵攻勢雖多,卻難命中對方,反觀夏時鳴屢屢破防,不只臉面,季陵的臂膀腰腿亦吃了不下二十棍,渾身犯疼。
鐵鐧的殺傷力比尋常棍棒來得大,還能使用戳刺等類似刀劍的招式,是介於銳器與鈍器的兵刃,然則加倍的重量是優點亦為缺點,雖能給予對手重擊,卻也要有一定的體力運使,若久攻不下,戰況陷入膠著,持兵者時常後繼無力,耗盡體能而敗。
季陵瞧出他的策略,斂眉稍思後,腳下步伐驟快,瞬間奔至夏時鳴跟前,先是撥開襲面的拐棍,再發力猛刺,杵中人的小腹,夏時鳴應力而撤,鐵鐧又來!他連忙側身一滾,「哐啷!」鐵鐧砸爛一排兵器架,架上的刀槍劍棍掉落一地。
「咭!」夏時鳴一個後翻,又一塊地磚碎得稀爛。
「喳!」一鐧打至木柱,震得梁上積灰如霜雪飄落。
「叩啦!」鐵鐧緊逼不捨,壞了一張椅子。
季陵陡地加快攻擊,欲在體力告罄前擊敗對手,這幾下兔起鶻落,兩人所到之處,無不裂磚爛木,碎屑四噴,夏時鳴更是無暇反擊,只得匆匆避走。
「嘿!」夏時鳴身一騰,撲向爹親喝茶小憩的桌椅,按桌一翻,身後的鐵鐧亦挾風攻至!
「咿──」、「咔咭!」木桌旁移,鐧身重重砸地。
夏進仍安閒地呷茶食糕,惟右腳勾著一只桌腳。
「霍──」鐧端堪堪削過夏時鳴的鼻頭,削得人鼻子熱辣生疼,他身形稍滯,季陵反手再揮!
「叩!」危急時刻,夏時鳴不退反進,右手拐棍硬扛重若千鈞的鐵鐧,左棍旋長,停在季陵的喉頭前。
「陵叔呼……呼……承讓了。」夏時鳴汗流浹背,氣喘吁吁。
沉重的鐵鐧巧轉,季陵倒鐧抱拳,躬身道:「比之上次交手……呼……鳴少爺進步許多。」
「老陵你太恭維他了!假使是正式交戰,他早被揍得滿頭包。」夏進叫道。
「爹親說得是。」垂在身側的右臂隱隱發顫,幾乎拿不穩拐棍,若非季陵先同夏進拆招,此後夏時鳴又採取迂迴的打法,消耗他的體力,欲架住最末由上揮下的鐵鐧,拉傷筋肉尚算輕了,手臂骨折是正常。思及茲,夏時鳴難得謙遜:「子謐本佔上風,仍得一而再,再而三地改變戰術,方勉強取勝。」
「你呀!」夏進拿著茶杯步來,「腦筋動得算快,卻老是橫衝直撞的,不知是隨誰的性子?」
夏時鳴低下頭,罕見地沒有回嘴,倒是季陵聽得這句話,兩眼直盯著自家總舵主瞧。
「好啦,你特地進來,所為何事?」夏進又拈一塊雲片糕吃下。
「呃……其實孩兒是來找陵叔的……」夏時鳴氣是喘夠了,講話卻仍吞吞吐吐:「我想請問陵叔,軒哥他們……還在季家的祠堂嗎?」季陵頗有深意地看向少主:「是。」
夏時鳴道:「他們是因為我的命令,一同前去晷丘島,不是他們的錯……」「沒有保護好鳴少爺,即是大錯特錯。」季陵冷冷回應:「季家在禹航會底下做事歷經六代,是主家之外,會中最有聲望的家族,地位可謂舉足輕重,但季家從不因此得意,更不敢自視高人一等。倘若我那五個孩子沒能力捧這碗飯,這碗飯不吃也罷。」
聽他言詞,竟有讓季南軒五人退會之意,嚇得夏時鳴瞪大了眼:「陵叔,您聽我解釋……」
夏進道:「老陵,你也累了,去歇會兒吧!」季陵亦不多作停留,默然告退。
夏時鳴立刻轉過頭來,情緒激動:「爹親,我知你怪我魯莽,思慮不周,但萬萬不能讓軒哥他們退出禹航會……」「為甚麼不能?」夏進挑眉:「假若咱家留不住人,放人走又何妨?說不準這對他們才是好的。」
「怎麼會好呢?季家世代效力禹航會,軒哥他們亦以此為己任……」見兒子遲遲點不通,夏進索性挑明:「你有沒有想過,假如今次受傷的人不是你,是小軒他們其中之一,甚至是死了幾個,我該怎麼向你陵叔交代?」
「我……」夏時鳴張著嘴,顫著唇,好半天說不出話。
「我自幼便教導你,禹航會好似一艘大船,小至榫卯大至帆桅,缺一不可,而你我便是這艘大船的舵,左右船隻的沉浮,哪怕僅偏離航線一分,撞裂一小片船板,這艘大船就不再完整,縱使之後補上那片船板,也非原先的船板。」父親語重心長:「這就是為何禹航會甚少涉足江湖事,江湖一如商場,掌舵者的一舉一動、一思一念,牽動禹航會上下數千人,稍有失策便是後悔莫及,差別在於一個賠的是錢,一個賠的是命。」
勻稱的十指攥緊,夏時鳴咬唇無話。
「晷丘島之事,希望是我最後一次瞧見你的莽撞。」言罷,夏進跨過門檻離去。
抬頭望著牆上歷代祖宗的肖像,夏時鳴怔然出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