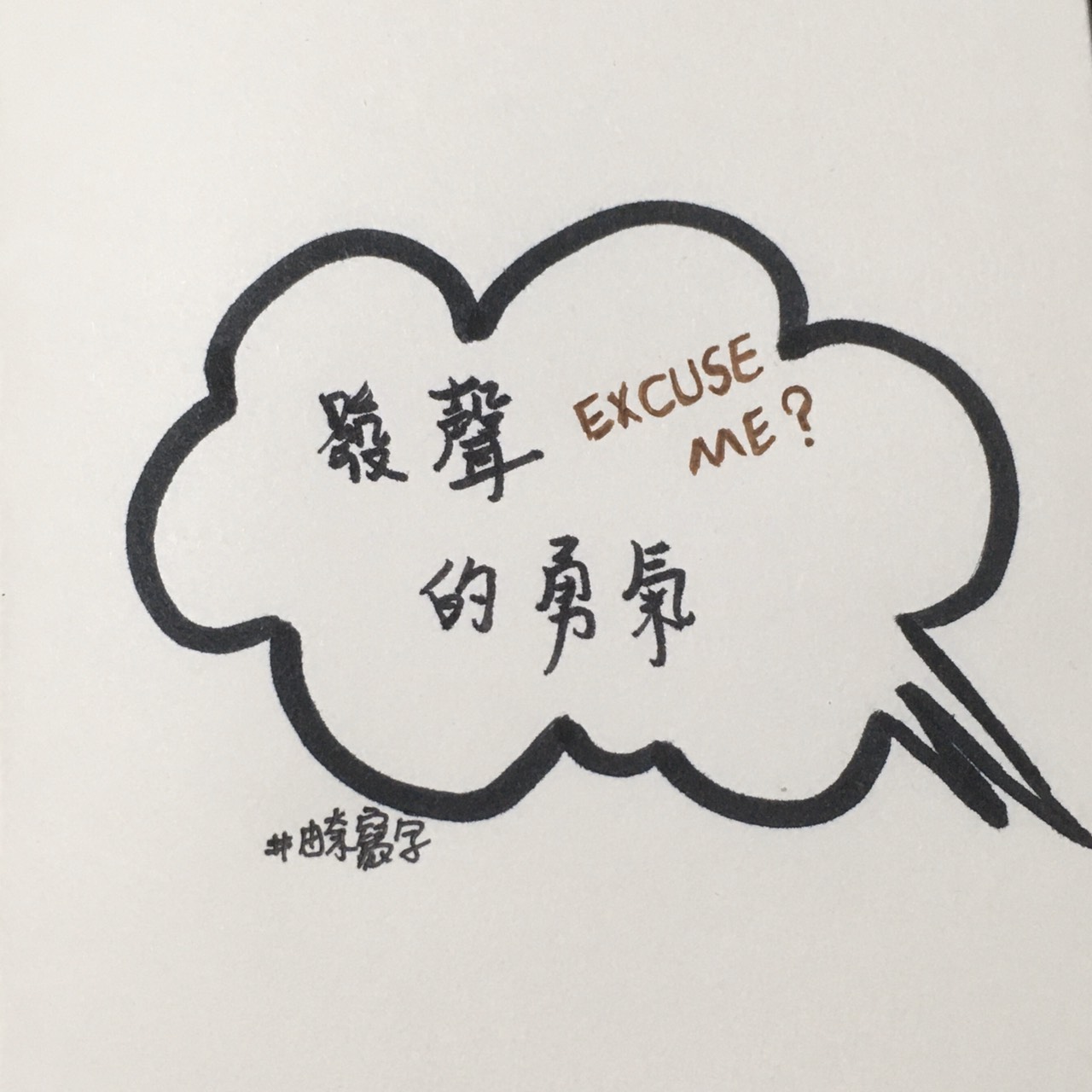說明:《斬畜隊》是《對話錄》式的系列,探討議題是「恐懼」。
【即時】義巡會今日於台北舉辦大規模繞境活動「義民巡守總會」今日下午一時開始,分四路於台北市區進行繞境遊行活動,預計活動將於晚間十時前結束。因交通管制區域廣大,台北市警局交通大隊請用路人改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或避免不必要的外出活動。(即時中心)
「這根本是閱兵。」
陳難得認同社內長官的下標。這就是閱兵,斬畜隊囂張到搞大閱兵了。一個個十乘十人的方塊,塊塊都對準著正前方的方塊,在忠孝東路上緩慢前移;加上兩旁的「緩衝空間」,就佔去了往西的所有車道。本來路權是不能這樣申請的,但他們就是申請到了。
也是十分鐘前,陳才知道這種人肉方塊叫「方隊」。
是黃告訴她的。陳幸運的坐上了黃的「專車」,所以不用在路上跟著隊伍走。這次斬畜隊沒設媒體專車或專區,他們高層似乎突然放棄了公關,媒體要來就來,不來就算了,態度意外冷漠。一些媒體在討論這改變是否另有深意。
黃是在出發點的路邊揀到了陳,就讓陳上了車。
「我現在是糾察大隊的中隊長,要維持路線秩序,所以不能用走的。」黃解釋自己的特權。
她的車,像選舉用的宣傳車,三噸半小貨車改裝的,車後斗是開放式,左右兩側裝了高高的廣告板,女生站上去就只能探出頭。板上沒有任何廣告,是全白的。幾支車載喇叭在那瘋狂播送台語歌謠,偶爾穿插一些獨派口號。
陳知道這種車的暱稱是「戰車」。她聽立委說過。身為政治線記者,不知道這種事就太好笑了。
「糾察隊?」陳直覺的反問。
「我現在是糾察大隊的中隊長,這是我們新設的單位。因為我們人太多了。」
「什麼太多了?」車子正放送亢奮的進行曲,陳沒聽清黃的回答。
「人變得太多了!所以要有糾察隊來管一管!」黃大吼,然後扯一扯金黃色的糾察臂章。就像小學生糾察隊,她左手上臂也有那麼一圈,上面倒不是繡「糾察隊」,而是「團結」二字,紅色的楷體。金底紅字,老派配色。
「所以妳現在負責什麼?」陳問。
「就是糾察隊呀!有不乖的就記下來!」黃左顧右盼,好像在抓不乖的小朋友,其實是種搭敞蓬車的快意。
「我們就是憲兵啦!」黃身旁一個男隊員轉身大吼:「就是憲兵!抓那些有問題的一般兵!」
「什麼?」陳沒聽懂,才想追問,黃就堵上一句:「反正我們就是維持秩序的人啦!」
陳跟著的這路隊伍,是從忠孝東路尾段的南港出發。斬畜隊分成四路,分別由台北盆地東南西北的集結點出發,往總統府前會合。這路隊最前段,就是一塊塊的方隊,隊伍中段,看來是一些「比較不重要」的隊員,雖然也穿制服,但不成隊形的零碎跟著。
最後面一段,應該是家屬親友團,或是一些喜歡斬畜隊的民眾。那邊已是單純在逛大街。陳跑過的集會遊行場合不少,但這麼詭異的遊行很少見。前面像是在閱兵,後面像是跨年封街的雜亂人潮。
「你們今天有多少人?」陳問。
「妳問這是要寫的嗎?正確數據要去問聯絡人喔!」黃答。
「不會寫,只是我想知道而已!」陳大吼回應,因車載喇叭又開始帶口號。
「最前面這邊走方隊的,是一個常備聯隊,有兩千五百人,分成二十五個中隊來走。後面沒有分隊,一長串接著走的,是一個後備聯隊,也是兩千五百人。最後面的是家屬或認同本會的自由參加者,大概也有一兩萬人吧。」
陳聽的不清楚:「所以總共是多少?一兩萬人?」
「對!我們這邊的家屬比較多,其他西北南出發的遊行隊伍是從中南部上來的,家屬會比較少!」
車載喇叭開始放歌了。曲調是原住民歌曲,歌詞卻又像是軍歌。
「這什麼歌?」陳問。
黃答:「我們都叫這首歌是萬沙浪。哈哈。聽說原來是國軍的軍歌,但是後來被禁唱了,因為歌詞太負面。」
「是嗎?他們在唱什麼榴槤?」
「喝完了這杯酒莫再留戀啦!」黃配著曲,靠近陳的耳朵唱:「你聽聽在山的那一頭,敵人的哭聲又響起,趁著夜色呀向前衝……」黃肩上的無線電開關卡答一聲,自動跳開,傳出磁性的命令:
「呼叫九一九一中隊長。九一九一中隊長。」
黃伸出一指壓下按鈕,轉頭對著收音麥大喊:「九一九一中隊長收到。」
無線電訊息雖雜,但在車載喇叭聲線下卻意外清楚:「九一九一中隊長請至後備一大隊,乙式狀況,乙式狀況。」
「九一九一中隊長收到。」黃彎腰向這車的司機下令,這台「戰車」就來個大迴轉,從路的中央緩衝空間帶,逆向往隊伍後方急駛而去。
「什麼狀況?」陳問。
「後面有點狀況,我要去看一下。」黃隨便回答。
「所以你們是九一一或一一九喔?」陳追問。
「九一一?」黃反而不解。
「就是救護隊之類的啊,剛剛不是呼叫什麼九一一?」
黃想了一下,突然大笑:「是糾察一中隊,簡稱糾一啦!哈哈。」
車很快抵達了「事故現場」。隊伍仍在行進,但一些戴著團結臂章的糾察隊員,似乎和一小批沒有臂章,穿著斬畜隊制服的阿伯,起了衝突。這群人站在路旁吵,其他遊行者雖略過他們徐徐前行,卻也多半會轉頭看上幾眼。
陳很驚訝。這好像是她首次親眼看到有斬畜隊隊員「不太合群」的。或說是不太聽命令。她分不出這些人的階級高低,但有臂章的,應該是比制服阿伯要高上一截才是,但他們壓不住這些阿伯,很可能是因為有臂章的怎麼看都像是普通大學生。
「注意。」黃跳下車大喊,「我是糾一中隊中隊長。什麼狀況?」
幾個臂章人開始告狀。或說是「報告」,黃應該是他們的上司。陳發現那些阿伯似乎頗在意黃的抵達。沒開口,反而退了幾步,在一旁看「大學生們」告狀。
因為車載喇叭關掉了,所以陳可以聽到那些臂章人對黃的報告內容,但那似乎不是人話,因為陳聽不懂。一整個不懂。連想透過支字片語來了解大概狀況也沒辦法。專業術語過多。
陳乾脆跳下了車,依記者本能向阿伯提問:「現在是什麼狀況?」
那阿伯一時反應不過來。因為陳沒有制服,卻又是從宣傳車跳下來的。
「報告長官,沒有什麼事啊,就小朋友對我們有意見。」不痛不癢,又客客氣氣。
「什麼意見?」
「小朋友說我們不能拿十手出來對著那些阿共啊!」陳聽不懂關鍵字,但順者阿伯手指方向,陳看到路邊民眾裡有幾個穿紅衣,舉五星旗的。
哦。
衝突場面,這個有新聞價值了。這附近好像沒有媒體,不知道有沒有民眾拍到第一現場。陳想去找其他中立百姓提問,黃就已聽完報告,轉過身來。
黃發現陳下了車,還剛結束對「阿伯」的訪談,嚴肅表情一閃而過,卻又看到陳在那裝無辜,想掩蓋自己的「非法採訪」,就笑了。
「他們和路旁的統派起了衝突」,黃講了和阿伯類似的故事,「總隊部認為這種狀況沒有必要。」
「這我可以寫嗎?」對黃的「寬大處理」,陳也友善回應。
「當然可以。有我在就可以。」黃講完,笑了,陳也笑了,但兩旁隊員都不知她們的笑點為何。
那統派只有三個人,還躲在稀疏的旁觀人群後叫囂。斬畜隊眾人只是看著,沒有什麼反應了。大概是因為黃在這裡。
遊行隊伍依然緩緩往前蠕動,起衝突的隊員們留在原地,以黃為圓心,成一個扇形。這些人若不是看著黃,就是盯著那些統派。沉默的流動與靜止。
黃在原地建立一個結界,彷彿在這,只有她能做些什麼。但黃也只是盯著那些統派而已。
「妳看起來有點可怕。有霸氣。」陳小聲說。
「我知道。因為我自己也很怕。」黃說。她還是直盯著那些統派。
那邊才三個人而已。到底是在看什麼?
「是害怕嗎?」陳突然想起之前兩人的嘴砲,「還是恐懼?」
「害怕。」黃沒有多說,轉頭大聲下令:「剛才發生的事情不會有記錄和懲處,有任何後續問題都由我,糾一中隊長,具結處理。請各位回到所屬隊伍跟上。」
不論有無臂章,各老少隊員都是手刀一揮,敬禮,屁字不留的離開,混入隊遊行隊伍中。也一兩分鐘,就分辨不出誰是誰了。
陳問:「所以現在就是我和妳的事了嗎?」
黃漠然:「什麼妳和我?」
陳問:「就是我要不要發這條,妳要不要處理的事嗎?」
黃笑:「這種小事,媒體要報,也是在我可以處理的範圍之內。我剛才是在看有沒有發生衝突的跡象,如果有就麻煩了。」
「可是,」陳更不懂了,「如果有衝突,不是更會造成你們之前說的那種恐懼的效果嗎?」
「的確是這樣,」黃看現場沒其他狀況,就爬回「戰車」,也拉陳上來,「所以我們並不在意這種衝突的本身,而是這種衝突會不會突然引爆什麼更進一步的狀況。」黃下令要車子留在原地,看來是要做現場的制高點,能監視那些統派的舉動。
但黃在分心下令的時候,似乎講了前後矛盾的說法。陳問:「我不太懂,所以你們到底在意什麼阿?是怕真的打起來嗎?」
黃這才發現可能多講出了什麼,於是整理自己的想法:「我的意思是,的確就像妳講的,這五六個人的衝突事件還好處理,頂多媒體拍一拍,但我擔心會捲進許多隊員,造成多打一,那時就不妙了。」
陳認為這說法合理,但不夠力:「就算多打一,也還是有製造恐懼的效果啊,你們弄那麼多人擺個全套的閱兵陣式,不就是想要嚇人嗎?」
黃回答不出,又只是盯著那些統派瞧。那三個舉五星旗的,居然就在地上坐著休息,像是鬧夠這一回,等著下一回。黃又看了好一陣子,才補上:「妳講的沒錯。打成一團,會製造更多的恐懼。」
「所以剛剛妳的判斷有錯嗎?」
「不是我的判斷,是上面的命令。」她側身靠近陳,低聲說:「上面今天早上對所有幹部下命令,要制止肢體衝突,沒有講理由。」
「所以妳只是服從命令?」
「沒那麼簡單。」黃搖搖頭,笑了。「我自己認為,他們這是在製造另一種恐懼。」
「我不懂耶。」陳沒想得太深。
「我分析給妳聽。」可能是會講到什麼機密的事,黃整個人蹲下來,躲到「戰車」廣告背板的後頭,陳也只能配合蹲下。
「他們沒有對基層的隊員下令,而是對幹部下令,而且要幹部不能對基層講。這到底是為什麼?因為這和過去的作風不太一樣。」
「嗯。」
「我們過去是若發生暴力衝突,就放著讓外界批評,總隊部只是該賠的錢賠一賠,反正有這種形象,只會製造更大的恐懼。」
「對。」
「但今天這個繞境,卻不一樣。上面要幹部制止暴力,但又沒有對基層公開宣示,這會造成什麼狀況呢?」
「基層的人像過去一樣衝了,然後幹部去攔嗎?」
「對,就像妳剛剛看到的那樣。我想基層隊員一定很疑惑,因為過去沒有這種規定,怎麼今天會有。他們是不至於和幹部起另一波衝突,就是會覺得很怪,很奇怪。」
「嗯,剛剛看他們的臉,的確有這種感覺。他們也不是生氣,就是覺得怎麼會被攔下來。」
「對啊,但這也製造了幹部和隊員的矛盾。那為什麼不公開講呢?我認為有一個很表面的原因,就是怕公開宣導,會被統派的人知道,那他們就不會怕我們,可能會整批來挑釁。」
「有道理。」
「雖然有道理,但這種說法很表面。以我們今天的人數,根本就不怕統派挑釁,就算來幾百人也不怕,因為光是這一路線,就有一個常備聯隊,兩千五百人的精銳。」
「所以呢?」
「所以我認為總隊部下令幹部要制止衝突,有其他的理由。」
陳的心縮了一下。黃居然有這種反思。記得黃似乎沒真正質疑過領導人物。或許有,上次碰面時,有那一絲絲的感覺,但沒有那麼明顯。
黃說明自己的想法:「我認為,應該這樣講,這還是有不同層次的考量。先講淺一點的層次。總隊部下這個命令,是要我們控制部隊,保持穩定,……」
部隊。雖然斬畜隊就像是軍隊,但陳似乎是聽黃第一次用「部隊」這個詞,這詞聽來很重。很沉重。
黃說:「穩定的理由,是他們有更重要的任務要執行。這是不公開的,但也不見得是真正的祕密,因為大家也都清楚,今天說是繞境遊行,但其實就是閱兵,講更難聽一點,就是朝總統府進軍了。」
「對。很多媒體都是這樣切入的。雖然沒有明講。」
「我們是以全部的人力往行政中樞推進,雖然只攜帶十手和一些輕裝,但真要發生大規模衝突,是的確有可能的。出發前就算沒有命令,但是自己人都知道,完整的編制人力都在現場,只要命令下來,大概一個小時內,就可以從義巡會轉變回斬畜隊了。」
「轉變回?不是一直都是斬畜隊嗎?」
「嗯,這樣講也沒錯,反正要大家進入狀況,是很快的。但過去我們都是說,敵不動,我不動,但今天卻主動擺出這個陣式,到底是為什麼?」
陳被問倒,連忙找聽來的答案:「我看一些名嘴說,你們在沒有發生大事的狀況下,突然辦這個活動,是要對總統施壓,放鬆對你們的管制。當然也有名嘴說,是你們要政變吧?」
「的確,都有可能,但我們自己幹部也都不知道。我們的確在轉變,往我們更不清楚的方向變了。應該是這樣說,過去我們自己人是一整塊的,會讓外面的人感覺到恐懼。但我覺得,最近我們自己的高層,總隊部那邊,也開始讓中間幹部和基層的隊員,產生一種恐懼,或說是很多元的恐懼。」
「嗯,什麼意思呢?」
「我們身在其中,感受很明顯。過去我們真的是,當對手感到恐懼的時候,我們就一無所懼。不過某天開始,我覺得我們越來越強大了,有點反過來,好像是因為我們一無所懼,所以對手開始感到恐懼。接下來這種一無所懼有點失控,隊員向外威嚇,差不多就是從失控的那瞬間開始,總隊部改變了策略。」
「怎麼改變呢?」
「像是兩派在鬥爭,又像是有人分別扮黑臉和白臉。比如一邊改名叫義巡會,搞一些小貓小狗愛心認養活動,但一方面又推出這種大動員、大閱兵。我們自己也不清楚要往什麼方向發展,就是命令下來,就遵守,就調動,就接新的職位。一開始就算很有信心,一無所懼,最後也會越來越茫然。」
「所以說,所以可以這樣說,你們的長官,最高階的那些大頭,現在不只要讓統派因為無知而感到恐懼,現在也要讓你們因為無知而感到恐懼嗎?」
「對,有這個味道,但我們現在又不只像是統派那種無知。他們是什麼都沒做,什麼都不會的無知,而我們是被命令推著一直動,一直被塞得滿滿的,一直有任務,就一直沒辦法思考。因為沒辦法思考,等到突然面對一個和過去不同的狀況,就會害怕,或是恐懼。」
「連想的機會都沒有。」
「對,連想的機會都沒有,或是他讓你想,卻想不深。我好像之前和妳討論過,無知和幻想太多的恐懼,都是一樣的吧。到了現在,我覺得好像那只是一種情緒,就是怕。害怕。害怕和恐懼是沒有差別的。」
「嗯,我也是這樣覺得,只是你們的上課教材叫你們去區分兩者嘛。我很討厭這種學院派做法,我第一次聽妳講,我就覺得這種分類法很無聊,鐵定是教授搞出來要考試的。恐懼和害怕根本就沒什麼差啊,我可以生理上對某個東西感到害怕,也可以想一想,想到它而感到恐懼。對象就是那一個,但那種不喜歡、很排斥的感受,本來就是很多元的,也沒必要去分。」陳難得講這麼長一串,像是把卡了一年多的心理話一次噴完。有點亂就是。
「妳講的有道理,只是我的官方身分無法公開接受,我還當過新聞聯絡人呢!」她笑了著補充:「反正怕就是怕,他們就是要你怕,哪有分這麼多。」
「怕就是一種手段。」陳想起了過去的討論。
「怕也可以是目的,也可以是手段,但分這個對一般人來說也沒啥意義。我現在比較在乎的,是這個怕的後面,到底是善意,還是惡意。我分不出來,這才是讓我感到痛苦的地方。」
「痛苦啊。」
「就算是總隊部今天突然下令展開最終行動,或是決定去攻佔政府機關或交通節點之類的,我也會想知道,這個命令背後是善意或惡意,如果不知道這件事,我的確會害怕,不是怕死,被怕抓,而是怕做錯事。做一件自己不認同的事。」
「最終行動?」
「就是去把統派清除掉。但我也不知道詳細內容是什麼,要等戰術手板發下來才知道。戰術手板就是一個像筆電包的包包,裡面有任務執行計劃。我從沒看過真正的。」
「聽不懂。」
「當然,」黃突然笑出來,「當然聽不懂。正常人都聽不懂。反正啊,就是一種不懂疊著另一種不懂。然後就會害怕,會恐懼,會討厭這種感覺。」
「但妳還是沒有離開。雖然開始討厭了。」
「我有一種被控制的感覺。被控制,離不開了。」
「或許害怕或恐懼的根源,就是自己被控制了,或是自己不能控制一切。」
「我正想要講類似的話耶。」
「這代表我們達成共識了嗎?」
「嗯,也許。不過我們兩個幹嘛要在這邊縮成一小球?」黃發現了有趣的現實。
「感覺像兩個小女生在講鬼故事。」
「我們都不是小女生了。」
「對啊。不過妳還是年輕一點。」
黃伸展四肢,站起來,探頭出車外。發現經過的人群已變成花花綠綠、熱熱鬧鬧的家屬隊伍。
陳也站了起來,與黃併排,往車外望。有些遊行民眾笑著對陳揮揮手中的小旗子。那金色旗面只寫了一個紅色的「義」字。雖然是基於錯認,但陳也對他們輕輕揮手致意,然後側頭與黃說:
「統派的還在。移到那邊的巷子口去了。」
「對。沒關係。巷子那邊幾個穿便服的小男生,是我們快速打擊聯隊的人。」
【後記】
斬畜隊是仿《對話錄》的文體,然而真正讀過柏拉圖《對話錄》的朋友,會發現兩者還是有明顯的差別,但這種差異不影響我想要說明的本旨。在這個系列裡,我並未打算呈現哲學家對於恐懼概念的細膩處理,而是用兩個不懂哲學方法的角色,從他們各自的生命立場與經驗出發,去處理一個超出她們思辨能力的主題。
這處理方法當然無法讓正統哲學研究者滿意,類小說的寫法或許更會引來文學批評者的不滿,但我認為這種粗糙是不可避免的現實,因為當平凡人面對一種極端主義(極右或法西斯)的思維系統時,總是混亂而脆弱的,這也是極端主義能生存甚至壯大的原因。
這兩位主角到最後仍未從恐懼中脫逃,也無法取得什麼進一步的力量,而是無奈的接受了自身能力有限的事實,我認為這結局對於普通讀者來說,會比告訴你「恐懼」的定義和發展可能性要來得有意義。處理一個哲學概念,不見得會讓你理解這個哲學概念,但透過這個思考過程,能幫助你進一步反思你的價值觀。
斬畜隊在現實的台灣沒有存在的空間,但類似想法隨時會成為一種社會意念,並且滲入我們對於社會政策的討論。當我們面對這種手段目的明確,且充滿鬥志的思潮時,我們能逃出其設定的歷史發展線性嗎?
如果你覺得有必要反對這種想法,那你得比他們更積極才行。
我原本打算用五篇來處理這個主題,但基於進一步的考量(在將來可能會利用這故事的世界觀另開專案),就以四篇作結。接續本系列的仍是政治批判議題,應該會是一個關於右派理論的系列。
連載回顧:
封面圖片:bryan… @flickr (CC BY-SA 2.0)
編輯:宅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