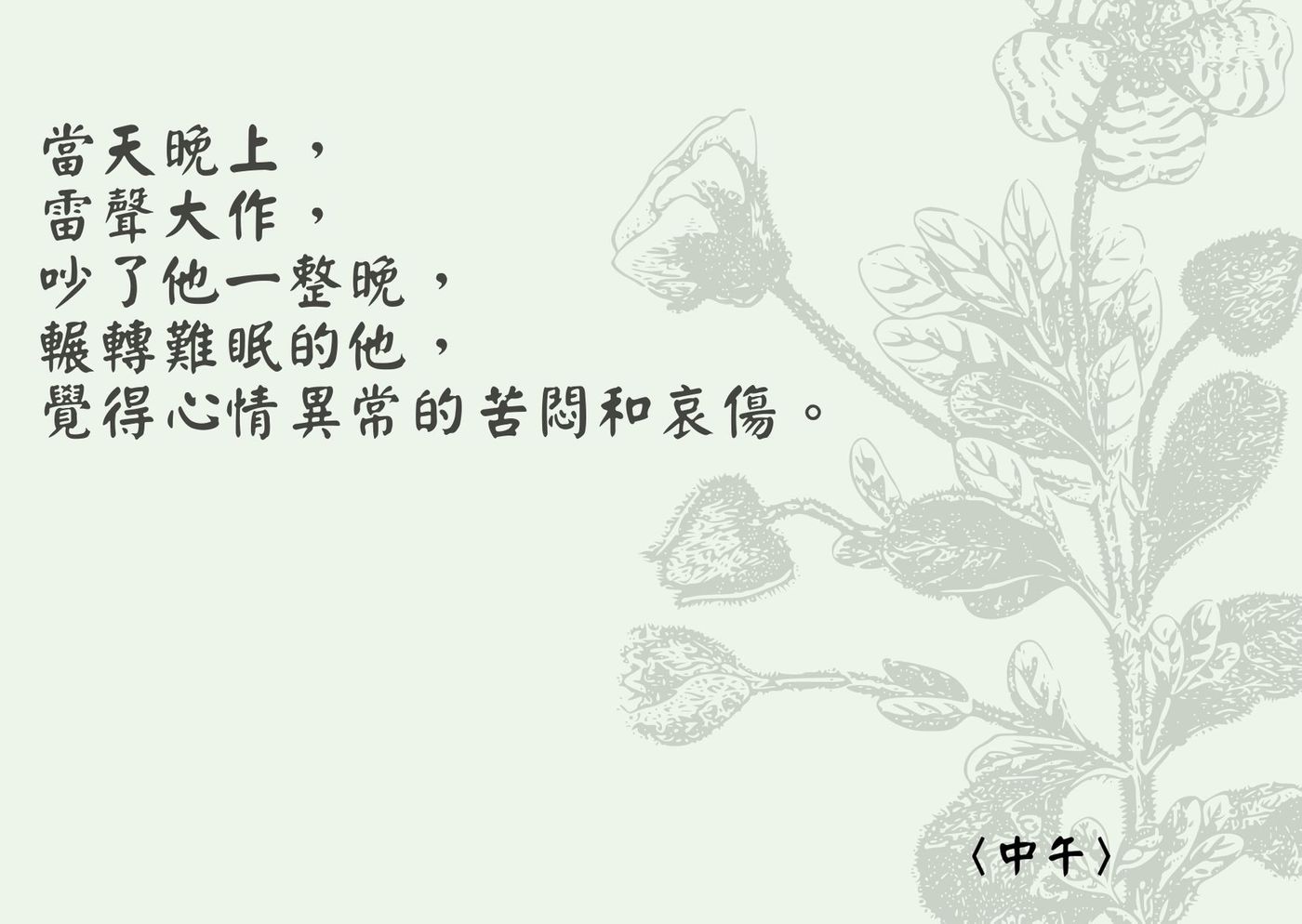老人打算在結束這段副歌後不顧一切立馬狂奔離去、不顧一切想找個安靜的地方歇息,把所有不願同別人展示的恐懼與懦弱深埋在那裡。但他還是回過頭,禁不住將視線往上移去想要看清‧‧‧‧‧‧
吹狗螺在民間意味的是什麼,她其實並不很願意真正相信,但在這黑夜時分,每個閃動過去的身形都彷彿鬼影幢幢。她拉開本應帶去修繕幾番的車門,幸虧裡頭還是令人心安的發出「登──登──」聲響──儘管提示音原本被設計的用途應該與這種心理沒有干係。霧氣在車窗上凝結了好一層厚,坐在其中有如身處在謎樣世界,看不清下一步、危險、同時動人異常。她一言不發地啟動引擎,以掩飾節律點的跳動速度。
有什麼東西把女子連人帶椅、側門一同拽了出去。
老毛病又犯了,他在屋簷下乾抽著從廢棄超商掘出來的菸時,除了還記得要餵飽在家門口徘徊不止的流浪狗外,竟似就剩這份思緒在腦中縈繞。身子骨到了這把年紀,每天能在乎的事也許只剩下清晨倚在這兒,看住一天之初依然冉冉升起的微光罷,那也是如今還遵循舊日常運轉的秩序之一。有時人生不過如此,只需假裝自己現在也過得很好,什麼困難就都過去了啊,可今天卻還是在下雨,霧濛濛的,街上還斜停著一邊沒門的車,頭卡死在騎樓正中。他嘆出一縷輕煙呼應,眉宇間的陷落隨著心緒而更加明顯了。致那逝去的美好,他想。幸好下的,不再是以前那麼毒的雨,出外也不至於繼續受限於防護衣,只是還需要戴著防毒面具以防萬一,再過不久就可以安享天年了──
忽然覺著額頭被東西給滴到一兩下,不是雨滴,摸起來有種黏膩與溫熱。
「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時起有時落──」老先生向人孔蓋啐出萎縮的菸蒂,吹的口哨是這段素日裡他最摯愛的節奏。這次有什麼落在了他面前,這幢大廈廢墟的後門前。他費了些力氣讓自己日漸衰老的軀體蹲下,沾了點在食指尖嗅聞,很快就明白了金屬氣味代表的涵義。他又撫摸額頭上的血滴,開始不住地發抖。那聲響仍在滴答、滴答‧‧‧‧‧‧
只見老先生的臂膀在激烈顫抖著,僅存的數顆牙在嘴裡瘋狂打顫卻碰不出格格作響的驚駭,格子褲的臀部織料則是沒有盡頭地開始滲漏出令人作嘔的黃棕色與撲鼻惡臭,自從頓悟那一刻起就再也沒停過。
老人硬是忍住那股衝動,那股幾欲將吞在腹中的不堪字眼一股腦兒傾洩而出的衝動,並繼續吹著口哨以求壯膽,試圖緩解對血液的不適及暈眩感。他憑藉多年累積下來的人生經驗隱約感到事情並不像原以為「自然」。老人打算在結束這段副歌後不顧一切立馬狂奔離去、不顧一切想找個安靜的地方歇息,把所有不願同別人展示的恐懼與懦弱深埋在那裡。但他還是回過頭,禁不住將視線往上移去想要看清‧‧‧‧‧‧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拚──」
冷風刺骨,寒雨繼續下著,將接踵而至的還會是場腥風血雨。
他瘋了。可猛爆性的精神錯亂只持續一小段時間,就被心肌梗塞所帶來的結果取代了。
一雙濕漉且布滿歲月痕跡的手,環抱著他的遺體。而她仍綁著安全帶但已不成人形的身軀,從樓上染血的遮雨棚運下來後被送至法醫那裡躺著,感覺寂寞得很。方才從老人臉上摘下的防毒面具就在身旁,淚痕劃過了護目鏡起霧的白茫。裹著半透輕便雨衣的男人再也壓抑不住情緒,放開雙手跌坐在積水裡嘶啞地叫了出來,一聲聲乾咳像是要直至撕心裂肺般。如今早已不再是能夠縱容自己抽抽噎噎的年華,也並非能將生死哭哭啼啼看待的時代。其實男人很早以前就認清現實。只是當真正遇到時,沒有人有絲毫機會抵擋那種難受。
就算他是「阿澤」,那個身旁已經沒有任何事物能夠再失去的李澤清也罷。
【正式版】內容將繼續刊載於 成功青年第166期校刊《磊》。
文章追蹤/喜愛/收藏人數達五即解鎖【原始版】下一章節──自白。
「說好要一起去探望那些孩子的‧‧‧‧‧‧」
自白
「這裡沒有生者,連思想也一起葬去。希望的篝火幾近枯竭,只能在風中無力搖曳。」──《返校》
兩日後。十一月三日。
調閱自對嫌疑人李澤青﹝特災應對中心‧審訊室長﹞所進行的調查錄音資料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