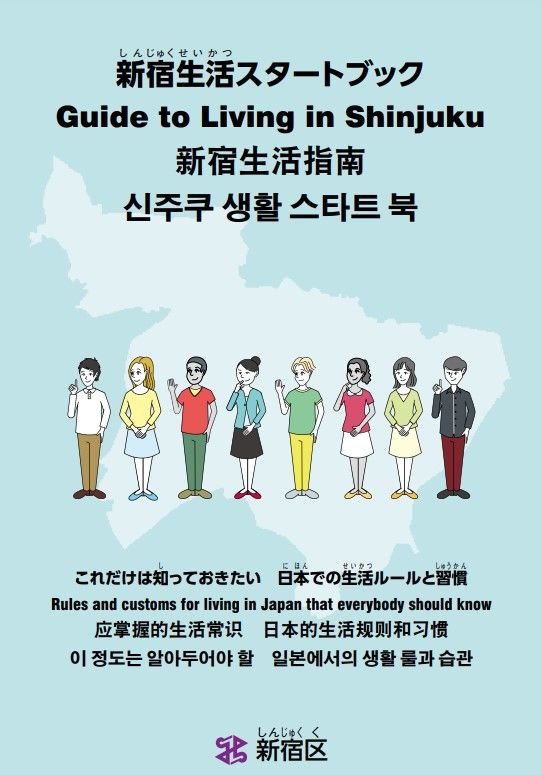有些對生活的盲點是到日本後才發現的。
例如自己對臺北其實所知甚少。生活了三年,大抵活動的範圍就是那些,探險挖掘的心不知何時被消磨掉了。甚至不曉得該去想念什麼,除了食物。跨年的時候,住在隔壁的德國室友曾說,要飛去臺灣一個禮拜。explore。他說。彷彿深入亞馬遜,充滿野性與冒險的字眼。怎麼我就沒想過要explore。
出國一方面是因為壓力而長久地對生活感到倦怠,一方面是面臨考研究所的岔點,強制性地為人生按下PAUSE鍵,想看看暫時離開法律系的環境後,內心會不會有一些什麼浮現出來。
花了一年培養自己的勇氣,姑且決定朝台文所前進。然而每當思及至此,內在的板塊仍然動搖得厲害。
基於一種偏見/欣羨(?),總以為接受西方教育體制的人們,對未來的輪廓會更有想法。然而我的徬徨也是他的徬徨,我的現實也是他的現實。嚴格而論,雖然程度或有不同,但看見不分國界與自己相同世代的年輕人,也都各自背負著彼此的煩惱,在理想的邊緣掙扎,與現實折衝,或是採擇中庸之道,自己的不安彷彿也沒有那麼不堪了。或許害怕,是相當自然的事情吧。
異國生活的神話不值得被信仰。生活不會單單因為環境改變而簇然嶄新。語言,文化,飲食,人際關係,思鄉。這些東西理所當然地可以預見,卻也不容易適應。生活的慣性深入肌髓,在調整步伐的過程,過往的鬼魂總是陰魂不散。直到半年過後,才感覺自己漸漸融入,理解了日本。
然而相較之下,在日本交換的一年,少去外在的壓力,確實多了許多餘裕,足以讓人感受到生活為何物。
每天散著長長的步到超市買菜,苛扣著幾十日圓的價差;回家的途中,遇見一隻在樹下午睡的貓,或是牆角邊沿盛放的櫻花;趁著放假的空檔,讓身心出一趟遠門。
除了偶爾的寂寞,大二大三盤旋好一陣子的死滅感已消失無蹤。
不會以喜愛來總結一年的日本經驗,但畢竟長居於此,到最後也產生了某種神祕的感情。
這一年,就是這樣一種感覺。
在過去從未抵達的異域,向著前所未有的生命,以開拓者之姿,一畝一畝開墾出自己的居場所。因為一件小事而氣急敗壞,或是說錯話而羞愧地想從地球消失。抱怨迭迭發生的不如意事,笑的時候用力笑,哭的時候大聲哭。然後好好吃飯,好好生活。有些瑕疵也無妨。居場所。只要回到屬於自己的地方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