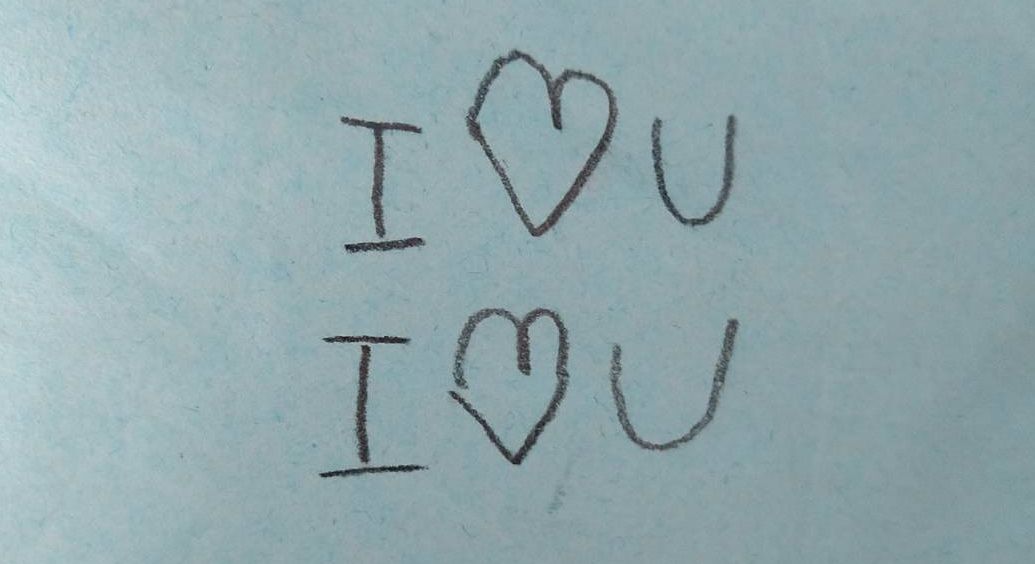1974年雨果獎的最佳短篇小說得主《從歐梅拉斯出走的人》(Ones Who Walk Away from Omelas)中,描繪一座名為歐梅拉斯的幸福小鎮,在那裡沒有階級、沒有戰爭、沒有族群衝突、沒有無謂的爭吵,只有無比的自在及逍遙。
只不過,在歐梅拉斯的某個地窖,有個沒有窗戶、上了鎖的房間,房內僅有的光線,是穿過佈滿蜘蛛網的窗戶、再透過房間木板的隙縫、裹著塵埃的微光,房裡除了生了鏽的水桶、發了霉的拖把之外,還有一個無辜的小孩。
他坐在有點潮濕的泥地上,對時間已經完全失去了知覺,他並不是出生就在這裡,他還記得陽光、還記得母親的聲音、還記得地窖外的歡笑和淚水,還會不時呼喊著:「拜託放我出去,我會聽話,拜託你們放我出去!」但每次,打開房門的只有送上食物跟水的人們,大人帶著小孩,如同校外教學般地來看這個悲慘的孩子,他們開了門後從來不說話,有時候還會踢他揍他要他閉嘴。久而久之,孩子不再哭喊,他安靜地、赤裸地坐在自己的糞便上,接受專屬於他的悲慘人生。
所有人都看過,所有人知道他在那裡,那些幸福快樂的人們,歐梅拉斯的所有人,都知道他在那裡,但沒有人在意。
因為他們認定了,這是一種交換。
他們的快樂、他們城市的美好、他們溫馨的友誼、他們子女的健康,甚至是他們的收成跟外頭的好天氣,都完全依賴著這個孩子悲慘的遭遇。他必須這麼地悲慘,我們才能過得這麼地幸福,這就是他們認定的公平。
每每讀到這裡我都不免會想,如果是我,是否也會為了多數人的福祉,將無辜的人關進永恆的悲傷之中?當他哀號爭取著屬於他的正義時,我是否會關上地窖的門,假裝自己從來都聽不見?當他要求真正公平的待遇時,我是否覺得,只要為他送上飯菜讓他苟活,就算是盡了一份責任?
也許,台灣多數人的心都是一座歐梅拉斯,只是我們不願承認。
我們假裝無法感受228及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的痛楚,把他們關進我們心中的地窖,彷彿從來看不見他們的眼淚、聽不見他們的呼救;當他們要求真正的公平時,沒有人出來為錯誤負責,也沒有人願意替他們爭取正義,我們只是用少得可憐的補償金打發他們,希望他們不要再出來打擾大家平靜愉快的連續假期。
也許我們早已偷偷認定了,他們的痛苦,是一種交換。
所以,當228連假時,孩子們走在充滿歡樂氣氛的遊樂園,天真地抬起頭問:「為什麼今天可以放假呢?」我們只是笑笑的不回應。
否則,能說什麼呢?你該如何對孩子解釋,時至今日沒有一個受難者家屬知道他們如何失去爸爸媽媽、沒人知道是誰開的槍、是誰刺的刀?他們終其一生都活在哀痛之中,而哪怕只是一句道歉,都未曾有任何加害者親口對他們說過。這就是我們放假的原因。
你該如何對你的孩子開口,告訴他,只要我們過得幸福就好,我們只要經濟、民生、發大財,至於地窖裡的小孩、承受苦難的受難者、失去家人的受難家屬,他們沙啞的呼救聲、他們淚水決堤的熱熾臉龐,我們都只是假裝在乎,其實,我們根本就不在意他們的公平正義,只希望他們不要每年228都出來煩、不要每次選舉都出來煩。這,就是我們放假的原因。
我們真的能夠接受那種,建立在他人痛楚之上的和諧與幸福嗎?這樣的我們,真的能夠幸福嗎?
在《從歐梅拉斯出走的人》的最後,作者Le Guin這樣寫道:
偶而會有一個年輕男孩或女孩,在見過那孩子之後就不再回家,他們沿著馬路獨自前行,穿過美麗的城門,離開了歐梅拉斯。當夜幕降臨,這些旅行者必須走進黑暗,孤獨地穿越田間小徑及山巒,不再回頭。他們要去的地方,對我們來說遠不如這歡樂之城,我不知道該怎麼描述,有可能,他們的希冀之地根本不存在,可是他們似乎知道自己要去哪裡,離開歐梅拉斯的人知道。
這就是故事的結局。
而我們呢?什麼時候我們才要誠實地面對自己?什麼時候我們才會明白,真正的族群和諧是必定是人人平等的,沒有人需要為了成全他人而犧牲,也沒有人可以犯了罪而不負責任;什麼時候我們才能理解,幸福是用最清澈的眼光回顧自己的人生,然後問心無愧;只有到那個時候,我們才有可能像故事的結局一樣,一起攜手走向遠方那個和平共生的島嶼,即使,我們都知道那條路是如此黑暗難行,有可能,那個平等的島根本不存在這世界上,但至少,我們知道我們該走向哪裡,我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