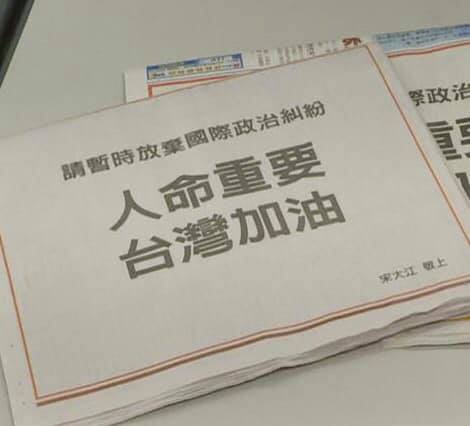卡繆《鼠疫》被引用得最多的應該是以下這一段:
「世上的罪惡差不多總是由愚昧無知造成的。沒有見識的善良願望會同罪惡帶來同樣多的損害。人總是好的比壞的多,實際問題並不在這裡。但人的無知程度卻有高低的差別,這就是所謂美德和邪惡的分野,而最無可救藥的邪惡是這樣的一種愚昧無知:自認為什麼都知道,於是乎就認為有權殺人。殺人兇犯的靈魂是盲目的,如果沒有真知灼見,也就沒有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愛。」
意思不是最明顯不過嗎?天下幹得最多壞事的不是奸惡,而是蠢惡。蠢人最忌好心,如果他心地壞的話,他的蠢自然會使他害回自己,好心地蠢只會害人哋。但卡繆不是想講這種,人們卻剝離整個脈絡理解這段話,忽略了之前這一段:「作者無意過分強調這些衛生防疫組織的重要性。的確,我們城裡的許多人如果處在作者的地位,今天免不了要傾向於誇大它們的作用。但作者則趨向於這樣的看法:如果對高尚的行為過於誇張,最後會變成對罪惡的間接而有力的歌頌,因為這樣做會使人設想,高尚的行為之所以可貴只是因為它們是罕見的,而惡毒和冷漠卻是人們行動中常見得多的動力,這就是作者不能同意的地方。」
這樣才稍為理解卡繆想批判的是對善的歌頌、防疫人員的英雄化。香港醫護發起罷工,抗議政府因政治理由拒絕封關防疫,爭取善待醫護,卻招來一些人惡意謾罵,將他們與2003年的抗疫「英雄」相比,看看人家多麼不計較利益犧牲自己的生命,你們卻怎樣怎樣,應驗了卡繆的批判:「如果對高尚的行為過於誇張,最後會變成對罪惡的間接而有力的歌頌。」捨己救人固然值得歌頌,但高舉它的罕見,就會形成一條苛刻的道德門檻——你如果不跨過它成為謝婉雯,你就淪為仆街!
蠢惡的人,英雄化犧牲。普遍醫護向政府施壓,是為免謝婉雯的悲劇重演,偏偏蠢惡者為了難得有醫護可被他們歌頌,竟反責這些人不肯犧牲自己。這是嗜善的歹毒!
大陸官方發放軍醫們慷慨就義地上機前往武漢的影片,令絕望的人民有了歌頌的對象,遺忘了武漢還有一群沒有被英雄化的醫護正不辭勞苦地前線作戰。武漢醫生對電話咆哮說:「我們不要人!我們要物資!」然而他們得到的,是一群準備好取代他們的「英雄」。
要讀懂這段話,還需要看透前一章才能理解——主角醫生里厄與同袍塔魯的告解。卡繆試圖替醫護解究一個問題:是甚麼使你們願意犧牲?
一般人的答案是:他們的情操很高,有仁愛精神等等;但卡繆一蓋否認這些是醫護就義的主因。里厄和塔魯都問同一個問題:為甚麼我們沒有這些東西,卻又準備好犧牲?
「既然您不相信天主,您自己又為什麼表現得這麼富有犧牲精神?」
里厄的答案是:同客觀事物作鬥爭。
「您一定會想這未免太自大了吧。請相信我,我只有這應有的驕傲,我並不知道會有什麼結果,也不知道在這些事情過去後將來會怎樣。眼前擺著的是病人,應該治愈他們的病。過後再讓他們去思考問題,我自己也要考慮。但是當前最要緊的是把他們治愈。我盡我所能保護他們,再沒有別的了。」
然後里厄這番話,正是醫護的肺腑之言:
「當我開始行醫時,我幹這一行有點迷迷糊糊,因為我需要幹它,也因為這同其他行業一樣,是年輕人所企求的行業之一。或許也因為,對像我這樣一個工人的兒子來說,這是一個特別困難的行業。還有,得經常看著人死去。您知道有人就是不肯死嗎?您聽見過一個女人臨死時喊叫'我不要死'嗎?而我卻見到聽到了。對著這種情景,我發覺自己無法習慣。那時我還年輕,我甚至對自然規律抱有厭惡的情緒。從此,我變得比較謙遜了,理由不過是我總不習慣於看人死去,此外我一無所知。但畢竟……」
醫護為甚麼要這樣做?就係因為需要去做啊!就是讓「2+2=4」這麼簡單。不是為了高尚,而是為了踏實,與抽象概念作鬥爭。
塔魯提醒他說:「明天您得上醫院來打防疫針。在著手幹這個活兒之前,最後一句話是:您得考慮一下,您只有三分之一的生還機會。」
里厄回答說:「這種估計是沒有意義的,醫生,這您也同我一樣明白。一百年以前,波斯的一座城市裡的所有居民全部死於鼠疫,波斯的一座城市裡的所有居民全部死於鼠疫,恰恰只有一個洗死屍的人活了下來,而他自始至終沒有停止過他的工作。」
像洗屍者默默做好手頭上的工作,才是最普遍(並不罕見)的醫德。
里厄載着塔魯,醒起自己還未問他:是甚麼驅使你幹這種事?
塔魯的答案:我不清楚。也許是我的道德觀念——理解。
這是里厄最後一次見到塔魯。
「第二天起,塔魯就著手乾了起來,他組織起第一支隊伍。以後又有許多小隊紛紛成立。作者無意過分強調這些衛生防疫組織的重要性……」
作者
==========
如果你想支持我全職寫作,鼓勵你加入我的Patreon,只要參與者夠多,每月小額資助就足以撐起一個作家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