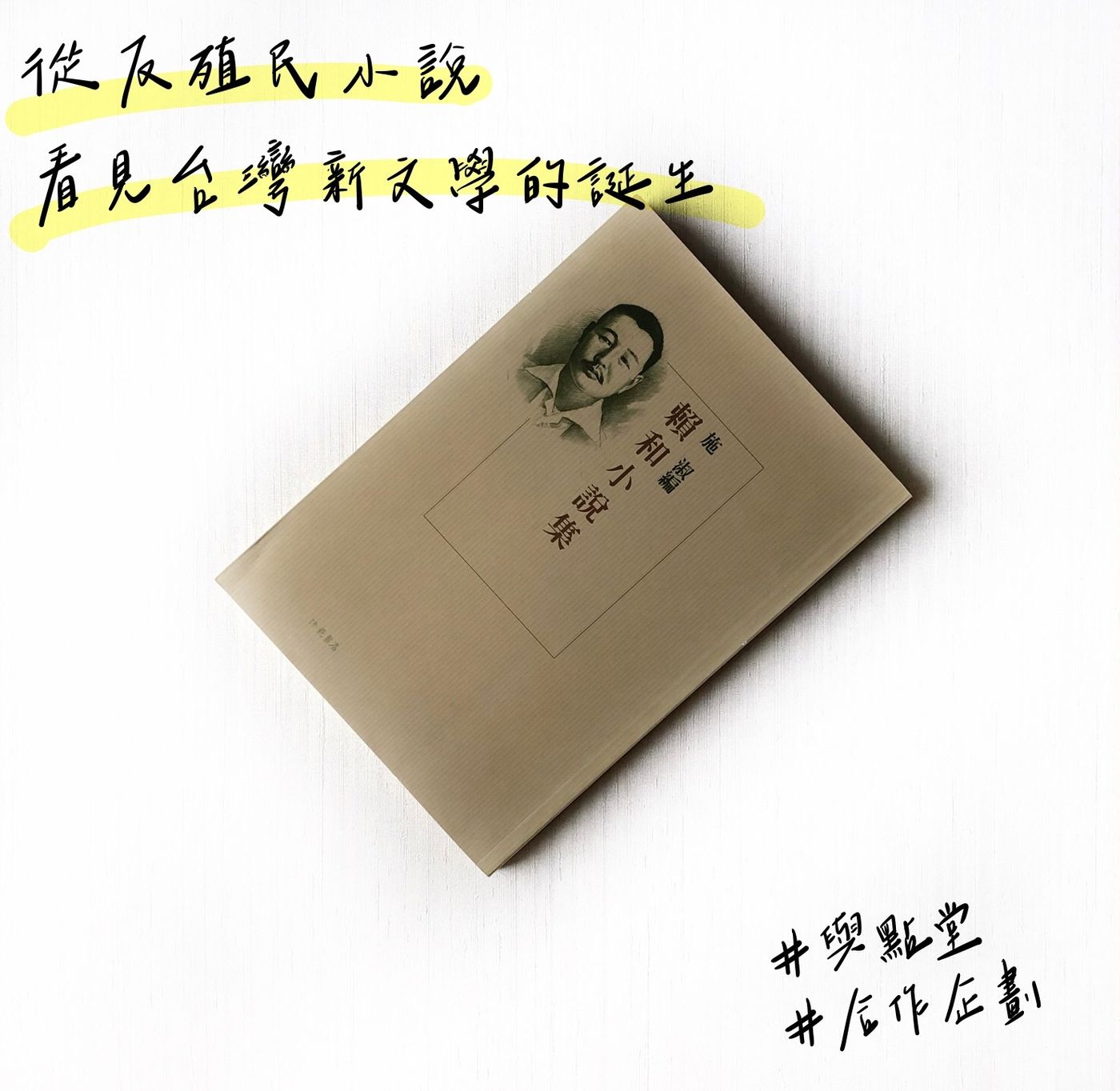[00:00:05] 主持人:本周應該算是一個特別節目,會直接公開在網絡上。您在臺灣出過幾本書,包括民國人物系列的三本、《遠東的線索》、《滿洲國》、《中國窪地》和《經與史》。應該在今年四月的時候就會在臺灣發行電子版。在臺灣發行電子版的話,就代表全世界所有看得懂華文的人都可以直接在網絡上購買您的著作。所以我想趁這個機會請您談一談這些書。當然,重點就是面對臺灣的讀者,做一個像是作者給自己的書做的點評和介紹。首先是關於《經與史》,這本書是您最早出版的書,是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出的,公認是您的著作裡面最難懂的。您可以談談,您為什麼當時要採取這種壓縮餅乾式的寫作風格?
[00:01:02] 劉仲敬:我好多東西都是按照壓縮餅乾的方式寫出來的。我知道有些人的寫法是摻水式的。而我用這種方式寫的目的就是留下種子。也許有朝一日我不在了以後,會有像我一樣的人從一個很小的信息包裡面抽出很大量的信息來。這等於是留線索。這就像是格林童話所說的,亨塞爾與格萊特(Hansel and Gretel)被父母扔在森林裡面,他們一路扔了一些小卵石作為線索,是同樣的做法。當然,你如果是掙稿費的作家的話,那麼你肯定會拿一個很小的題目來摻很多水,做很多事情。但是我所做的事情差不多像是,給未來的偵探——也就是像我這樣的人留下一些線索。而大多數人能不能夠懂,基本上是不予考慮的。
[00:01:54] 主持人:您在這本書的最前面提到,您心目中有三種讀者:一種是《日知錄》的假定讀者,類似漂流瓶的接收者;第二種是對中國古代的歷史有不同想像的人;最後就是國家計委的從業人員。請問一下,就您的想像和認知,臺灣的讀者大部分是歸在哪一個分類裡的?
[00:02:25] 劉仲敬:當時我並沒有考慮臺灣的讀者。《遠東的線索》還考慮了一點兒,而《經與史》基本上是沒有考慮的。《經與史》考慮的其實主要是三種人當中的第一種。像《日知錄》那種寫法,本來就是,明亡以後,假定你寫的書永遠不會出版,像他崇拜的鄭所南的《心史》那樣藏在井裡面,經過幾百年以後才能問世。當然,你甚至還需要發明一種特殊的語言,保證在當時如果出版的話不會被一般的讀者辨認出它內在的涵義。後面那兩種人都是附帶的。假定會有這兩種人讀到,那也可以附帶一下。
[00:03:07] 主持人:看得出來,您這個嘗試是完全成功了。關於《近代史的墮落》這三本書(晚清北洋卷、國共卷、民國文人卷),我覺得最有共感的反而是第三本,就是民國文人卷,尤其是陳寅恪、余英時、張愛玲和金庸這四篇。您在這四篇裡面的分析清楚地顯現,所有的文學創作和歷史研究都是依託于作者本身的社會背景的。雖然您的書籍以歷史為主軸,但是如果說我們想要把您的書推廣給對歷史沒有涉獵或者興趣的讀者,那麼您認為這本《近代史的墮落·民國文人卷》是不是一個很理想的引子?
[00:03:42] 劉仲敬:這個事情有一點點不一樣。《近代史的墮落》都是一些分散的文章,它是給約稿的讀者寫的,而不是給自己寫的,所以它不符合所謂的“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那種顧炎武式的標準。它是根據讀者的要求,讀者感興趣什麼,就相應地定制。而且,寫作跨度的時間是極長的,涉及到體系的升級。比如說,寫慈禧太后的那個時候,那是共識網那個時代,約稿的就是Carmen(邵思思),是共識網的小編,眉山人,後來變成了党妹。寫到最後幾篇,比如說金庸那一篇的時候,已經是在美國了,那時候我已經完全肆無忌憚了。所以,它中間涉及的體系升級的跨度是很大的。
[00:04:37] 總的來說,這個跟我自己的做法有關係,我做事的方法從來都是分自留地和公家的事情這兩部分的:自留地是不計成本的,是完全給自己準備的;而對付公家的部分,那就是以應付為主的。按照我原先的規劃,我會始終是吃著公家的東西,玩兒自己的自留地,實現利益最大化。但是搞到最後,每一次都是自留地變成了主業,然後我又在自留地的內部再開拓一個新的小自留地出來,於是原來的自留地又變成帶敷衍性質的東西了。總之,這是一種以戰養戰的做法。比如說,我是拿著體制的工資,然後自己搞自己那一套的;寫慈禧太后那些篇目的時代,我又把從共識網或者廣西師大出版社拿來的錢用來支付自己的內部事業。直截了當地說,那些分散的文章在我看來是不算數的,屬政治宣傳的外圍,儘管它看上去不像是政治宣傳。有些也還有實質性的創見部分,但是那是不得已的,是順便帶出來的。
[00:05:57] 等於就是這個樣子:如果我要寫自己的東西的話,你可以像博爾赫斯說的那樣理解,像一個將要被納粹德國槍斃的作家在臨死之前抓緊時間構思一下劇本一樣。對於他來說,上帝是唯一的讀者,除了上帝之外不會有別的讀者。在他自己的主觀世界內,在行刑隊開槍之前的那幾秒鐘,時間突然停止了,他有幾年的時間寫完那一本書,寫完了以後,一聲槍響他就倒下了。但是從外界和行刑隊的角度來看,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變化,幾秒鐘之內就開槍了。這就是他跟上帝之間達成的私人契約。在他的主觀時間內,那幾秒鐘被拉長成了幾年,他寫出了這本以上帝為唯一讀者的書。對於外界和行刑隊來講,什麼都沒有發生變化,就是開了一槍,把人給打死了,僅此而已。
[00:06:57] 這是以上帝為唯一讀者的書,但是最後交到了廣西師大出版社的手裡面。準確地說,它所涉及的那個理論體系是以上帝為唯一讀者的。像是泡利(Wolfgang Pauli)說的那樣,他見到上帝以後要提一個問題(“Why 1/137 ?”)。而我是在寫一份答案。我跟他相反,我不是給上帝提出問題的,我是來寫一份答案,因為我是一個優秀的做題家。這道莫名其妙的題——就是中國的存在本身,是上帝扔在很多人面前的,現在我把答案給你解出來了。這個答案是寫給上帝的。其他人能不能懂,我完全不在乎。這時,廣西師大出版社來約稿,而我又沒有別的東西可以給他們,於是我就倉促地把這個東西給了他們。
[00:07:52] 至於與此同時開始寫的那些亂七八糟的文章,那就要看約稿的對象和我設計的對象是怎麼樣的。一般來說,我採取的辦法總是那種借水養魚式的辦法。就是說,你約稿,我可以給你稿,但是我暗中藏有的一些信息你不一定能夠看得出來,而這些信息其實是帶有政治宣傳目的的。那取決於當時的形勢,例如共識網代表的是什麼,它的假定讀者是什麼。後來的有些東西是給冬川豆的俱樂部讀者寫的,他們又是另外一撥人,我假定他們是被亂七八糟的民小(民主小清新)或者其他人薰陶過來的,然後要傳遞給他們什麼信息。基本動機其實是很簡單的:假定你是什麼樣的人,然後每一個提供給你的信息都會把你往某一個方向拉。
[00:08:49] 共識網的動機就是,把所有人都往一個中間的、統戰的平臺上拉。共識網的背景是南方週末那一系的,南方週末的前身就是華商報。華商報在廣州淪陷以後從香港撤回來,它的幕後主持人就是廖承志。梁漱溟或者其他什麼所謂的“近代的良心知識分子”,都是他們出錢包養的。所以,日本人打到香港的時候,東江縱隊就直接出兵,派地下黨員去把他們接出來,然後又由東江縱隊武裝護送他們到別的地方去,就是這個原因。後來日本人投降了,然後他們就回到香港,繼續從事在國統區不能從事的各種活動。但是在廣大淪陷區的無知青少年——比如說對於共產黨有一點不滿、但是又找不到引路人和合適的思想導師或者輿論領袖的人看來,這些人說的話跟共產黨不一樣,就等於是一個准反對黨。這樣一來,它就把在其他地方會直截了當變成反對黨的人群引到統戰黨手裡了。
[00:09:57] 這樣一來,執政黨是我的人,反對黨是我的白手套。通過共識網這樣的“共識平臺”,你們左右共識一下,於是天下英雄又重新回到了我的口袋裡面。免得天下英雄對體制不滿,使比體制裡面的酒囊飯袋有點本事的人流散出去給我搗亂。這樣一來,繞一個圈又回來了。尤其是那些虛榮心很強、很想當偉大導師的知識分子,比如說像我這樣的人,它給了充分的機會,讓你覺得你已經是偉大導師了。然後在不知不覺之間,你就順著這個平臺被引回來了。這就是共識的意義所在。共識就是,磨掉反對的人和各種異己力量的鋒棱,盡可能向體制靠攏,向共識的方向靠攏,大家和解共生。儘管他們不會用“和解共生”這個詞,但是實際上是這個意思。凡是和解共生,都是有前提的。它有一個隱含的前提,但是它可以使你覺得,如果就我不和解共生,我是不是跟塔利班沒有什麼區別?那我要不要讓一讓步?然後,我往哪個方向讓步呢?這個方向就是一目了然的。
[00:11:09] 我是逆向的統戰,往相反的方向拉一拉。我一直是這麼做的。我做這件事情的很多時間在外界是沒有痕跡的,但是一般來說實際上就是這樣的:對於死硬的毛派,要把他們往改革開放派的方向拉一拉;對於改革開放派,要把他們往市場經濟自由主義者的方向拉一拉;對於市場經濟自由主義者,要把他們往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的方向拉一拉;對於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要把他們往麥卡錫主義者的方向拉一拉;最後一步是,對於不可救藥的麥卡錫主義者,要把他們往民族發明的方向拉一拉。當然,這個跟共識網和他們那種統戰方式是恰好相反的。統戰的原則是什麼?白區党對於不可救藥的反華分子不能要求太高,你儘量把他搞成“只反共不反華,什麼都是共產黨的錯”就行了;對於不可救藥的反共分子,你不能指望他不反共,但是你可以誘導他,反共的同時,你還要愛國,一切都是共產黨的錯,中國是沒有錯的;對於不可救藥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你要讓他在反對共產黨的同時承認世俗政權對教會的權力;對於不可救藥的市場經濟自由主義者,你要引導他相信,全世界沒有絕對的市場經濟國家,中國正在向這個方向靠攏;對於改革開放派,你要教育他,畢竟國家是党建立的,沒有黨就沒有改革開放。總之,每一圈都要把他們往共產黨所在的圓心引導。
[00:13:03] 而我搞的統戰實際上是,對相應的每一圈,都要把他們向外引導。因此,我說的話跟白區黨說的話一樣,對不同人說的話是不一致的。例如,對於人數最多的民小來說的話,就要努力把他們往麥卡錫主義這個方向引。而共產黨對於民小,則是要把他們往愛國者的方向去引,對於麥卡錫主義者,要往民小的方向引,諸如此類。從數量上來看,我寫給民小的東西還是最多的,因為恐怕他們的人數是最多的。但是這也跟我自己的活動空間是有關係的。隨著我的活動空間漸漸移動到深圳,然後再移動到美國,漸漸的,過去的那些統戰對象從我的視野中消失了。搞到最後,麥卡錫主義者就變成其中最溫和的人了。在這個時候,麥卡錫主義者已經不能讓我滿意了,就開始全面推行反華了。反華這個最後的階段,體現在余英時、金庸、余光中那幾篇裡面。按時間線來講,那個過程也正是我在總結民族發明的各種模式的時間,所以我又忍不住把相應的內容也給帶了進去,儘管跟有關的當事人其實關係不是很大。因為這些事情其實是統戰工作或者說是反統戰工作,所以它是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和工作對象的不同而不斷變化的。因此,你如果把它當成是某種抽象的、純粹理論的指標的話,最後就會發現它們每一篇的框架都是不一樣的。
[00:14:41] 其實,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也是這樣的。你要是把他們的所有著作都當作神聖不可侵犯的,那麼就會陷入極大的混亂。實際上,他們的大部分著作是雜文或者政論文,是根據當時的對象的。例如,馬克思絕大部分時候說話的對象是當時的自由派或者激進派。他的做法就是,把他們盡可能地往激進的方向拉。因此,他有時候說起話來跟保守派和反動派一模一樣。因為他要打擊主流激進派和主流自由派,所以他經常運用保守派的論據,但是目的是跟保守派相反的。但是馬克思也有他的根本性的書,比如說《資本論》。這是他的核心理論,這個核心理論不是為了具體的政治爭議而設置的。當然,他到死也沒有寫完,那是因為理論上出現了漏洞的緣故。而我也有我自己的核心理論,屬核心理論的、搭建框架的書是不受影響的。但是,實質上是屬統戰和影響輿論的東西,那是隨時隨地憑相應的環境而改變的。但是在寫作的過程當中,我可能把我當時正在搭建的理論的某些部分不由自主地給帶了進去,所以會在裡面留下一些片段。
[00:16:01] 主持人:您有兩本書主要是由演講稿所集成的,其中一本是《中國窪地》。我們可以想像,“中國窪地”這個詞應該是您創造(Coin)出來的。現在其實在臺灣有很多人在用。您在這本書裡面提到,內亞海洋的作用在我們所謂的中古時期的黃金時代是非常巨大的。如果未來有人能夠對內亞海洋在漢晉到唐朝這段時間產生的巨大作用做一個系統性的整理和分析,那應該是對人類文明的理解有非常巨大的功用。但是您在關於美索不達米亞的講座裡面提到,考古學基本上背後都是有政治立場和政治意義的。現在如果您把內亞的黃金時代(西元五百年到一千年的那段時間)作為技術輸入管和旋轉門的功能整個總結出來,對現在內亞的那些國家到底有什麼好處呢?
[00:17:20] 劉仲敬:這個其實只是一個解釋體系的問題。對他們來說有什麼意義,其實就要取決於他們將來的認同。對於東亞來說,這就是一個重構歷史體系的過程。
[00:17:43] 主持人:《滿洲國》在諸夏和諸亞的民族發明學講座裡面是最巨大的一個體系,一共有十講。當初是有意為之嗎,還是說跟滿洲國相關的史料特別豐富有關係?
[00:17:58] 劉仲敬:不是有意的。但是也不能說它是特別巨大的,恐怕只是它跟開講的那幾講相比起來是更加巨大一些。講座這些東西,在我自己做事的方式當中其實是比文章更外一層、更漠不關心的東西。我真正要寫的書是極少的。在那以外會有一些比較多的像是分篇的文章,那是計劃外的。理想中的我是純粹的火星人,跟世界沒有發生接觸。但是實際上發生接觸了,於是就滲透出一些秩序輸出性質的外圍。而講座這個東西又是外圍的外圍,是後來跟社會接觸的產物,而在我自己心目中則是很不值錢的東西。大體上我做事的方法是這樣的:製造一個資料夾,把相應的資料放進去,放到足夠多的時候,漸漸就可以形成書了。但是根本不用到放到足夠多的時候,還是一些零零星星的資料的時候,每一個資料都可以製造出一個或者N多個講座。講座多少,是完全看需要的。如果變成比如說餘傑那樣的性質的雜文的話,每一個小小的篇章和材料都可以寫出無數多的雜文來。《滿洲國》實際上是一本書,但是是一本還沒有寫成的書,因為資料和時間都還沒有湊到足夠齊的地步。但是在這個時候,製造出很多相應的講座來已經是不成問題了。例如,現在我的文件夾裡就有很多《滿洲利亞史》、《巴蜀利亞史》之類的文件夾,每一個文件夾裡面有幾百個材料。等到時間成熟,它們會變成書。但是在沒有變成書之前,就已經有一部分透露出來,變成了講座,然後就有人把這些講座整理成為書。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就像是,陳寅恪的《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其實是他在上課的時候給學生講的講義,他自己不想拿出來當書的,但他死了以後就有人把這些東西搜集起來作為書,所以你注意,這本書的注釋其實是極少的;而《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是他自己親自寫的,是他認為已經足夠成熟而拿來出版的。兩書之間有很多重合的地方,只不過一個語氣是口語體,另一個則是典雅的文言。還沒有出版的那本書和已經出版的這些演講錄之間的關係,其實也是這樣的。嚴格來說,這些演講錄之所以拿來出版,是滿足粉絲的需要,而不是滿足我自己的計劃。
[00:20:36] 主持人:最後我想請您談談我最喜歡的那本書,就是《遠東的線索》。這本書是我最想要推薦給臺灣讀者的。這本書很清楚、很完整地解構了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歷史神話,也為臺灣的未來做了推估和建議。您曾經多次提到,臺灣的地緣位置就相當於東亞的比利時。大英帝國需要比利時存在,讓它鎖住法蘭西通往英吉利海峽和北海的道路。英國不允許任何歐陸列強控制北海,無論你是誰。日本國亦然,日本需要臺灣鎖住支那通向西太平洋的野心,日本不會允許任何亞洲帝國控制台灣海峽和黑潮(Kuroshio Current)航道,無論你是誰。可不可以請您給臺灣的讀者稍微拓展一下《遠東的線索》這本書裡面跟臺灣有關的那幾個小部分,簡單地說就是冷戰過後的那幾個小部分的課題?
[00:21:31] 劉仲敬:其實臺灣跟《遠東的線索》的關係不大,倒是跟歷史真相學家的關係很大。九十年代以後的中國正在經歷一個類似蘇聯的歷史真相重新發掘的過程,這個重新發掘當然是有政治性的。如果歷史體系倒了的話,共產黨把它稱之為歷史虛無主義。什麼叫“歷史虛無主義”呢?凡是不接受共產黨領導的學說都是歷史虛無主義,否認共產黨作為歷史製造者的基本作用就叫歷史虛無主義。但是這個跟“虛無主義”的原始定義是不一樣的。“虛無主義”這個詞的原始定義是在歐洲基督教文化的傳統中產生出來的。實際上,共產主義及其前身經常在布爾什維克產生以前的俄國被稱為“虛無主義”。“虛無主義”的意思是什麼?就是你解構了世界本身的意義。世界的意義在表層是由很多很庸俗的東西組成的,比如說一般市井小民所關心的錢和女人這些東西;再進一步,是自由主義者和法學家關心的帝國憲法、議會、皇室繼承權這些問題。但是這背後,你只要按照幾何學家尋找第一原理、從定理推向公理的那種邏輯,推到最後,一切意義的終極歸於上帝本身。俄國文化和西方文化建立在上帝的基礎之上,建立在兩希(希臘和希伯來)文明的基礎之上。所以,解構這個意義體系就是虛無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是十九世紀中葉和十九世紀晚期俄國虛無主義大浪潮當中產生出來的最極端的一翼。所以在俄國布爾什維克的思想史當中,它的十九世紀的祖先通常都是虛無主義者。現在它把這個虛無主義拿來逆向運用,從神學的角度來講就是撒旦為王,試圖把解構說成建構,把建構說成解構,以共產黨為中心,違反共產黨創造世界的一切解釋都是虛無主義。
[00:23:33] 我們要注意,同樣的,違反上帝創造的各種解釋,有很多表面上看來跟上帝沒有關係。比如說,在女人的問題上,你覺得這只是成功男人好色的某某事情,只是純粹世俗的東西,但它背後肯定涉及到你是否尊重婚姻的神聖性,而婚姻的神聖性是一個上帝契約的問題,所以歸根到最後是一個是不是承認兩希正典的基本問題。同樣,共產黨設計的所有問題,有些問題是市場經濟的問題或者企業知識產權的問題,好像都是純粹技術上的,但是追溯到最後也是承不承認共產黨作為假上帝的這個基本地位。共產黨的整個體系,無論是關於歷史、政治還是經濟的,追溯到最後就是你必須得承認共產黨是上帝。如果共產黨不是上帝的話,那麼它就只能是撒旦的門徒和恐怖組織,沒有中間道路的。共產黨不是自由黨、民主黨或者其他什麼純粹世俗的黨派。這些世俗的黨派只在淺層次活動,為具體的利益和社會關係而活動。它不干涉原有社會的意義體系本身,而是默認這些體系的存在。但是共產黨在這樣的前提下是存在不下去的,它必須顛覆意義體系的最深層,實現無神論的篡位。
[00:24:52] 但是這個篡位在理論上存在著巨大弱點。例如,基督教文化和相應的政治體系在理論上是自洽的。上帝創造世界,但是儘管如此,我們兩個人可以是死敵。我認為你完全是邪惡的,你所說的全都不對,但是我們的意義體系的最深處仍然是建立在“上帝創造世界”這個最基本的前提之上的。儘管在整個爭議和鬥爭的過程中間可能一個宗教詞匯都沒有出現,但是骨子裡,有判別能力的人都可以看出,最後都要追溯到這一點。包括基督教世界產生出來的那些理論上的自然神論者、人文主義者或者無神論者,像費爾巴哈這樣的人,其實他們的理論追溯到最基礎,仍然要涉及到所謂的此岸性和彼岸性諸如此類的問題。無論如何,這些所有的觀點最終都是自洽的。它們之間的矛盾是這樣的:一棵大樹越長越高,它的分支就越來越多,開始的時候只有兩、三個枝椏,最後幾百年、幾千年以後,枝椏無數多,每一個枝條上都結出了果子,每一個果子都說我是正統而你不是正統,相互之間掐來掐去。但是,你從最外面的果子追溯長出果子的枝條,從小枝條追溯到大枝條,追溯到土地表面,最後發現它們都是從同一個樹芽上長出來的,只是後來分開了。他們的理論是能夠自洽的,就是說是一步一步建立起來的。
[00:26:26] 但是共產主義的理論就很難了。你可以把共產黨推成歷史創造者和上帝,但是這跟建立在上帝觀念上的基督教(當然你還可以延伸到伊斯蘭教和其他宗教上面)就有一個非常致命的不同:共產主義理論是一把斧頭,不是一棵樹。無論是馬克思和列寧本人的著作,還是歷史上共產黨作家進行的所有實踐,都是砍樹,對準這一根枝條砍下去。從理論上是,反對自由主義,反對社會民主主義,反對各種主義。從實踐上是,打倒地主,打倒資本家,打倒走資派,打倒……無限延長下去。每一次行動都是砍掉了樹上的某一個枝條,但是留下來的是一大堆死在樹上的碎木頭。共產黨的整個歷史,按照他們自己的歷史發明,應該是共產黨創造歷史的整個過程。但是實際上它顯示出來的是,共產黨破壞這個破壞那個,破壞以後自己站不住腳,又把原來砍掉的東西想辦法像木頭拐杖一樣重新撿回來或者重新改裝,它們彼此之間是沒有連貫性的。
[00:27:41] 你看,在伏爾泰和其他什麼反對基督教的人文主義者身上,它是有連貫性的。每一個思想家或者每一個人,他都有自己的“母親”,有長出他的枝條。你從長出他的枝條上可以看出,例如在伏爾泰和法國啟蒙主義者身上首先就可以看出,冉森派(Jansenism)和耶穌會建立起來的那些皇港修道院(Port-Royal-des-Champs)和其他學院,以及圍繞著他們的關於預定論(Predestination)和自由意志(Free will)之間的長期爭論,這個爭論不僅從性質上講是基督教的,而且他們使用的所有工具全都是經院哲學創造出來的。再往前延伸,就要延伸到早期教父(Early Church Fathers)和基督教引進希臘哲學的時代。每一步都是連續的。就好像是,你要考證你是誰的時候,你首先發現了你的父母是誰,然後你的父母有他們的父母,一步步搞上去。你沒有任何一個祖先是人工合成的,即使你沒有把他們全都考證明白,但是你可以想像,他們全都是某一個時代的人,只是越來越古老,連續性的家譜是顯然可見的。
[00:28:46] 但是共產黨所做的事情就沒有一個連續的家譜。相當於,有人殺了你的祖父,又有人砍了你曾祖父的一條胳膊,第三個人打傷了你的母親,第四個人跟你打了一架,然後你要把這四個人構成一個譜系。張三跟比利時基督教社會黨做過殊死鬥爭,李四跟英國工黨做過殊死鬥爭,王五勝利地擊退了俄國民粹主義者的猖狂進攻,趙六打敗了帝國主義在上海的走狗,然後你把他們聯繫在一起,說這些人是你的祖先。第一,這些人全都是斷子絕孫的,沒有一個有後代,第二,你不是他們當中的任何一個人生出來的,但是你要堅持說這些人都是你的祖先。共產黨的歷史發明,就是這樣製造出來的一個破碎的體系。這就是為什麼所有接受過共產黨教育的人全都處在思想混亂的狀態。只有最愚昧的人例外,因為他什麼也沒有聽懂。而接受基督教教育和其他教育的人不一樣,它是教育層次越低的人思想越混亂,越高的人思想越嚴密。共產黨恰好相反,你只有是完全無知、背過書又忘掉的人,才能夠保持一點人格的完整性。受的教育層次越高,你就越來越陷入人格分裂的狀態。這就是正典和負典,像奧古斯都說的那樣,性質上是不對稱的。不是說左派和右派是對稱的力量,像我的左手和右手一樣看上去長得一模一樣。不是這個樣子的,解構和建構是不對稱的,一棵樹和砍樹的斧子是不對稱的。斧子砍下了許多根樹枝,但是這些樹枝和一棵不斷長起來的樹之間沒有對稱的關係。正典和負典之間的關係不是兩棵樹之間的關係,而是一棵樹和一把砍樹的斧頭之間的關係。
[00:30:44] 這樣自然而然就造成了,共產主義只能依靠恐怖來維持。恐怖的主持者是玩世不恭的人,他們並不相信他們維護的東西。而被恐嚇的對象則要盡可能愚昧,越愚昧越安全。恐怖一旦放鬆了以後,就有各式各樣的人從那些砍下的樹枝上找出不對的地方來,比如說“你是不是抗戰的中流砥柱”這些枝枝節節的問題就會跳出來,於是歷史真相學家就要大行其道了。比如說“《絞刑架下的報告》(Notes from the Gallows)那本書的作者(Julius Fučík)是不是匪諜”、“你們塑造出來的民族英雄怎麼全都是壞蛋呀”諸如此類的問題,就有各式各樣亂七八糟的東西出現。於是,黨當然要雇傭一大批五毛和御用學者,粉碎這些階級敵人的猖狂進攻(按照共產黨在毛澤東時代的術語應該是這樣的)。但是這個仗是打不完的。在你沒有把他們全部殺掉的情況之下,各種混亂的東西被一股腦地找出來。但是這些歷史真相學家背後都沒有完整體系,他們自己找出來的東西也都是一片混亂的。民小、國粉、啟蒙主義者和各種各樣的人,他們唯一共同的特點就是:他們找出了各式各樣的破綻,但是他們並不能夠從破綻背後找出歷史發展的真正脈絡來。要找出真正脈絡來,那是要嚴重地損害自尊心的。你如果不承認東亞基本上是殖民地,而且前現代的東亞也不像波蘭一樣,也同樣是殖民地,那麼你所製造出來的體系也會像共產黨的體系一樣充滿顛倒錯亂。於是,你就是拿一個顛倒錯亂的體系去對抗另一個顛倒錯亂的體系。
[00:32:20] 結果就變成這個樣子:共產黨是一把斧頭,砍下了很多亂七八糟的樹枝,共產黨一定要說這堆樹枝是一棵樹,然後你跳出來說那不是樹,你拿了一把小刀去砍。共產黨用這些樹枝搭起來一個像是死樹搭成的聖誕樹那樣的結構,彼此之間沒有連續性,只是無數樹枝搭成的一個架子。你說這個架子很容易打倒,讓我砍它一刀,於是你就拿了一把比共產黨的斧頭更小的刀,對準共產黨搭起來的這個假樹去砍了,砍下一根枝條,然後你就把這根枝條砍成了無數碎片。然後你跳起來說:你們從來都不是抗戰的中流砥柱,而且你們自古以來就沒有實行過民主,不是說你們以前實行民主、後來建國以後腐化了,而是你們自古以來就沒有實行民主。你砍下了一根枝條,砍下了另一根枝條,然後又砍下了第三根枝條。那麼你處在什麼地位呢?你是一個解構者的解構者,你把解構者冒充建構搭起來的枝條拿來又砍了一陣子。共產黨把樹上的枝條砍下來,砍成一堆木頭,然後你又把共產黨砍下來的這堆木頭搭起來的這個積木砍成了無數的碎屑,但是你還是沒有任何可以自己站得住腳的東西。大多數歷史真相學家都是這個樣子的,他們攻擊和提到的都是具體的問題。當然,這也跟實證主義的傾向有關。九十年代以後的基本學風,在學術界內部的實證主義就是只講小問題。小問題會搞出很多枝節。
[00:33:45] 比如說羅志田他們那些人考證了一下,“曹錕賄選”其實並沒有賄選,他只是在補發國會議員被長期拖欠的工資(因為財政困難,大家都在拖欠工資),其實國會議員被拖欠的工資、被打的白條還算比較少的。但是,這也可以說是廣義的賄選。從法律上講這並不是行賄,但是實際上,為什麼大家都拖欠工資,而你偏偏給國會議員先發了工資呢?你想討好國會議員。你討好國會議員的目的是什麼?希望他們投你一票。這個就是法律上的賄賂和政治上的賄賂之間的關係。例如,羅馬或者美國的一位政治家跑來說,你們選我當議員,我就要在本地修一座大橋,開一個兵工廠,讓所有人都拿到很好的待遇。這個不違反任何法律,但是按照老加圖這些人的看法,你就是一個腐化分子。羅馬人民本來是應該為國家利益著想的,而你用私人利益去誘惑他們,用國家的錢去收買選民,好讓你自己當官,你丫就是一個腐敗分子。但是這個腐敗分子不違反法律。法律上的腐敗分子是什麼呢?你拿了某個承包商的錢,就把當地的工程承包給他了,這個才叫腐敗分子。凱撒並不是這種腐敗分子,但他確實是老加圖意義上的那種腐敗分子。我在高盧打仗,拿了很多戰利品回來,這筆戰利品我不私吞,本來我作為統帥應該分一個大頭的,但是我把這些大頭全部拿出來送給羅馬人民,羅馬人民愛上了我。這個就是老加圖意義上的那種腐敗了。曹錕的腐敗就是這種意義上的腐敗,從法律上講他並沒有腐敗。
[00:35:18] 但是,這樣的分析肯定要破壞北伐合法性諸如此類的整個體系,如果你會想的話;但是如果你不會想的話,那就不會,你只看到這個具體的分析。九十年代以後的學風,基本上都是搞這些具體的東西。對於一個有思考能力的人來講的話,你肯定會想到:“曹錕幹了這樣一件事情就算是賄選,那麼蔣介石幹的事情不是比曹錕厲害得很多嗎?那麼為什麼曹錕幹了這一點點就變成壞人了,蔣介石幹了這麼多反而變成好人了呢?毛澤東又比蔣介石幹了更多的東西,那麼他為什麼反而變成英雄了呢?這裡面一定有問題。”但是沒有思考能力的人就說:“我只是搜集了一些材料,把它們湊在一起,把它們剪輯拼接在一起。我是一個磚瓦匠人,我並不知道我搞出來的東西有什麼意義。你們應該給我付相應的工資,其他事情我完全不管。”這種行為在毛澤東時代還是要打死的,毛澤東不管你這一套,你丫搞出來是何居心?但是現在可以不管了,現在你只要不直接搞其他的體系,那就可以不管了。但是這些條件從長期上來看,等於說是,堆了很多木頭,早晚要著火的,所謂乾柴烈火。你沒有這些乾柴堆在這裡,是不會著火的。所以,毛澤東其實是做得很對的,斯大林同志做得也是很對的,而改革開放幹部其實是在自欺欺人。
[00:36:33] 像諸如此類的材料,比如說你在基督教文化當中堆這些細節材料,對基督教本身並無任何傷害;但是在共產黨的體系之下堆這些材料,堆多了以後,那是早晚要著火的。所以唯一釜底抽薪的做法就是,你一開始就把這些堆材料的人統統幹掉。你沒有這麼幹,是一個嚴重的歷史錯誤。當然,這時候自然而然的,早晚會產生出試圖堆材料的人,比如說像秦暉這樣的人。大多數人是不肯或者是沒有能力從材料中間製造體系的,而秦暉根據的是歐洲戰後共識政治、福利國家民主制那一套體系,把這套體系移植到中國來,用這個體系來衡量共產黨和它的全部歷史,所以他是極少數能製造體系的人。但是我對他的體系仍然不滿意,於是我就製造了另外一套體系去對抗他的體系。而我的重要性就在這一點,因為大多數人是不肯製造體系的。但你無論製造出任何體系,其實都是對共產黨的體系不利的,於是後來相應的事情都會不斷地發生。
[00:37:37] 但是製造體系的過程並不是像嬰兒直接就跳出來那樣,它是慢慢積累而成長起來的。這有點像是,傳說中猶太人在居魯士攻佔巴比倫以後,從波斯回到耶路撒冷來,建造第二聖殿的時候,基本上是一邊打仗一邊建造聖殿,建築工人也同時是打仗的人。他們離開以色列以後,當地已經被其他的部族佔領了,居魯士把他們放回去的時候他們又要跟那些部族不斷打仗,同時一面製造他們的聖殿。結果,我是在一面進行論戰的過程當中,一面製造我的那套體系的,所以我不斷地把我搜集出來的零星材料拿出來作為打擊材料。你要明白,建造自己的聖殿和打擊別人的建築是兩碼事。一個東西在自己的體系當中只能起很小的作用,甚至完全沒有用處,但是一個不和諧的文件就可以破壞整個畫面,就可以把別人製造出來的歷史體系整個給破壞掉。例如,國粉為了破壞“共產黨是抗戰中流砥柱”的學說,一定要把國民黨說成是抗戰英雄,一定要把日本人說成壞人;但是我推出去一個盧溝橋事變後的英國外交官的文件,就可以破壞他們的整個體系。
[00:39:00] 於是,在這種一面論戰一面建築的過程當中,就產生了《遠東的線索》。它跟《經與史》是不一樣的,它並不是我在九十年代或者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按照火星人那種狀態,純粹理性客觀中立地製造一套解釋體系。從製造解釋體系的角度來講,你只要製造了解釋體系,不需要搞具體的歷史事件。就好像是,你發現了能量守恆定律,你不用去當工程師,會有工程師利用你的定律去做具體工作的。但是《遠東的線索》是戰爭的產物,是跟楊奎松、沈志華和劉統他們不斷作戰的產物,是對於他們為了修補共產黨的歷史體系做出的各種行動的一種破壞性活動。主要是因為我對他們被很多人當成是啟蒙者而感到不滿。在我看來,他們明顯是替共產黨修補整個體系的大匪諜,僅僅是從他們使用材料的方式就可以看得出來。但是還是有很多白癡一樣的民小,因為他們搞出了很多歷史秘密材料,就以為他們是啟蒙者。因為我看他們不順眼,所以我就順便在這個過程中寫了這一本書。
[00:40:14] 這本書寫的方法是這個樣子的:先搭一個框架,然後把各個歷史時間的相應材料一個一個掛上去。這個跟製造理論的方式是不一樣的,它是把你的正在製造過程中的、還沒有拿出來的理論當作一個架子掛出來,然後你把各式各樣的史料掛到相應的樹枝上去。史料多的,就可以多掛;史料少的,少掛一點。而且,它出版和產生的過程都是適合論戰的需要的,而不是適合一本書本身產生的內在邏輯。例如,我現在要寫的這本書,我要掛進去的東西要多得多,可能要多出兩、三倍。但是在《遠東的線索》裡已經掛不進去了,因為書已經出版了。現在我只能把這些材料掛到共產國際的那本書裡面去,把它們作為共產國際在遠東的部分的一部分資料。現在共產國際那本書正好就處在2014年和2015年《遠東的線索》處在的那種狀態。它是一個架子。這本書寫到了全世界,有些部分其實就是在《遠東的線索》那條線上、但是沒有放進書裡面的材料。遠東的部分和歐洲的部分掛得非常密集,非洲的部分和拉丁美洲的部分還只是零零落落的。那本書現在還不能出版,就是因為它還處在一種很不均衡的狀態。資料多的部分,例如東歐的部分,掛都掛不下,而拉丁美洲和非洲的部分只有零零星星的幾個。你要是仔細看《遠東的線索》,你也會發現它的各章節之間是不平衡的,原因也是與此相同,因為它有政治鬥爭性。
[00:41:41] 順便說一句,現在沒有政治鬥爭性了。這樣的書在毛澤東時代和習近平時代不具備政治鬥爭性,因為在毛澤東時代和習近平時代解決這種問題的做法是直接槍斃,你根本不用找什麼證據。但是在江澤民時代和胡錦濤時代,那就像是在戈爾巴喬夫時代一樣,你要裝逼,你要論證,論證的結果就是這樣。這一點我在2014年前後就已經有所預見了。遲早有一天,到你論證不下去的時候,你就只有兩種選擇了:要麼就像戈爾巴喬夫一樣滾蛋了;要麼呢,TMD,我給你論證個鳥,批判的武器鬥得過武器的批判嗎,統統給我拉出去槍斃。後面這種可能性隨著習近平的上臺而迅速地成為事實。結果搞到現在,《遠東的線索》反而只在臺灣有意義了。其實,《遠東的線索》主要考慮的部分是為了跟共產黨的高級匪諜作對。所謂的低級匪諜就是那些罵罵咧咧說共產黨是中流砥柱、誰說共產黨的壞話就黑誰全家的那種匪諜,高級匪諜就是楊奎松和沈志華這種人。但是他們現在肯定也已經沒有什麼用處了。我沒有用處的時候,他們肯定也沒有用處了。臺灣只是一個附帶問題,但是結果搞到現在,就像是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主要出版機器在倫敦那個樣子,因為在俄國已經混不下去了,結果搞到在臺灣出版,影響力全在淪陷區之外。它涉及臺灣的部分,從比例上來講其實是很少的。
[00:43:11] 對於我來說,最重要的就是把共產國際成立以後經略東方的那一部分梳理清楚。那一部分是赤裸裸的,中國共產黨90%以上的經費是他們提供的。而且,所有有分量的技術人員,像牛蘭(Jakob Rudnik)這種人,像羅倫斯(Maxim Rivosh, a.k.a. Joseph Walden)這樣的人,鮑羅廷(Mikhail Borodin)當然更不用說了,全都是蘇聯派來的。能打的人,能做事的人,全是蘇聯人。中國人都是陳獨秀這樣的只會寫文章的人。順便說一句,他們存在的目的是使很多文人產生幻覺,覺得我只要會寫文章就什麼都行。其實你只是一塊遮羞布。有陳獨秀這樣的人在上面活動,大家就不去注意鮑羅廷了。但是比如說對於香港政府的政治部或者工部局的政治部來說,他們知道得很清楚。他們要扣壓的肯定是鮑羅廷夫婦這樣的人。陳獨秀算個鳥,你愛寫什麼愛說什麼,隨你怎麼說好了。之所以隨你怎麼說,就是因為你說的東西其實都是無關緊要的。但是大多數小知識分子直到現在還不明白,他們還自己以為自己人人都是陳獨秀,像何清漣他們那樣:“哈哈哈,我總算發現你們共產黨是一幫壞人了。其他人都沒有發現,你看我發現了,我是偉大的啟蒙導師。”但是接下來的事情就令人奇怪了:我既然已經發現了這些事情,為什麼共產黨還沒有倒臺呢?而且為什麼哪怕是在海外的反共人士當中,大家都還沒有自願地擁護我當領袖呢?按照陳獨秀的故事來講,這些事情都是必然要發生的。其實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陳獨秀的故事根本就是編出來的好不好。
[00:44:39] 像以前紅二代在共識網召集會議,邀請我和金觀濤等人(反正是“走向未來叢書”的那幾個逃亡海外的編者,他們理論上是在六四就已經被通緝而且逃亡的人,但是在2014年前後他們就出現在北京),主辦包括大批紅二代當學員的研討班,我在北京參加了這次會議。當然,其目的是類似高級的共識網,就是把你們這些各式各樣的在思想界有影響的人拉出來搞一個共識。我們按照鄧小平的話說,團結起來向前看,過去的恩怨都不問了。召集起來,宣佈他們的學說。金觀濤在海外研究了這麼多年(他好像就在臺灣,至少當時他可能就在臺灣),他的研究方式是這樣的:他用先進的美國方法搞了一個搜索引擎,把1920年代或者什麼時代的報刊上出現的各種“主義”來一個統計,論證比如說社會主義在這一方面的曝光率大大提高了68個百分點,以此來推測各個思想界的動向,然後他就覺得他的研究十分先進。我聽了以後,就覺得這些人全是廢物。鮑羅廷和斯大林同志拿來的隨便幾架飛機和幾門重炮,比你那些報刊上說的各種主義要重要不下一萬倍。
[00:46:01] 當然,你要研究那些東西是可以的,但是要有適當的比例感。東江縱隊的賬單就顯示得很清楚。華商報的人馬拿的都是極其可憐的一點點,一般來說他們拿的只是實物的物資,例如宿舍、食堂的飯票之類的,在困難時刻還要求他們自己捐獻,以便讓報社維持下去。而像梁漱溟這樣的人拿的就是硬通貨,而且不管他幹不幹事,平時都要給,只為了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平時你把國民黨和共產黨一起罵,想怎麼罵就怎麼罵,高興怎麼做就怎麼做,只要在政協會議解散的那一刻你跳出來配合我們罵一下蔣介石就行了。只要你罵這一下,別的好處全都可以給你。最後,最重要的是比如說送給佛山市警察局長或者是拿給東江縱隊的那些東西,那是用金條支付的。廣州起義的時候,蘇聯代表是拿著從俄國資產階級那裡搶來的珠寶,坐著英國人的船,從蘇聯直接開過來,變賣那些珠寶作為經費。你們這些外圍的寫傳單的宣傳員連稿費都不見得領得到,你們這些領不到稿費的文章卻會被統計進去,證明社會主義的支持度增加了比如說68.7%;而蘇聯拿來的那些珠寶和軍火,你完全就沒有統計進去。你要說那些68.7%是可以的,但是與此同時,你還應該統計一下鮑羅廷或者牛蘭拿的錢和軍火增加了多少,計算一下共產國際在馮玉祥、江西蘇區或者其他人身上花的錢有多少,順便再跟國民政府的收入比一下。比完了以後,你就會覺得那些東西完全都是扯淡。
[00:47:50] 我如果不看的話,我是根本想像不出,在一個國家,理論上統治這個國家的政府的全部收入,還不如共產國際顛覆經費的三分之一。但是仔細一想,這種情況肯定在冷戰時期的非洲發生過很多次了。從殖民地獨立的那些非洲小國,本來在殖民時期都是宗主國倒貼錢給你主辦的。宗主國一旦不倒貼了,就一個個窮得喝西北風。在那個時代,所謂的安哥拉反政府軍之類的,它肯定會比安哥拉政府或者其他什麼殖民地遺留政府錢多。殖民地留下來的政府,恩克魯瑪的那些政府,可能就賣點咖啡豆,換一點可憐的錢,連公務員和教師都養不起。而共產黨包養的那些遊擊隊,肯定就像當年共產國際包養馮玉祥那樣,是飛機、坦克和火炮大批大批給你送來的。你全加納的咖啡豆,把全國人民十年種出來的咖啡豆賣了,買不起蘇聯給你送來的一個坦克分隊,你是註定要打敗仗的。但是從理論上講這個國家還是由加納政府統治的,實際上你這個政府還沒有共產國際匪諜的錢多。當然,你自然而然會做出相應的推論:這些錢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你在早期可以打土豪分田地,把沙皇和地主資產階級的錢拿來用,所以你才可以直接賣珠寶,但是後期這些都沒有了,錢從哪裡來?那當然就要問集體農莊的那些農民是怎麼死的了。這樣一來,整個思路就可以理清了。這應該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據我所知,好像以前沒有人搞過這樣的事情,這樣的比較方法以前從來沒有人搞過,包括西方人都不去算這個賬。
[00:49:27] 其實,共產國際從西方轉向東方,財政上的因素是很明顯的。在《007》的作者和他的女朋友正在蘇格蘭的工業基地活動的時候,列寧同志就把他的匪諜任命為蘇聯駐格拉斯哥的領事。這跟張作霖必須抄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和蘇聯使館的道理是一樣的。他是外交官,但他不遵守外交官的行為準則,他把軍火和文件直截了當地運出來。順便說一句,蘇聯在德國也是這個樣子的,它在德國的公使館就是直截了當運貨的。所以德國內政部長就曾經酸過他們,說過風涼話:“他們除了顛覆材料以外,到底有什麼貿易可言?我們為什麼要辦貿易代表處?他們的貿易是什麼?除了顛覆材料以外就沒了。顛覆材料又是免費給的,哪裡有什麼貿易可言?”但是無論如何,他在格拉斯哥主持工運,這也是要花錢的。英國工黨當時已經是根深蒂固,它自己也是很有錢的。於是,雙方就打起來了。打起來的經歷有一部分被寫進了《007》小說裡面,但是當時《007》小說的作者還根本沒有想到冷戰會爆發,也沒有想到他將來在五十年代以後會寫《007》小說。但是無論如何,雙方就鬥了起來,鬥起來的結果是布爾什維克全被趕出去了。相對于英國工人來說的話,俄國布爾什維克其實是窮鬼。但是在阿富汗、廣州或者蘇門答臘,那就情況不一樣了。相對於窮途末路、在上海以炒股為生的蔣介石來說,布爾什維克就是很富有的人了。鮑羅廷拿出去的那些東西,放在英國和波蘭是要打敗仗的,放在廣州和爪哇就足可以雪中送炭,製造出一大批人。
[00:51:19] 這時候,歷史神話就要出現各式各樣的矛盾了。事實證明,所有人都是按照短期利益行事的。例如,孫文和越飛在上海談判的時候,按照孫中山的衛隊長馬湘(就是我上次講過的那個人,作為非法移民,差一點點就要被美國驅逐出境,在這個時候孫中山突然擊鼓招兵,要招敢死隊,於是他就抓住了救命稻草,跟了孫中山幾十年)的報告,當時大多數元老是反對的,只有廖仲愷和蔣介石兩個人支持,汪精衛不置可否。汪精衛變成左派是後來的事情。如果親蘇就算左派的話,當時他還不能算。蔣介石為什麼會支持是很簡單的:他是軍人,蘇聯的援助是集中的軍事援助,他是最大的受益者。他是直接受益者,別人只是間接受益者。而且,國民黨內的權力平衡會因此而改變,他在國民黨內的發言權會極大地上升。當時汪精衛和胡漢民都是國民黨的大佬,蔣介石算個毛。國民黨在軍事方面的大佬是許崇智和陳炯明,蔣介石是一個極不重要的小嘍羅。但是有了黃埔軍校、有了蘇聯援助以後,他就跳過了許崇智和陳炯明,變成跟汪精衛和胡漢民平起平坐的人了。
[00:52:39] 所以,國民黨後來的事情之所以會發生,從人情之常的角度來講是很明顯的。比如說,我為什麼一天到晚要歧視牛爺爺(推特:牛白 @niubai)?這個邏輯跟汪精衛永遠看蔣介石不順眼的道理是一樣的:“TMD,我跟孫中山同志一起混的時候,你蔣介石算個毛。你現在居然跳出來,擺出一副跟我平起平坐的樣子。TMD,我又想不出什麼辦法來整死你,實在是氣不過。”據說人類語言的產生就是跟人類的社交性有關,社交性本質上就是階級鬥爭。就是說,你隨時隨地需要知道,你同一個部落裡面,你周圍的人相對於你是上升還是下降的,而你對相對於你上升的人永遠看不順眼。正如戈爾·維達爾(Gore Vidal)所說的那樣,每一次我聽到我的朋友成功的消息,我都感到我自己的身上死了一塊(Whenever a friend succeeds, a little something in me dies.)。汪精衛和胡漢民對蔣介石的看法就是這樣的。但是蔣介石之所以能有這樣的進步,全靠蘇聯。這個跟汪精衛和胡漢民不一樣,汪精衛和胡漢民是在有蘇聯以前已經有相當的政治資本,怎麼樣都是大佬的。但是因為蔣介石後來搞了清黨,殺過共產黨,後來歷史發明家就把他發明成為真正的反共人士,把汪精衛發明成為左派。這就是低估了歷史複雜性。這個歷史複雜性,你得直接看原始材料才能看出來。
[00:54:04] 在當時我對此的感覺就是,你們全都在胡說八道,需要我來給你們清理一下,正本清源一下,證明你們全都是傻瓜,同時製造出一個讓所有的匪諜全都沒有辦法反駁的論證。例如像楊奎松那種人,他像研究中國文化的金觀濤一樣,一本正經地研究斯大林和毛澤東之間的來往電報,論證朝鮮戰爭到底是斯大林要打的還是毛澤東要打的。這都是純屬扯淡的事情。你只需要研究一下滿洲的鐵路網是誰在經營,如果蘇聯專家走了以後毛澤東有沒有能力經營,這些偽問題就是根本沒有必要考慮的。考慮這些偽問題無非是為了造成一個印象:斯大林和毛澤東是平起平坐的領袖,他們之間在做出決策的時候還需要相互討論一下。按說的話,我這本書寫出來以後,像劉統這些人就應該當眾切腹自盡。但是他們現在並沒有切腹自盡,因為從理論上講,淪陷區以外出版的書是不存在的。你不能引用它,所以它就不存在。
[00:55:11] 你可以看出,防火牆的用處是什麼呢?它營造出一個特殊空間。在這個特殊空間裡,楊奎松和沈志華就算是最先進的、引用秘密史料最多的人。大多數人都像是我們敬愛的何清漣同志和韓國瑜同志一樣,講的都是中學教科書上告訴他們的那些東西。但是如果把牆拆了的話,比如說把柏林自由大學成批量出版的那些蘇聯信件和原始材料拿出來出版的話,那麼這整個體系都要倒下去。所以,這個牆是一定不能拆的,它像關稅壁壘一樣有必要。關稅壁壘如果拆了的話,本國的很多企業是不是都要破產?你想,防火牆是在保護誰的?首先就是保護他們的。當然,等到他們保護不下去的時候,習近平要自己赤膊上陣的時候,他們也就沒有用處了。他們存在的目的就是讓共產黨省點子彈費。如果你完成不了這個任務、讓共產黨必須多花子彈費的話,那麼TMD要你何用?你為什麼不去下鄉支邊,去給貧下中農提高一下文化水平呢?所以,表面上的敵人實際上是相輔相成、相互依託的。例如(這件事情是真實的),法輪功剛剛產生的時候,我們敬愛的江澤民同志正在準備精簡機構,把共產黨黨政部門支付的所有文化項目統統砍掉。那時候國有企業都砍掉了,你們這些廢物消耗的預算也不算少。但是法輪功一出來,黨就改變主意了。如果把這些人砍掉了以後,意識形態領域宣傳豈不是要被李洪志他們占去了嗎?看來你們還是有點用處的。不但不能砍,還要多給一些經費。這就是雙方之間的真實關係。
[00:56:54] 《遠東的線索》是赤裸裸地為這個目的而產生出來的,所以它的時間性其實是很強的。冷戰以後關於臺灣的那部分,實際上是輔助性的,只是順便在樹枝上掛了一些史料上去,其主要目的並不是為了臺灣本身。寫《遠東的線索》的那個時代,我是以麥卡錫主義為主打的。我是按照我自己的環境確定主打方向的。如果我的環境是以民小為主的話,那麼我的主打方向就是麥卡錫主義;如果我的環境是以共產黨頑固派為主的話,那麼我就是市場經濟自由主義者。總之是,由市場經濟自由主義者變到麥卡錫主義者,這本身就反映了我的階級環境發生了相應的變化。第一,離體制的距離拉大了;第二,階級地位相對上升,以至於原先的主要鬥爭對象在我看來已經是沉在下等階級裡面,不值得對他們進行鬥爭了。主要的鬥爭方向是把廣大民小拉到麥卡錫主義的方向來,《遠東的線索》是服從於這個目的的。但是後來我到了美國以後,從我的角度來講,等於是階級地位進一步上升。這時,我周圍已經全都是麥卡錫主義者了,因此認同中國的人就要變成打擊對象,儘管倒退兩年他們還是統戰對象。而原先的民小在現在看來已經失去統戰價值,你愛死愛活跟我沒有什麼關係,你跟你自己環境裡面的麥卡錫主義者去鬥吧。
[00:58:31] 所以,現在我就不再寫《遠東的線索》了,甚至把共產國際那一本書拖了下來,而是十分積極地去寫比如說《巴蜀利亞民族史》這樣的書。而且,違反我自己原來的做法,早在書寫完以前就把零星的材料放出來做講座。這種東西是違反我的美學偏好的。按照愛因斯坦的說法,理論家製造體系的目的是美學上的。在智力比較低的人看來,世界是一系列片段,彼此之間沒有聯繫;但是在目光深刻的人看來,所有的表面現象背後都有聯繫,把這些聯繫總結成為精美的體系是很好的,是很美的,這就是根本。而且,他判斷一個理論正確不正確,第一個理由就是美學上的。他說這個理論不正確,說上帝不應該擲骰子,因為這樣搞出來的理論不夠簡潔優美。真正深刻的大統一理論,最明顯的特點是,它應該是簡潔優美的。你們搞出來的東西不簡潔不優美,所以它頂多是一個局部的理論,不可能是大統一理論。我能理解這一點,就是說我製造理論的動機也是這樣的。所以,如果我不把理論搞得完美無缺,是不肯拿出來的。其實,民族發明理論我自以為我還沒有搞得完美無缺,但是我卻提前把這些各種枝節性的東西統統拿出來,當然是為了政治鬥爭的目的,就是為了在海外的麥卡錫主義者圈子當中解構大中華主義,把他們改造成為滿洲愛國者、南粵愛國者、巴蜀利亞愛國者等等。做到這一點以後,他們作為麥卡錫主義者的身份是不會有任何問題的,因為他們已經是不可救藥的反動派了,所以要把他們往更反動的方向推一推。你看,共產黨統戰的目的是把任何人都相對於原有的位置往進步的方向推一推,而我是把他們相對於原有的位置往反動的方向推一推。
[01:00:29] 我在武漢的時候認識一個很年輕的傳教士,他曾經跟我說:“你不要看很多基督教徒是壞人,不是這個樣子,你要看看他在信仰基督以前是什麼樣的人,信仰基督以後是什麼樣的人。一般來說,他現在雖然是壞人,但是比起信仰基督以前,他的生命狀態還是好多了。當然,他現在還是壞人,因為所有人都是罪人。而且,一個人總是惡習難改,總是不斷要舊病復發。但是相對來說,他已經是在往向善的方向走一走了。你不能對所有人用同樣的標準,有些人的起點是比較高的,有些人的起點是比較低的。我們起的作用本來就是,即使是對起點很低的人來說,我們也使他稍微變好一點。如果按照你那種高標準的話,那麼世界上有一部分人都是活該死的,這些人是註定要被像你這樣的自由主義者和自以為正義的人拋棄,變得一點希望都沒有了。而只有基督徒才肯給這些確實是罪惡深重、按說是應該萬劫不復的人一點得救的希望,這些事情只有我們才肯做。”也就是說,他們實際上也是這個樣子的:對每一個人來說,以他們自己的原始狀態為出發點,把他們往好的方向引一引。而撒旦的門徒則恰好相反。例如,把所有的社會上的不滿,無論有關無關,都盡可能引向破壞的方向,往壞的方向引一引。但是兩者之間有一個相同點:它們都不是一刀切地制定一個抽象的標準,而是根據每一個具體的人和具體的事件的原有情況。只是一個往好的方向引、一個往壞的方向引而已。
[01:02:07] 我跟這些人的關係也是這樣的。我引導的方向是不一樣的,要看我自己當時的位置和他們所在的位置,但是我是始終把所有人都往反動的方向引的。於是,就產生了很多本質上像馬克思和列寧的雜文性和政論性著作一樣是屬政治鬥爭產物的東西。但是按照技術性角度來講,例如《遠東的線索》比起《經與史》來說更能稱為學術著作。學術著作的關鍵就在於格式以及注釋。如果每一步都有注釋,那就算是學術著作。但是它背後的動機是什麼,用這樣的技術性標準是衡量不出來的。按照法律形式主義(Legal Formalism)的觀點來看,你做某一件事情真正的動機是什麼是衡量不出來的,你只能夠衡量發生的事實。從發生的事實來講的話,《遠東的線索》當然是更學術的東西。其實,民族發明學這些著作還要比《遠東的線索》更學術一些。跟何清漣想像得相反,我製造出來的《巴蜀利亞民族史》,例如論證古代巴蜀利亞是波斯文化的產物、是美索不達米亞文化的產物以及是二郎神的信徒,是極其實證主義的,比她閉著眼睛想像出來的二裡頭那些東西(注:見何清漣推特 @HeQinglian 2020年3月2日左右的相關推文)是要實證主義得多。她當作是極端思想的那些東西,反而在我的所有著作當中是最實證的;她認為比較稀鬆平常、比較溫和的那種東西,其實反倒是意識形態的建構。
[01:03:37] 比如說二裡頭這個東西,二裡頭是五十年代發現的,在七十年代以後被發明成為夏。但是跟殷墟不一樣,甲骨文證明殷墟確實是殷的。當時的考古學報告認為二裡頭是早商文化,也就是說是產生殷商的那個文化體系,可以劃成殷商前期,也可以劃成產生殷商的文化母體,但是沒有說它是夏。後來被建構成為夏,是為了強行支持“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理論體系。但是在她這樣的外行和落伍分子看來,這樣的東西是很溫和很王道的,而我製造的那些關於三星堆和波斯文化的東西是很離經叛道的。但是從實證主義的角度來講,我製造的那些東西全都有考古學和文獻的證據;而她說二裡頭是夏這件事情,除了她自己這麼說以及她學習的那些中華民族發明家是這麼說以外,完全沒有一個字或者一個物體的支持。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二裡頭產生的時代很晚,比三星堆要晚得多,它在技術上又比三星堆要落後得多。無論是財富還是技術,都要比更早的三星堆、鄂爾多斯的古城、李家崖文化要落後得多。它本身就是中國窪地的一個證明。它位於黃河中游,中國的核心區,產生的時間晚,卻比產生時間更早的鄂爾多斯高原和巴蜀盆地更落後。這就好像是,今天中國的技術比起日本七十年代的技術更落後,是同一個道理。說明技術傳到你這裡的時間更晚,天花板要更低一些。但是她像所有的外行一樣,她其實沒有判讀史料和考古材料的能力。我想,她至少是看過二裡頭的資料的,但是她顯然什麼也沒有看出來。這種事情其實就是沒有經過系統學習的結果。這種東西像是學外語一樣,不是需要天分才能夠做到的事情。傻瓜只要按照一定的程序學,也是可以學到的。但她肯定是根本沒有花時間去學,就得出了這些結論。
[01:05:45] 大多數中國主義者都是跟她和韓國瑜一樣的。問他為什麼會是這樣,他會理直氣壯地說,這難道不是天經地義的嗎?例如韓國瑜說中秋節(2019年9月9日:“你們中秋節問問嫦娥支持台獨嗎?”),這照我看來就是送一個把柄給你,因為中秋節是眾所周知的一個洋節。但是你要是在廣大貧下中農那裡去說農曆是什麼曆,他們肯定會說是中國曆,他們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這是耶穌會製造的曆。小知識分子會想到這一點,但他們也不會想到,耶穌會的農曆以前的曆法也是元朝的穆斯林給他們製造出來的。像中秋節這個東西,放到廣大人民群眾心裡面,這不是中國還什麼是中國?嫦娥難道不是中國的嗎?但是很可惜,神話學就是對中國主義者最不利的學問,因為中國就是沒有原創神話。這件事情跟中國近代沒有原創意識形態是一樣的道理。“主義”就是外來名詞。共產主義是外來的,自由主義是內生的嗎?憲法是內生的嗎?沒有一樣是內生的,全都是翻譯過來的。所謂的中國古代神話,無論是漢代的神話還是唐代的神話,所有的角色都是外來的,跟西遊記裡面的那些神一樣,還有很多是印度人的名字。而且最要命的就是,漢代的神跟唐代的神不是同一個系列的,就跟唐太宗並不是漢武帝的後代是一個樣子。唐代的神是南北朝的印度-伊朗神的後代,跟漢代的那些有美索不達米亞風格和早期伊朗風格的神不是同一系列。所以,早期莊子和列子、漢晉時期文獻中提到的那些神,以及漢墓裡面描繪的那些神,到唐朝,就像他們的統治者和居民一樣,整個被洗了一通牌。
[01:07:38] 第一,它們沒有一個是原創的,全是外來的;第二,外來的還是滅絕了一撥又重新從外界輸入的,跟共產黨和國民黨是屬同一性質的。這種東西不研究還好,你一研究以後,比任何東西都更能證明,其實就沒有“中華文化”這樣一個東西。但是,這個東西是怎麼製造出來的?答案就是,它是在張之洞那個時代以後,在滿洲人已經衰微以後,廣大晚清士大夫階級發明出來的。他們到古代文獻中去找了祖沖之或其他什麼人,為了在洋人面前證明我們過去還是有一點東西的。他們漸漸製造出來,但是那時候是分散和不系統的。到國民黨的時代,特別是到抗戰時期,就產生了像李約瑟這樣的人,把整個東西都系統化起來。然後七十年代的中國共產黨在放棄國際主義以後,把這些東西進一步地完善起來,把全部學術資源都投到這上面去。你以為是很古老的東西,其實真正的歷史是極其短暫的。不要說別的,它比我自己的家譜都還要短暫得多,它是完全後來的東西,所以我很有底氣地要顛覆這套東西。但是我也可以想像,有很多人的家譜,比如說向榮和劉耀春的家譜,可能就是從1978年開始的。對於他們來說,中華民族就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而韓國瑜的家譜肯定比國民黨黨史要短,所以他才會以為這些東西是理所當然的。我不知道蔡英文的家譜是怎麼樣的,但是霧峰林家的家譜肯定比中華民族的歷史要長,所以他們大概就不會很容易信仰這一套體系。
劉仲敬先生最新著作《文明更迭的源代碼》三月底出版,購買地址: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52365
出版後,將會進行作者簽名售書拍賣活動,詳情請關注燈盞社推特 @luminasociety
更多劉仲敬先生最新文章和視頻,請加入劉仲敬文稿站(lzjscript.com)會員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