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更多向不可能開放的經驗
閱讀時間約 13 分鐘
人是觀念的動物,不活在現實中,而是活在思維的空間裡。
所以唱歌時雖大喊「同一個世界,同一首歌」,而其實對世界的想法人人不同。同一件事,也是理解各異。每個人都在疑惑、都在嘀咕:「他這是怎麼想的呀?」
怎麼想的,就是思維模式的問題。
每個人的思維模式都不一樣,所以父母子女都常難以溝通,更別說民族之間了。
但思維模式也不完全都是個別化的,只有差異,沒有雷同。在一個群體、一個地域、一個時代之中,這群人的思維自然就會有些共性。所謂的「文化」,大抵就是指這群人通過其共同思維所創造出來的具體想法、制度、生活方式、行為傾向。就像有哪個地方鯉魚、螃蟹、兔子氾濫成災了,中國人必跌足嘆息:哎呀,何不讓我們去吃?
古人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講的就是這個。中國跟西方總總矛盾、不理解,包括具體想法、制度、生活方式、行為傾向上的隔閡,也有許多就在思維模式這根子上。
我現在不能講得太細,僅就大的思維框架上略作介紹。先講世界觀。
希臘傳統思維模式從巴門尼底斯(Parmenides)區分真理與俗見、柏拉圖區分理型世界與現實感官世界以來,在存有論上便有真實與虛假之分,在價值論上也有價值真假之分。依這個兩分的模式,世界可劃分成一個真實且具永恆或完美性(perfectio)的本體界,和另一個較不真實也較不完美的感官界。
這種二分模式,或被稱為兩領域定理(Zweisphärenthenorem,指本體與現象之分)。自柏拉圖以降,可謂一脈相承,影響深遠。至康德,翻轉過來,認為現象界是真實的,本體才是一種權宜概念(Problematischer Begriff),並非實相。
但這雖逆轉了柏拉圖以來的真假區分與價值判斷,且謂柏拉圖硬說現實世界虛妄不實是自作孽,可是整個兩分的模式並未突破。本體與現象之分,依然是西方最重要的思維模式。
據柏拉圖說,先有床的理念,才有具體的床。後來亞里斯多德再區分道:床有床的質料部分和形式部分。
兩分的思維,就是將物事一分為二,A與非A;A之中再分成A-1、A-2,非A也可再分為二,一直分下去。
這是整個分類學的基礎,也是邏輯的起點。因為A與非A,形成「矛盾律」;間並無另一物,兩者為相排斥的窮盡關係,則是「排中律」。依此兩分之法,主客分了,理性感性分了,本質與現象分了,一般與個別也分了。主體之中,又可再分為心靈與身體;客體事相,亦可分為實體與屬性;凡此等等。
在兩者之下,界定或描述所分的兩個部分,則有本體與現象、質料與形式、主體與客體、真實與虛假等。運用這樣的兩分以及這類區分二者的語詞,西方思想家雖然每個人各有創見,卻幾乎都以此思維著事物、論析著世界。現在,深受西方思維影響的中國現代菁英也常會說要「透過現象,掌握本質」。
除了兩分法以及兩領域論述之外,希臘傳統在思維上還廣泛運用範疇(Category)。運用範疇,主要是用以描述自然世界。據亞里斯多德之見,描述事物時可用十個範疇去描述:
實體(是什麼?) (實詞)
分量(什麼大小?) (形容)量
性質(什麼性質?) (形詞)質
關係(什麼關係?) (形詞)比較
場所(什麼地方?) (副詞)地點
時間(什麼時候?) (副詞)時間
位置(什麼姿態?) (動詞)關身態
狀態(具體什麼?) (動詞)完成式
動作(做什麼行動?) (動詞)主動態
被動(接受什麼行動?) (動詞)被動態
這十個範疇,後來成為西方思維並描述物事時的重要方法,也有些人予以損益,發展了不少引申範疇(predicables),形成一個陳述網絡。對西方經驗科學的發達,極具影響。甚且被認為是人類普遍具有的內在化的「認識能力」。
可是這樣的認識能力,並不是所有人類都有或應該具有的。因為認識或表述世界的方法,正因文化不同而有所差異。在不同文化傳統中或不同時代中,人可以「看」到意義不同的「世界」,因為看的方法本來就不同。
中國在春秋時期即已具有的思維模式,大抵也是兩分,例如「本-末」「陰-陽」「始-終」均是兩分。
然而兩分皆不涉及價值上的真假,而是性質上的比較。較重要者為本,較不重要者為末;較偏於剛者為陽,較少剛者就是柔是陰。因此既非真假,亦非相對立互排斥之兩端。兩端且是相依相待相需而成。物極者必反,如卒者若環;攻乎異端,乃得中庸。這些,都迥異於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的思維。
亞里斯多德的十範疇,傾向於對事物做確定的描述,是客觀性的說明。我們講「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則重在體會事物內部之關係。這也是中西之不同。
熟悉中國人思維的人,都曉得中國人辦事時有多麼講究關係。其實面對任何事務都是如此,著重於去體察、體會事物與事物之間的關係或事物內部的關係。
關係的認定,有許多地方非十範疇所能奏功,須恃乎體察。因此中國人俗話說「找關係」,關係確實是找出來的。一件事的本末、輕重、終始、陰陽或者與什麼數相繫,每個人認定都會不同。《左傳》莊公六年說凡事「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度,就是挈量長短、仔細揣量的意思。
度,本身是計長短的單位,原應求其客觀準確,但中國人說「度」卻往往不然,更多的是心中的體會。例如說「審時度勢」「他人有心,餘忖度之」之類。計量時,若說「以某某為度」,指的也是一個大概的約略數,到底可以比這個「度」長多少或短多少,須由人自己去審酌情況。
因而,對關係的揣摩度量、體會玩察,顯示了一種非理智邏輯客觀知識性的思維狀態。這種狀態本身就與二分法、十範疇或「知識量表」式的認知模式不同。
揣量衡酌、拿捏分寸,本於心中對該事之體會,來決定我們對它的認識以及應採取態度或行動。這種審度,又著眼於我們對於事物間關係的判斷,某事與另一事有無關係,找不到得出關係,或一事中某個部分與另個部分的關係何在,都取決於我們的關係性思考。
關係性思考,是說一事通常不是孤立的,必與另一事有關,事物也應在關係、關聯或脈絡中才能被認識。
例如要明白什麼是本,得同時知道什麼是末;要了解陰,得同時了解陽。同異、有無、進退、高下、短長、前後、美醜、虛實、強弱、動靜、開合、榮辱、古今、清濁、曲直、多少、新舊、輕重、成敗、巧拙、生死、子母、上下、先後、存亡、遠近、奇正、彼此、大小、正反、主客、左右、凶吉、得失、終始、寒熱、生滅、貴賤、明晦、損益、厚薄、取與……等各類相對語詞,瀰漫在一般用語及思想性文獻中。這些,都是要由彼此相待的關係中去理解的。
這跟西方常以定義一事物的方式,對一物予以定性定位,非常不同,強調的是其關係與脈絡。
例如「彼」「此」,誰是彼、誰是此,要看在什麼場合、什麼脈絡、用什麼東西來比較。物無非此也,亦無非彼也。
正如跟天地比,泰山就小了;跟細菌比,螞蟻就大了。故大小彼此等詞,不僅本身顯出一種相互關係,這種關係也呈現其脈絡義,讓我們明白一事一物均非孤生自成,而是在關聯與脈絡中顯其意義與價值。
關聯性思考,注意彼此的關係與脈絡,即必然帶動「聯想」與「取譬」之思維。何謂取譬?《論語.雍也》有言:「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謂能夠處處以自己作比喻,可稱得上實踐仁德的方法。《說文解字》:「譬,喻也。」故取譬,就是「以什麼作比喻」之意。
《論語》取譬之處就甚多,如「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譬如為山……譬如平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歟」「譬之宮牆……」「譬道之在天下」「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墨子》一書更有〈大取篇〉和〈小取篇〉,取即取譬之取。可見取譬之法是先秦諸子通用之法。
而且我們看《論語》,凡涉及孔子核心思想範疇的語詞如仁、孝、禮等,均以比喻作答。
以仁為例,《顏淵》:「克己復禮為仁」;又「樊遲問仁,子曰愛人」。這些是抽像地對「仁」作比喻。仁的具體化是仁者,即有仁德的人。《論語》更多地是對仁者比喻作答。《里仁》:「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雍也》:「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仁者樂山,……仁者靜,……仁者壽」「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子罕》:「仁者不憂」;顏淵:「仁者,其言也訒」。由這些地方,可以發現《論語》沒有一處對仁作「屬加種差」式的定義,甚至有意迴避對仁下定義。此即取譬式思維方法與亞里斯多德式方法絕大的差別。
據胡適說:「一個中文的命題或者詞,和西方的與之相當的東西的不同,在於系詞。系詞在西方的邏輯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在中文的命題裡卻被省略,它的位置僅用短暫的停頓來表示。……在西方邏輯中,圍繞系詞發生出來的一切神秘的光暈就這樣被消除了」(先秦名學史)。因為西方自亞里斯多德的《工具論》以來,就是以判斷系動詞來建立整個邏輯學的。
在存有論中,所謂「存在」直接關聯到判斷系動詞「是」;而且「是」是一個與其它思維世界、可感世界沒有內在必然關係的獨立自存世界。
在認識論方面,柏拉圖舉「一」和「是」兩個字為例。當「一」和「是」未結合時,它們分別自成一個封閉的世界。若二者結合,即「一是」時,就產生了許多意義世界的變化。「一是」中的「一」和未經與「是」結合的「一」就有差別,在「一是」中的「一」已蘊涵了部分與整體等意義世界。同時,「一是」中的「是」是未經與「一」結合的「是」亦不同。「一是」中的「是」已成為聯繫特定主詞、揭示特定關係的「是」而非原來僅表示自身是一種存在的「是」(見〈巴門尼德斯篇〉)。
這種思維方式的後果是:世界上萬事萬物及相應概念都被分成了兩個世界,如「實體與屬性」、「本質與現象」等等。而這些關係的兩方並不存在一一對應的關係。
亞里斯多德則在《工具論》中將世界分成兩類實體,即第一實體(個別的事物,如個別的人)和第二實體(一般的事物,如人這個「種」和動物這個「類」)。據他的看法,在一個由「是」構成的判斷句裡,第一實體不能被第二實體斷言。因此不能說「人是某人」,只能說「某人是人」,也就是第二實體被第一實體斷言。另外「種差」也不依存於主體。如「陸生的」「兩腳的」等種差可以被斷言於人這個種,但這些種差卻不依存於人。如「人是陸生的」,不能倒過來說「陸生的是人」。所以,主詞與賓詞、第一實體和第二實體等,一個由「是」構成的判斷句裡,前後項都不是相互對等的關係。總之,「是」(或存在)這一語詞世界和思維運動導致了以上哲學認識論、存有論的諸多變化。
中國的情怳則完全不同。先秦文獻中判斷系動詞已呈弱化狀態。弱化,意指:
(一)判斷句可不用判斷系動詞,而代之以「……者……也」等句式。
(二)「是」「為」等可充作判斷系動詞的字,其最初和基本的語義、功能都與判斷系動詞沒有直接關係。如「是」,《說文解字》云:「是,直也,從日正。」並註曰:「是,籀文是從古文正。」亦即是的最初意義為直、正,或為通常用語中的「對」。後又引申出「此」「這」等具有指示代詞功能的涵義。所以從詞源學分析,「是」不是一個判斷系動詞。
(三)在某些場合,「是」「為」等如用作判斷系動詞,都必須有某種特定語境和句式的限定。譬如在提問題身份的語境裡使用「是誰」句型。又如在比喻關係的語境裡使用「為」字。
以《論語》來看,〈陽貨〉:「偃之言是也」(正確,對);〈八佾〉:「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指示代詞)。另外,如「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夫顓臾,昔者先王以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此三句中的「是」均非判斷系動詞,而是用作指示代詞。
上述判斷系動詞的弱化狀態,使得說明一物通常不採用限定判斷語或種屬定義的方式,而須廣泛採用取譬的方法。在取譬思維方法中,任何事物都被當作不能分割的整體;任何抽象的概念都有現實具體的東西與之對應,對任何概念的說明都會先採用類比法。
這個道理,說來複雜,想必你已看暈了。但簡單地用中國話說,那不就是「比」跟「興」嗎?
比、興都是《詩經》中詩歌中的表現方式。比,當然就是指比喻,「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於歸,宜室宜家」,桃花之美,正像喻著新娘的嬌豔,以及花開即將結子的新婚景況。這就是取譬比喻之法。
興的問題較為複雜,或云為比喻之一類,或云為象徵,或云為無端起興。但無論如何,都是聯類性的思考,而且所聯之類乍看根本毫無關係。像「關關雎鳩,在河之洲」那般。河上沙洲的鳩,相互鳴叫著,本來跟底下要說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毫無關聯,可是藉此起興,想頭橫空而來,卻構成了彼此特殊的意義關係。此即為興。
宛若兒童遊戲時,一霎時興高采烈起來,折楊柳為馬鞭、堆沙石為城堡,宇宙萬匯、觸手牽聯,綰合捏對到一塊兒。此物彼物,捏合作對,若有意,似無情,又無端,又有趣。正如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下竟接盧江小吏夫妻分離之故事。這其間的審美性質、創造思維,豈西式理性推論、定義界屬云云所能臻哉?
這種中西思維異同的比較,看起來很嚴肅、很凝重,但你只要多體察一下,進取諸身,遠取諸物,一定隨處都可以找到許多有趣的例子。認識到這彼此的差異之後,當然可以發展優劣判斷,爭個高下,形成對立。但若能進行溝通理解、欣賞異量之美,就更好了。
一般說來,人都固執於自己的思維方式中,不太可能用另一套思維去想問題。因為外型易改、言詞可變,但思維方式是腦根子上的事,要改很不容易。可是若真能換個角度,用別人的思維方式去看世界,卻多能看出另一番景光。所以我們更需要的不是堅持壁壘,而是更多向不可能開放的經驗。
為什麼會看到廣告
66會員
268內容數
留言0
查看全部
龔鵬程大講堂的沙龍 的其他內容
你可能也想看
孩子教我的那些|禮物一定要用買的嗎?或許,路邊就會發現更多可能!禮物,之所以貴重,不在於金錢本身,而是那份心意,想著那個人的需求,然後挑選一份適合他的禮物,在合適的日子裡,送到他手裡,只要光想著,他收到的喜悅,那份感動就足矣了。


2021-09-28
孩子教我的那些|換宿不只一種想像,你可以,帶著孩子也可以,把旅遊活成更多驚奇的體驗!有孩子以前,我對打工換宿的概念,只限於個人的行為,直到有了孩子後,因為還想要繼續完成這個未盡的夢想,所以,開始在思考是否還有沒有別的可能性。


2021-09-22
我們有沒有可能活在一個不需要功成名就也能被溫柔善待的世界?如果把認同、愛或欣賞這些東西物質化,它有沒有可能其實是很貴的東西?


2021-08-11
「我們需要更充分利用『羅浮宮』這個名字」—疫情中創造多元收入,連《蒙娜麗莎》都能幫「開源」羅浮宮作為 2019 年全球參觀人次最多的博物館,以及法國博物館的龍頭,預估過去半年因疫情閉館的影響,整體虧損超過 9,000 萬歐元(約台幣 30 億),使得一些正在進行或預計辦理的計畫不得不暫緩,疫情造成的損失涵蓋了有形與無形範圍。


2021-03-31
比起緊抓不放,放手需要更大的決心 — 麻姑神德魯納酒店 Hotel del luna
第五集「來自陰間的新娘」教了我們「放手的勇氣」,準新娘秀敏意外身亡後因為極度想要結婚而導致在陽間的未婚夫昏迷不醒,未來婆家為了兒子,擅自幫秀敏舉行冥婚。因為準夫家的出手十分闊綽,滿月便欣然答應承辦這場婚禮,但燦星的好友桑切斯卻成為了冥婚的新郎。


2021-02-17
《哈囉掰掰,我是鬼媽媽》觀後感 /「世上不可能有準備好要離別的人。」在現在全世界都倡導非必要不要出門時,所以小編幾乎每一天都在挖掘Netflix上有趣的戲劇、電影、節目,也從每晚衝電影院,取代成每晚回家盯著手機與電腦螢幕的Netflix狂K猛看。


2020-08-13
日子都是自己在過,我們也不需要那麽多的觀衆。我們總會聽到別人説,要活在當下,但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呢?
一切都要回到疫情發生的去年。年初,我換了份新的工作,新的工作讓我有了工作和生活之間的平衡 (work life balance),這是在我第一份工作的時候所沒有的,也是我一直以來想要的生活。
這一年,恰巧就讓我碰上了我很喜歡的偶像來新加坡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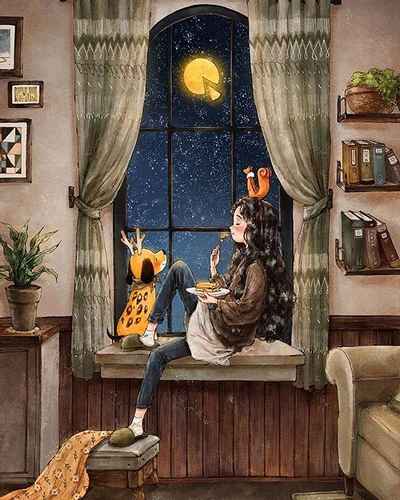

2020-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