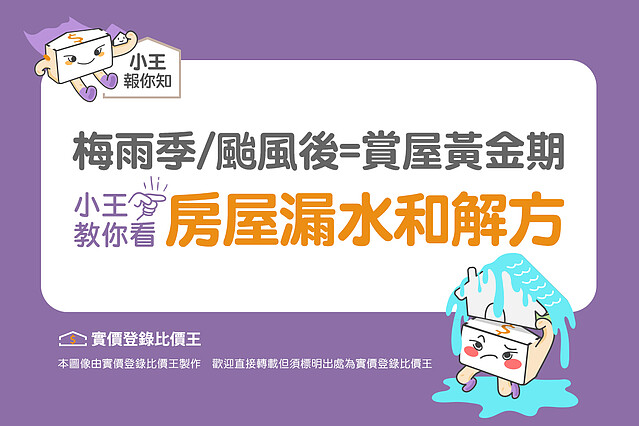作者:李鈞冠(臺大城鄉所碩士)
本文轉載自台北村落之聲夏季專題「狂熱城市」。氣候變遷愈加劇烈,意味著「災害」的發生愈加難以預估。災害的發生應當視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並在這樣的基礎上,重新思考社區之於災難容受力的韌性基礎。究竟城市如何應對災害的日常化?歡迎至台北村落之聲與我們一起思考。
對沒有實際經歷過災害的人來說,「災害」經常是一種超現實的體驗。
畢竟,災害的發生既無法預期,也是偶然才會發生。即使災害真的發生,一般人傾向將問題交給「專家」處理,政治人物及技術官僚通常也不吝大開支票,宣佈將在幾年內投入幾千億的建設計畫,來防止災害再次發生。將問題交給專家之後,災害彷彿又與人們無關。媒體報導所見的「非日常」景象,宛若電影情節的畫面,縱使當下感受甚深,對災害的記憶在幾天後,不免被新的生活訊息給沖刷殆盡。
然而,當我們將防災的問題交給專家與政府處理,專家與政府也大興土木打造各種防災建設,難道災害真的就不再發生了嗎?我們都很清楚,答案是否定的。當然,這並非意味著專業防災知識與技術是全然無用的,也並不代表那些斥資千億的防災設施是無效的,更根本的問題在於:我們對於災害的認識,已然無法跟上災害發生的頻率了。

以最常發生的水災來說,根據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統計,臺灣極端的豐/枯水期發生週期越來越短,已經緊湊到能在一年之內同時發生大規模的旱災與短時強降雨造成的水災。還記得嗎?上個月中南部正因五十年來最嚴重的乾旱而飽受限水之苦,然而當梅雨季終於在一個月後報到時,短時間內爆量降下的雨彈,反倒讓部分缺水地區成為水鄉澤國。
當旱與澇的改變只在一日之間,意味著災害的發生已然成為一種日常,我們即將邁入的是一個「與災害共生」的未來之中。不只過往對於災害的認識需要檢討,對於災害的應對方式,也需要重新調整。這點在人口大量聚居而與自然環境疏離的都市中,更是迫在眉睫的課題。
面對災害,硬體防災工程的侷限
所謂的防災工程,是以硬體建設打造出將災害隔絕於外的設施,最直接的如提防、擋土牆、排水道等等,更大規模的工程如1960年代以降,為了治理臺北水患而出現的基隆河截彎取直計畫。
這類防災工程背後,都會有一套對於災害發生頻率與強度的估算,將自然界的不確定性(風險)轉為可計算、可評估的對象,而技術理性則被視為執行風險決策的重要解方。以防洪為例,技術官僚在設計防洪設施時,會以「重現期」作為保護標準。重現期也稱作「頻率年」,即平均幾年一次的降雨強度;以機率來說,則為一年中可能發生的機率。以都市道路側溝設計為例,大多數是以2到5年為重現期,區域排水設計則多以10年重現期作為保護標準,當時雨量超過防洪設施所能承受的量值時,水漫四方的景況就會出現。實際上臺灣都市近年來遭逢的淹水,大抵上不脫上述原因。
越來越多的受災案例顯示,純粹以技術性的手段來控制災害風險的作法有其侷限。實際上,工程手段除了可能提高災害風險,甚至可能降低一個地區對於災害的耐受度。

例如,水泥化的河川整治美其名是為了加速洪峰通過,然而這樣的工程剷除了河川原生植被,既降低土地的透水能力,也因為減少了洪水流經時的阻力,當洪水溢堤時,對週邊地區的破壞力更為顯著;連帶地,水泥化後的渠道斷面難以加挖擴大、容易累積淤泥,反而降低水道對於洪水的容納量,一旦降雨超過一定強度、排水系統阻塞,抽水站更無法運作,連帶癱瘓的是整個都市防洪系統。

如今,降雨頻率與強度的極端化,挑戰了人們過去想藉由技術控制災害風險的想望:災害變得難以預測,難以預防。工程手段有時緩不濟急,考量到成本效益,也不可能與極端災害進行軍備競賽,一味地擴大工程規模。
因此,當代都市防災的思維,已逐漸從過往「工程至上、人定勝天」的避災邏輯,轉變為「還地於自然,與災害共生」的韌性(Resilience)邏輯。
堤防效應:真正讓災害發生的,是那些「安全」的假象
過去技術至上的防災思維,利用現代化工程將人從自然中剝離,認為一旦降低生活與自然的接觸,受到災害侵襲的可能就會減少。這種現代化的技術看似免除了災害發生的風險,實際上卻帶來更大的不可預測性:誰知道哪天水會真的淹過堤防?哪次降雨的泥沙沖積會堵塞排水系統?其所建構的安全體系,更降低了一般人對於風險的意識與應變能力,形成了矛盾的堤防效應(Levee Effect):人們誤以為自己身處在安全的環境之中,進而開發原本就容易發生災害的土地,結果是將自己置身於易受災害侵擾的風險之中。

因此,社會必須發展一套新的風險思考方式,來降低一旦災害真的發生時的後果。「災害風險」不再只評估災害發生的機率(重現期),也必須包含評估社會承受災害衝擊的能力,以及能否快速回復正常運作的韌性。
簡言之,原先「災害風險」的控制只取決於技術能力,如今則需納入社會韌性的培養,以應對不確定性風險。在這套邏輯思考中,自然災害不再只是藉由專家/技術所隔離的「非日常」現象,而是生活中「日常」會面對的一部分。處理災害風險的責任,不再只是委由專家處理,而是必須由社會中的每個人共同承擔。
與災共生,需要「韌性」相伴
這套觀念的轉變,體現在聯合國國際減災策略組織(UNISDR)2005年提出的〈兵庫行動綱領:重建國家與社區的災害韌性〉(Hyogo Framework for Action 2005-2015: Building the Resilience of Nations and Communities to Disasters)中。正如該份報告的標題所示,促進社區參與減災工作、強化社區面對災害的因應能力,已成為當前國際減災工作的首要目標。
而所謂的「韌性」能力評估,可以分為三個面向。第一是「災前」的自然環境與社會條件評估,例如該地區是否位於不易發生災害的地方、是否具有強力的社區組織能夠自我照護。第二是「災時」所採取的可能應變作為,例如無論社區居民或政府機關,能夠在第一時間掌握災情狀況,疏散災民以降低傷害。最後是「災後」的學習與調適,例如改變既有的產業型態,降低災害帶來的衝擊等。

臺灣自1999年經歷921大地震後,政府首次體認到民間及社區投入救災的重要性,同時因應國際減災工作的潮流,開始著手研擬「防災社區計畫」,並由臺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在全臺各地推廣、試行防災社區的操作。
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罕見的災害規模再次凸顯社區參與防災工作的重要性,也促使各主管機關依其業務職責,擬定「自主防災社區計畫」。例如內政部消防署推出「災害防救深耕計畫」,主要對象為都市社區;農委會水保局推動「土石流自主防災社區計畫」,主要對象為山坡地社區;經濟部水利署則提出「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計畫」,對象涵蓋位於水災潛勢的社區。

韌性的社區實踐:自主防災社區的推動與創新
各主管機關的自主防災社區計畫,雖然會有執行及評比細節上的不同,但主要的操作方向還是大同小異,主要目標是建立社會韌性。首先,由地方政府評估災害脆弱性高的社區,委由專家團隊進駐輔導,對口以社區發展協會或村里辦公室為主。
在計畫執行上,以同時參與水利署「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與水保局「土石流防災社區」的宜蘭縣蘇澳鎮蘇北社區為例,蘇北里民在宜蘭大學團隊的輔導下,除了參與水保局「防災專員」的培訓課程,成為具備防救災能力的專業者;也藉由社區成員分享生命經驗、社區訪調與環境探勘,找出該社區容易發生災害的位置、標示易受災害的群體,由下而上擬訂防災計畫,彌補專業者僅藉由技術軟體分析災害潛勢區域的不足。

除了災前的培訓與計畫擬定,蘇北里長作為防災指揮官,也會在颱風豪雨期間,帶領社區防災隊員巡走社區,一方面進行防災實作訓練,一方面在第一時間向縣政府回報當前的社區狀況,例如是否淹水、路樹是否倒塌,以供縣府團隊即時採取應對措施。
然而對許多社區來說,自主防災社區計畫如果只有社區成員參加,對於災時的防救能量而言,絕對是不夠的,還得納入更多的利害相關人。而所謂的韌性,指涉的也不僅只是人力的動員,還必須包括完備的減災環境以提高災害容受度,以及儲備足夠的資源以提高災後重建的速度。
以參與「水患自主防災社區」的桃園市觀音區樹林社區為例,樹林里長除了組織社區的災害防救隊,也積極協調擁有閒置土地的地主,將土地提供給社區興建滯洪池,以減緩社區淹水的狀況。樹林里長更進一步與在地企業合作,將滯洪池打造為「蓮荷防災農場」,在滯洪池中養魚並種植蓮花、絲瓜,不但成為社區特色遊程的一環,也藉以推出荷葉養生茶、荷葉拉麵等伴手禮,打造能夠自給自足的防災社區。

從社區到群體:防災共同體的形成
自2000年代推動自主防災社區計畫以來,如今看似已初具成效。這個計畫所帶來的意義,絕不只是以「社區」為單位、培養社區居民的防災意識而已。早期針對「社區」的韌性防災,如今已逐漸往「區域」的規模邁進。
例如近期桃園市位於黃屋庄溪及埔頂支渠週邊的九個里,便採取「區域聯合防汛」的作法,各防災社區不再只是點對點式地向區公所回報災情狀況,而是讓位處於上游的社區能夠在第一時間,向下游的社區提出警訊,並由下游社區的居民協助上游居民撤離,形成跨社區的防災共同體。
透過上述自主防災社區的案例,可以發現許多社區已經強化了無論環境或組織上的耐受性,並培養災時的應變能力。有些社區甚至自主協調,降低土地使用的強度,將原本可能被水泥鋪面覆蓋的土地轉型為滯洪池、形成社區的自給經濟來源,而有利於社區的災後復原能力。
重新學習與災害共處,人們重新打開了自己與自然的邊界,藉由一次次的災防演練,將對災害的記憶銘刻至自己的身體裡,並從技術官僚身上拾回應對災害風險的責任。認識自己所處的環境、擔起自己行動所應負的責任、建立與自然/社區與他人的連結,這不僅是以韌性防災的意義,也是作為民主公民的意義。
結語:都市規劃的韌性再思考
面對防災議題,即使整體防災的觀念已轉向與自然共生、社區也逐漸建立起韌性能力,但面臨實際的都市開發議題時,卻並不總是能記取歷史教訓。本文最後想以社子島開發的案例,作為反思結尾。
臺北市士林區的社子島,位處基隆河與淡水河交會之處,屬於洪氾區。1960年代行政員提出臺北防洪計畫時,將社子地區視為臺北市的滯洪池,將該區排除在堤防之外,並由經濟部頒布限建令。隨著員山子分洪道的開闢,社子地區作為滯洪池的重要性降低,臺北市政府在2014年決定「生態社子島」的發展定位,將社子島堤防上修至200年重現期洪水標準,增加其防洪能力,並將其都市計畫的容納人口從1萬1千人提升至3萬4千人,增加土地利用強度。
在這樣的開發邏輯底下,正陷入了先前提到的堤防效應的問題,隨著開發人口的移入,將使更多人暴露於受災的風險之下。而為了生態社子島的開發,臺北市政府計畫執行的區段徵收,更可能導致大量居民被迫遷移,使當地的聚落紋理與社區網絡形成真空,更不利於當代減災工作的推廣。

當前的防災工作已將責任下放於社區之中,不過對於都市發展能否以建立與災共生的社區韌性為基礎規劃,仍是需要我們持續關注與思考的課題。
➤ 延伸閱讀:不怕水淹,更要與洪水共生!打造具有「承洪韌性」的城市培養指南
首圖來源:incent Sheed /CC BY-NC-ND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