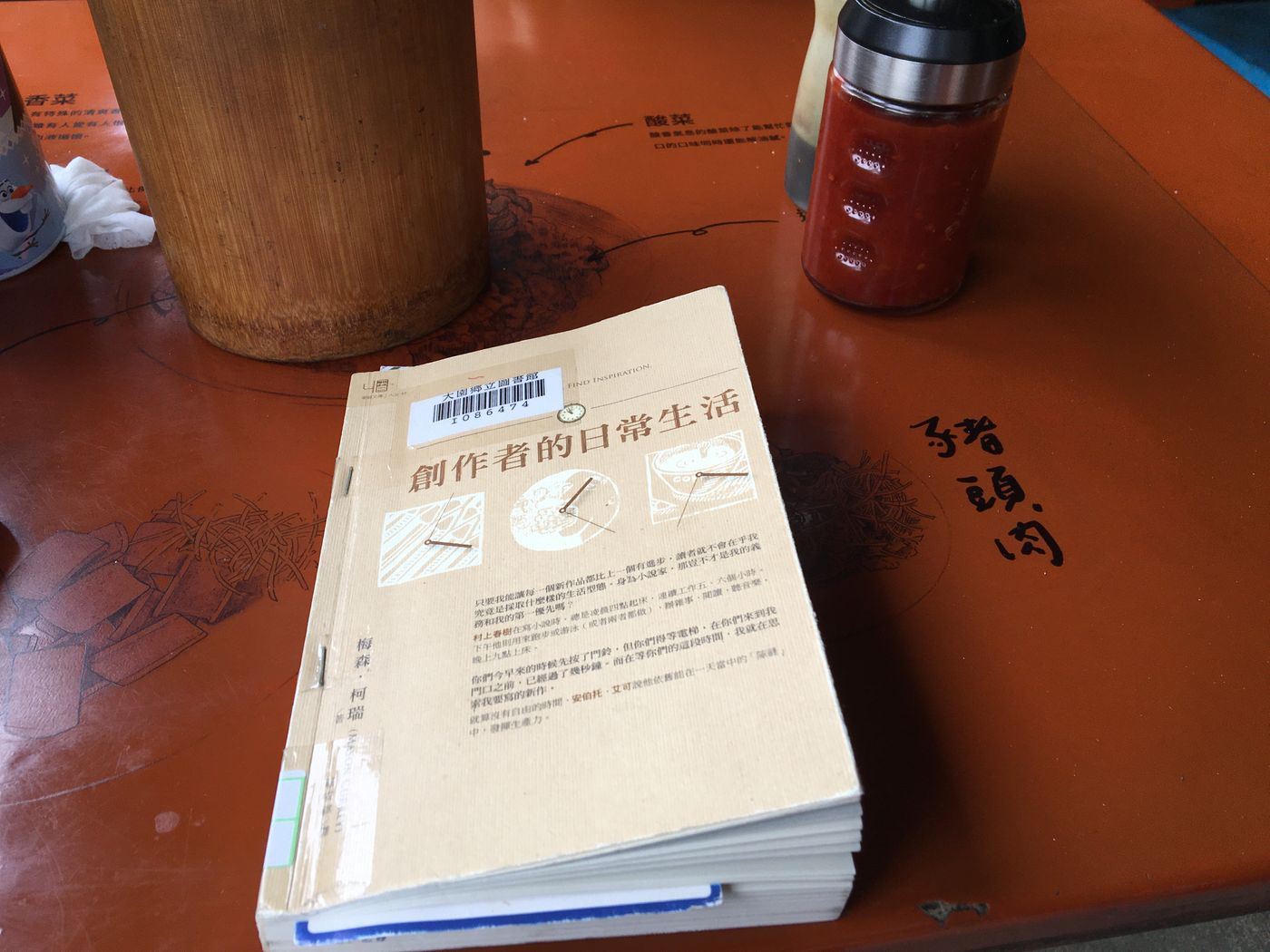每當我讀了書,裡面有觸動我的章節與故事,總是胸腔裡的五臟六腑都在沸騰著,腦袋過於急轉,作家寫出我想說的,或是我想忙著呼應的,他們的字到達了我想去的地方,或是故事如大雨直接澆下,從頭到腳都被那字裡的重墨染透。
小時候我很愛讀小野關於家庭的一系列出版書,談他的父親,母親,妻子,兒子,女兒。依稀記得作家寫道,一家人去賣紅豆湯好像也不錯。
我家那時正在賣紅豆湯,我貧瘠的渴望著那樣中產的生活,知識份子的父母,會說故事給孫輩聽的奶奶,懂得傾聽孩子心聲的家長。我的零用錢努力攢著買書,每當我坐上287公車到台北車站,我會在重慶南路的隨便一家書店買看來順眼的書,在華南銀行總行公車站前,等往內湖的回頭車路線,可以安心的佔據最後幾排的窗邊位置顛簸著看書,行經台北車站,人潮一湧而上,縮在後方的我可以心理得的不用起身讓位,不用拉著吊環與他人併肩搖晃著三十分鐘的路程回到內湖。或是,去圖書館借一大落亦舒的小說,在麥當勞裡一根薯條一根薯條的吃著,讀著。移動的過程,將自己置在一個公眾的空間裡,現代的人盯著手機,拿出書來讀的人少了。
高職時我無心聽課,我過度自負聰明,不想接受大考的壓力測試,申請學校抵定後,就業或補習班等與我無關。坐在教室後排讀村上春樹的「地下鐵事件」,坐在我前方的溫柔少女同學回頭看我在讀什麼,竟難以解釋,她的耳洞左右穿了數十個,猶如天線般可接受大量資訊,也像針灸後未拔除的針,這才是閃耀的青春。
在湖口時,新的校舍新的圖書館,我不是在往圖書館的路上,就是在宿舍裡閱讀,讀圖書館的書,新圖書館的第一次借書比賽,我是第二名,第一名是當初打電話給我通知我錄取了,那位職員。
二十四小時的誠品有大群文青的夜貓,各自捲縮在某個木質書櫃下方或階梯,捧著最新上架的書或雜誌,我喜歡找一個最沒有人會待的小角落,設計影像類,影相圖文集那裡,算是小眾,我隨手抽出了瑪丹娜尚未被封膜的全裸影像集,拍照,可以這樣拍,裸露不是色情,是藝術。
內湖到哪裡坐公車都需一番周折,袋子裡必定有錢包鑰匙與一本書,我可以在台北城裡的公車上,晃悠著,看上下車吞吐的人,看眼前的書,沒有目的地,只是閱讀與觀看。
終於我抵達了一個充滿書的屋子裡,窮的只剩下捨不得割捨的滿滿書藉,各種類型,文史哲,東方文學西方文學,心理學,建築學,電影書,繪本書,卻失去了那偷來時間一段,在搖晃的移動中讀書的專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