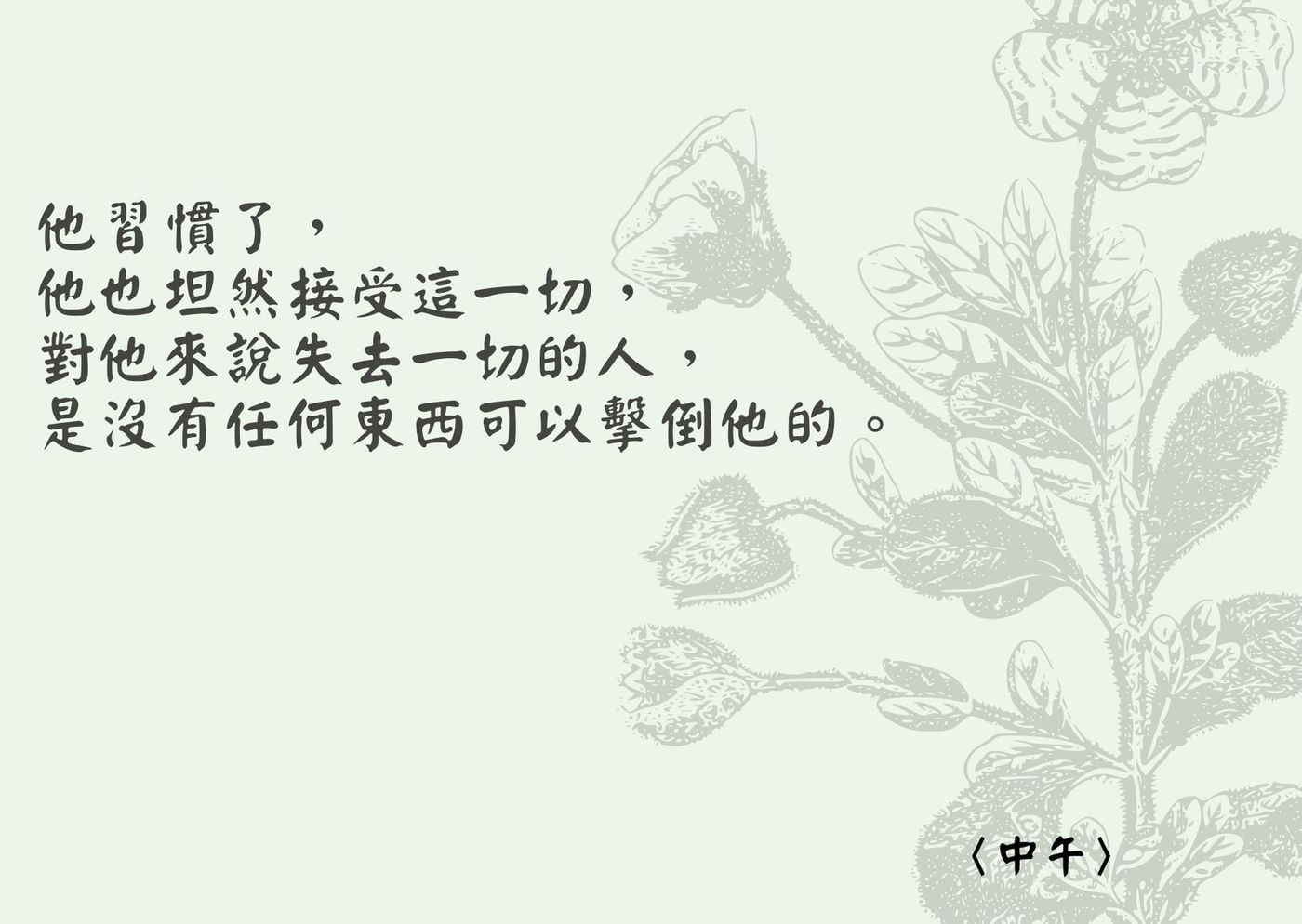他走向前,從口袋裡摸出所有的零錢盡數投入打賞箱中,老者照舊從袋中拿出一物要遞給他,黑褐色的棍狀物,表面浮著一層亮光,原來是阿勃勒的豆莢。
「裡面是大樹的種子,種在那裡都可以活。」
他接過豆莢,邊走邊漫無目的地拋甩著,心想著這豆莢雖然跟阿勃勒的花相比之下顯得平淡無奇,但是在不起眼的外表下包藏著是無數個堅韌的生命。手裡握著豆莢就像握著無數個生命,但是在他腦海裡裡卻搜尋不到任何可以栽種它們的地方。即使再強韌的生命,沒有生長的土地不也是枉然?
他穿過廟埕,彎進老街,橫越馬路,走入市場。晨間到市場採購食材的人群散去後,菜市場內的攤販正忙著打包剩餘的貨物,或者正忙著拆卸早晨辛苦架設好的攤子,將所有的東西成綑的綁妥,批次地搬上停靠在攤子前的貨車,另一頭正在興建的新菜市場則是有許多工人忙進忙出。
他看著這些人正在做著人力銀行中不會出現的工作時,覺得他們就像以前時常清理的彈藥庫牆角的雜草,水泥堆裡明明毫無生機,但卻仍然使盡全力穿透水泥牆,緊緊扎根在水泥底下的土壤中。
這些雜草是怎麼知道牆底下有土壤?或許唯有穿透牆才會可能有生機吧。
不遠處的騎樓邊,其中一戶鐵捲門上貼著寫著「租」字的鮮紅告示,告示底下裁成易於撕下的鬚狀紙條,上面印著房東的聯絡資料。告示與紙條讓他想起阿勃勒與豆莢成串相連的模樣。
他走向前,撕下其中一張紙條,謹慎地放入襯衫胸口上的口袋,想像著紙條像種子一樣在他的心上扎根,越扎越深。
他重新跨上摩托車,往家的方向前進。
「爸,我想做生意。」在晚飯時他趁著所有家人都在時,慎重其事地向全家人宣布此事:「現在天氣這麼熱,新市場那邊這個多工人,賣紅茶冰剛剛好,生意一定會不錯。」母親拉著他憂愁地問了許多的細節,需要多少錢?生意會穩定嗎?他耐著性子一一回答母親接踵而來的各種問題,一邊不安地瞧著父親的反應。
父親沉著地吃完晚飯,沒有如往常一般地再添一碗飯,默默地放下碗筷,走到屋外,從胸口的口袋摸出一包菸,掏出一支菸在牆頭敲了幾下才就著打火機的火光點起菸,蹲在門口,一口又一口,一支又一支抽著菸。
「這印章跟存摺是你的名字,你之前當兵拿回來的錢,全存在這裡」夜裡,他聽著腳步聲就知道是父親來到床前,卻不敢睜開眼睛,只好閉著眼假裝已經睡下了。父親知道他還沒睡,便將印章跟存摺放在他床頭,繼續接著說下去:「工廠的事不再考慮看看?」
父親離開房間後,他在黑暗中摸到堅硬的印章和柔軟的存摺簿,他將這兩個東西貼在自己的心窩上,想起小時候父親上完夜班後總會無聲地到他的房間來,為他的小豬撲滿投入幾枚硬幣,硬幣相互重擊著,噹啷,噹啷,在夜裡迴響著。(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