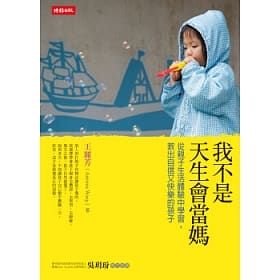「你現在有兩個選擇……」
有一回我太太在上藝術課時,遇到一個三歲大的孩子還沒收完材料就想要玩玩具的狀況。她跟孩子說:「現在還不能玩喔!要先整理好材料,才能玩玩具,這是我們的規矩哦!」沒想到他就爆哭,喊著說他想要玩。於是太太跟他說:「我知道你真的、真的很想玩玩具,但我要很認真地跟你說,你現在有兩個選擇。第一,把桌上的材料收完,你就還有十分鐘可以玩玩具。第二,繼續在這邊哭,直到媽媽來接你,但這樣就不能玩玩具了。」突然,這位孩子很神奇地就不哭了,立刻收拾桌面,甚至還幫忙擦桌椅。
我有時看太太跟孩子的互動,都不得不敬佩她的智慧,總能先肯定孩子的情緒、聽懂他們的需要、再解釋團體的規則,一步一步地引導他們。然而,跟孩子講道理、讓孩子有選擇權的教養方式,其實是晚近才在台灣成為主流的。還記得小時候,我在馬路上哭鬧吵著要買玩具,故意在斑馬線上走到一半就不走了。我媽沒有跟我講道理,也沒有給我選擇權。她只是不耐煩地回我說:「沒有玩具!你不走,我就先走了!」我只好放下自尊,哭著臉奔向媽媽。
我們的教養文化,歷經了很大的轉變。孩子從依賴於成人,轉變成權利的主體;教養方式從威權管教,轉變成重視說理、不打不罵;空閒時間從野放成長,轉變成規劃栽培。然而,儘管主流的教養腳本期待父母花更多時間投入在孩子的成長中,積極培育孩子的天賦與才能,但往往忽略不同階級的家庭,有不同的教養資源,進而將勞動或貧窮階級的教養方式貼上「疏於管教」、「不適任父母」、「不夠積極」的標籤。
不同階級的教養模式:規劃栽培與自然成長
談到不同階級的教養策略,就不得不提到美國社會學家安妮特‧拉蘿(Annette Lareau)的經典著作《不平等的童年:跨世代社會學革命性經典鉅著》(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她在本書訪談88個來自中產階級、勞動階級與貧窮階級的家庭,並進入12個家庭進行深入觀察,寫下極為豐富的民族誌研究。拉蘿透過不同家庭的故事,呈現階級作為社會結構的力量,是如何影響父母的教養策略,又為孩子的成長帶來何種影響。
拉蘿指出,中產階級的教養傾向「規劃栽培」(concerted cultivation),注重孩子的認知發展、積極安排多元的課外活動,並以說理為溝通模式,讓孩子逐漸產生「權利感」(a sense of entitlement)。相對地,勞動與貧窮階級的教養傾向「自然成長」(natural growth),除了滿足孩子的基本需要,大多任其自行發展。他們大多以直接下指令的方式作為溝通模式,讓孩子逐漸產生「侷限感」(a sense of constraint)。
規劃栽培的忙碌,自然成長的侷限感
中產階級的教養模式真的比較理想、比較正確嗎?拉蘿透過她細膩的觀察指出,儘管父母花大量資源栽培孩子(各樣體育活動、才藝班),可以讓他們培養未來於教育或職場上的有用文化資本,但往往在過度密集的行程中,犧牲了家庭相處的時間,也讓孩子很難適應自由的時間,一沒有組織式的活動就會「無聊」。相對地,勞動階級的孩子因著父母忙於工作,無暇管他們,反而享有比較多的自由時間。這讓他們得以與非正式的同齡群體嘗試各種遊戲,學習制定規則、管理衝突的社會能力。他們更能獨立探索這個世界,在空白的時間發揮創造力,不怕沉悶與無聊。
然而,談到語言的使用,中產階級強調的「說理」,就能讓孩子在未來享受主流體制中的各種好處。因為在現代社會,老師與老闆喜歡的是善於說理、勇於協商、富有主見的人。中產階級的孩子從小就被當「大人」看,當與父母的意見衝突時,父母會傾向花時間解釋、引導,並尊重孩子的選擇。這為孩子帶來權利感,認為自己的意見很重要,可以跟大人平起平坐。但勞動階級的溝通模式往往是「直接下指令」,孩子與成人的世界有一明確的界線,孩子只有服從的義務,沒有協商的地步。他們沒有機會跟成人談判,也較少整合自己的想法、發表論述,使得他們有較少學習新詞彙的機會。這無意間影響他們日後在課業的表現,加深面對學校、醫療機構與職場時會浮現的侷限感(覺得自己不如這些「專業人士」)。

介入體制與非正式知識的重要性
我認為《不平等的童年》一書最精采的分析之處,在於拉蘿深刻地指出孩子在學校體制的成就,相當有賴於父母的掌握與介入。中產階級的父母,有較多的文化資本,可以為孩子安排最適合的教育,甚至積極地干涉老師的教學方式。例如,向老師抱怨作業太多,或是認為孩子應該要轉到資優班學習。因著他們的高教育程度與高階白領的工作經歷,他們可以理解老師的專業知識語言,並認為自己有權利與責任干涉教學體制,或與老師協力對孩子進行規劃栽培。
然而,勞動階級的家庭卻有意與學校保持微妙的距離。這些父母不了解專業人士的用字遣詞,只能默默順從,並傾向認為教育是老師的任務,父母無須積極與老師聯絡。但由於規劃栽培是主流的教養模式,他們常常被老師視為「不適任」,不花心力在孩子的認知發展或閱讀能力上,導致他們落後於同年級的學生。拉蘿說道:「老師不希望家長順服或聽命行事,他們追求矛盾的策略,既希望家長們主動參與、有意識地帶領孩子的學校體驗,但又同時要有禮貌、順從,並支持教育者的教學計畫,只要意見相左,家長應立刻服從教育者的安排。」[1]這樣的教養方式,對於時間與資源匱乏的勞動階級家庭而言,成為頗難達致的理想。
除此之外,中產階級的孩子更有機會藉由「非正式的知識」,獲得較好的教育資源。父母明白各高中與大學的排名與學校特色,會積極協助孩子準備考試、申請學校,甚至藉由各種人際關係了解有關升學的重要資訊。例如,書中的塔林格女士就透過在長春藤聯盟大學任職的「朋友」,得知這些競爭比較激烈的大學,很重視孩子是否有在高中修習一些較困難的課程。因此,她希望孩子可以提早在高中就修最嚴格的課程,以為將來申請大學做預備。
相對地,勞動階級的父母對教育體制的知識所知較少,他們不太清楚該如何為孩子安排最適合的學校,也不知道申請學校的複雜手續。在他們的成長經驗中,大學彷彿遙遠的國度。因著資源的匱乏,他們也傾向叫孩子趕快工作,而非繼續升學。拉蘿特別指出,儘管「勞動和貧窮階級的青年有才能、有決心,但他們沒有成年人的幫助,無人替他們介入體制。」[2]
長期下來,因著社會階級帶來的兩種不同教養方式,形塑了不平等的童年。中產階級的規劃栽培相較於勞動階級的自然成長,顯然更能轉換為未來在社交或職場上的利益。這些孩子從小就培養權利感,有自信地認為可以跟體制打交道,甚至讓體制為自己服務。

「出生就站在三壘,但他們以為自己打了三壘安打」
說到底,為什麼要這麼強調社會階級的影響力呢?拉蘿認為,因為我們都傾向認為成功是來自於自己的才能與努力,卻沒有察覺到原生家庭的優勢,是如何在成長歷程中不斷地給予我們特殊的資源,為我們鋪平了前方的道路。這讓我們產生一種錯誤的思考方式,即認為那些沒有學習能力的孩子,都是因為他們不努力,或父母不夠用心。再者,社會沒有平等地看待不同教養方式的價值,反而一味推崇規劃栽培,貶抑自然成長。這讓我們忽略規劃栽培的缺點(過度緊繃、焦慮),以及自然成長帶來的優點(自由、創造力)。事實上,規劃栽培會成為美國主流的教養模式,也是來自日趨不平等的社會脈絡。拉蘿指出,這跟美國經濟型態的改變有關。由於許多產業外包給其他國家,高薪的製造業變少,低薪的服務業變多,人人必須爭相取得好學歷,才能在高度競爭的市場中獲得優渥的工作,這使許多有資源的焦慮父母開始採取規劃栽培的教養方式。
拉蘿用一個很巧妙的比喻濃縮本書:「中產階級的孩子們『出生就站在三壘,但他們以為自己打了三壘安打』」。[3]相較於階級的影響,美國人更傾向相信每個人都該為自己的成就負責:只要努力工作,就能獲得機會,讓天賦與才能帶我們實現自我。這種個人主義的思考方式,非但沒有誠實地看待社會不平等,更帶來了「贏家的傲慢」與「輸家的羞辱」,正如政治哲學家桑德爾在《成功的反思》所提到的。[4]討論社會階級至關重要,因為它讓我們了解到自己會處於現在的位置,有很大程度是來自於原生家庭的優勢與劣勢。

看見階級內的異質性
《不平等的童年》詳實地記錄社會階級的影響,捕捉了常人看不見的結構力量如何形塑我們。然而,我認為本書在某些面向的探討稍嫌不足。例如,作者傾向將中產階級、勞動階級與貧窮階級視為同質的群體,而忽略了階級內的異質性。事實上,並非每個中產階級都用規劃栽培的教養方式,也有不少人看見自然成長的價值,或調和兩者。此外,作者似乎太過強調階級的影響力,隱含一種決定論的觀點,彷彿成人的未來發展早已被原生家庭的條件所決定。
針對上述的探討,我覺得台灣社會學者藍佩嘉在《拚教養》一書中就提供更細膩的分析。她從社會階級的高低與教養目標(規劃栽培、自然成長)的兩向度,畫出四個象限,分別為培養國際競爭力、規劃自然成長、培育階級流動力與順其自然造化,對同階級中的教養實作進行更多元且豐富的探討。書中也特別將教養視為一種反思性的實作與保安策略(security strategy),更能捕捉到父母在既定的結構底下,為教養實作賦予的意義詮釋。
結語:誠實面對不平等,培養感恩與謙遜
我認為閱讀《不平等的童年》重要之處在於兩方面。第一,作者誠實地探討既有社會階級的不平等,是如何透過教養實作與教育體制再製不平等。她邀請我們放下對於教養的執著與成見,去看見結構的力量如何影響著我們。意識到今天所站的位置,並非全靠自己的努力,而是一路上有許多經濟、教育資源的挹注。由於這樣的優勢並不存在於每個家庭,因此我們應保有更多的感恩與謙遜,同理每個家庭都很努力地在運用不同的資源,拉拔每一位孩子長大。
第二,本書讓我們重新省思不同教養方式的優與劣,了解規劃栽培並非「最正確」的教養方式。我們的社會主流肯定中產階級的規劃栽培,認為孩子「不能輸在起跑點」,同時貶低勞動階級與貧窮階級的自然成長,認為這些教養策略對孩子的成長毫無幫助。但是,拉蘿不斷提醒我們,規劃栽培的沉重負擔往往使家庭成員筋疲力竭,也可能在過度強調個人主義的權利感時,難以培養團體意識;相對地,自然成長則能讓孩子盡早學習獨立,並在尊重與義務的框架下培養深刻的家庭連結。
無論我們的成長背景為何,《不平等的童年》都邀請我們對每位教養者存有更多的敬意與善意。或許,下次當你在社會上看到令你眉頭一皺的父母時,我們能更溫柔地去同理他們的無助,以及他們的用心。
[1] 安妮特‧拉蘿(Annette Lareau),《不平等的童年:拚教養能翻轉階級嗎?》(新北:野人,2021),頁212。
[2] 同上,頁280。
[3] 同上,頁20。
[4] 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成功的反思:混亂世局中,我們必須重新學習的一堂課》(台北:先覺,2021),頁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