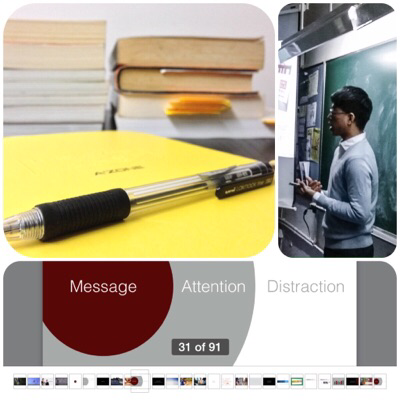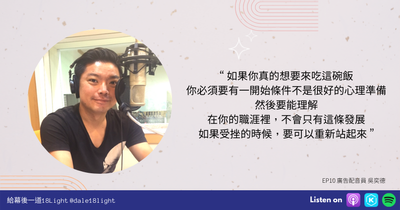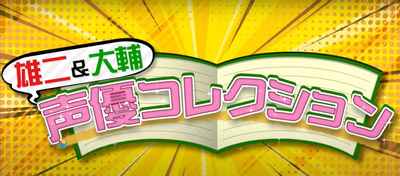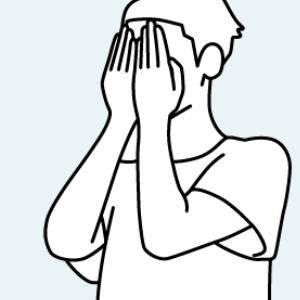配音員的情緒演繹之路:從傳統演技走向身體感受
身為配音員,情緒理解與表達方式,卻是每個人天份各有不同,甚至大相逕庭。像我就始終無法把傳統的「方法演技」應用在配音上,這也讓我在配音生涯發展中阻礙重重,也造成我與許多業界人士不同程度的困擾。
什麼是方法演技呢?方法演技(Method Acting)源自俄國劇場大師康斯坦丁·史坦尼斯拉夫斯基(Constantin Stanislavski),其技巧鼓勵演員們,將自己的人生經驗投影在角色身上,並深入探索角色內心動機,細心捏塑出該角色的人格特質和出身背景,好讓演員跟角色合而為一,從中打造出最真實的角色面貌。
但當我的人生經驗與角色相距甚遠時,幾乎是完全無法投射、也理解不能的。舉例來說,傳統配音教學,當學生在跟班時期(學徒)抓不到角色情緒時,前輩們都會請我們回想相關自身經驗,來喚醒記憶並投射情緒進入角色中。劇中角色憤怒罵人、怒中帶恨、時而哀傷時而悲痛,前輩們會這樣循循善誘:「回想一下妳跟家人/男友大吵一架的時刻?被誤會被陷害感到憤憤不平的當下?是不是忍無可忍?髒話直接爆出來?感受一下,就是那股憤怒!來!邊回想邊試一個!」
我:「......嗯,我如果很生氣,就只會一直換角度跟對方說道理,不會像這樣宣洩情緒欸...... 其實,我是個理性的人......」
前輩(不耐煩):「不要解釋那麼多,不然妳總該看過別人憤怒的樣子吧?像是父母罵妳或被師長罵時,她們臉上猙獰的模樣與那些脫口而出無法控制的情緒?來,想著她們的臉再試一個......」
我(盯著前輩越發憤怒的臉、有點擔心的說):「可是、我覺得氣成那樣很沒道理欸,與其發洩情緒在我身上,倒不如好好跟我講,也比較能解決問題啊。」
前輩:「.........妳給我出來。」(被趕出錄音室)

康斯坦丁‧史坦尼斯拉夫斯基(Constantin Stanislavski)生於1863年1月17日,是俄國著名戲劇表演藝術家,同時也是方法演技的提倡者。
像這樣「孺子不可教也」的窘況,在我學習配音過程中一再發生。但我能直接上麥(mic)聲音又還算堪用,看帶也還算幫得上忙(*備註1),所以領班前輩們就通通把沒什麼情緒、或語氣很平的角色都先丟給我錄惹。像是:記者、主播、話外音旁白、各種廣播語音等等。基本上有點半放棄我,把能穩住的角色先錄好,其他角色以後再說的概念啦!
但錄久了總不能老讓其他人辛苦吧!於是一些小女生、青少女的角色,也就試著分給我錄錄看。前輩:「年紀小的女生情緒也單純,要嘛說話又衝又直接、要嘛就是撒嬌談戀愛,這應該很簡單,妳來試試看。」
......這下糟了,小女孩情緒層次確實不如成年女子豐富多變,理論上每個剛入行的年輕女性配音員應該都能迅速駕輕就熟;但偏偏我...... 我、我沒有過什麼小女孩時期的情緒啊!而且,我也完全無法理解小女孩為什麼要氣噗噗、說話為什麼要又直又嗆、為什麼要用娃娃音撒嬌裝可愛......
在我的少女時期,就是個說起話來情緒穩重到不行的小大人啊!(崩潰)而且我聲音稍偏厚實,又不擅長鼻腔共鳴,別人的送分題根本是我的魔鬼地獄題!(再度崩潰)
當然啦,當時的我也嚐試著想解釋什麼...... 然後硬著頭皮彆扭地錄完...... 果然語氣生硬造作到不行。(然後再度被趕出錄音室)(?)
訓練演技方法不只一種,何不試著「讓身體說話?」
雖然,上帝為我關了一扇門(也不算關門啦,就是搞了三年語氣仍顯生硬這樣,連我自己都受不了),卻也在同時替我開了一扇窗。跨足廣告圈的前輩們,剛好發現了我的聲音特質,非常適合簡介、語音等穩定度極高的案子,也讓我從另一條路開始慢慢發光,也因此有了更多時間與空間,去尋找訓練情緒的方法。
我發現,我在情緒演繹上的障礙,多半是因為原生個性與思考邏輯所致,所以需要繞過傳統提取記憶經驗的方法,改用別種訓練模式,才有機會讓情緒順利展現。
既然問題出在腦袋用太多,那就別繼續用腦思考下去了啊!
「何不試著讓身體說話?」在因緣際會之下、看了幾場舞台劇之後,這樣的想法慢慢萌芽。
我一直很好奇也很困惑,為什麼舞台劇的演員,有另一種屬於他們世界的說話方式。跟電視影集、電影長片演員的那種只集中在口鼻頭腔部位共鳴的口條咬字並不一樣,而是能量從整個身體散發出來,每個舉手投足、每個身體部位,都像在對著我說話。
我無法理解。明明我坐得離演員那麼遠,明明劇場的空間並不小,但就是能一直有股能量,帶著聲音,從遙遠的距離,把情緒投射到達我的前方。
這種感覺太奇怪了。跟我所理解的配音咬字共鳴轉換之類的概念,怎麼都不太一樣。而且站在舞台上的人,似乎都能自帶這種特殊的能量氣場。
對我來說,無法理解的事情,只分成有興趣理解、跟沒興趣關心。無法理解,就不會行動。就如同配音時坐在麥克風前,我並不關心那些電視裡的角色們為何歇斯底里的哭泣、撕心裂肺的怒吼,也不關心年輕女孩們為何說話要娃娃音撒嬌或到處惹罵人惹事。所以,打從心底也排斥著,不想變成她們。但現在的我,卻急切的想了解為何站在我眼前的那些演員,是如何長出滿滿的情緒,讓角色這樣說話、那樣唱歌;就算是站在幾乎沒幾個道具或寫實布景的舞台空間上,那些情緒卻也能如此真實的說服、感動著我。
他們是如何憑空建構出這些角色的血與肉?哭與笑?愛與恨?是否也跟配音一樣參考模仿著誰?抑或這些都是演員某部分的自己?
啟動一切的源頭,到底是什麼?
我被深深地觸動著,卻也很是迷惑。
被舞台劇演員強大的能量感動,轉化為「用身體配音」
後來,我開始接觸劇場,慢慢一齣戲一齣戲的看,慢慢一堂課一堂課的上;從尷尬到完全無法自處及被人觀看的不協調肢體,到走進無垢世界的從根伸展與拔開、甚至自由即興舞蹈的自在;從另一種由身體開始再啟動聲音的感受與練習,從骨骼肌肉裡慢慢試著長出、聽見自己的另一種聲音......
我變得無法光用腦袋思考了。也開始慢慢理解,原來有很多情緒,都是從身體先行。是身體先感受著、肌肉帶動著、骨骼支撐著、關節轉動著...... 最後開口的第一個字,也是在無數個呼吸中,才從唇齒間碰撞出聲音來。
原來,情緒就是這麼回事。
不用拼命去理解為什麼,而是讓身體去模擬、去動作,自然就能感受。原來我不是沒有情緒,是藏在身體內部的情緒,沉睡了許久,終於被看見、釋放、爆發出來。一切的發生,都是如此自然。身體知道、骨骼知道、肌肉知道、呼吸吐納之間知道、皮膚知道、流動奔騰的血液知道...... 就唯獨腦袋,最後一個才知道。(*備註2)
真是太笨拙了。(笑)
我就這樣從另一個地方,慢慢找回了以前的那些、用腦袋怎樣都無法理解的情緒。漸漸再幫自己把這些情緒,堆砌拼湊成只屬於自己所架構出來的、名為林瑋婷的各種角色。
跟別人不太一樣,但似乎也長出了血肉,開始有了生命力。
我的學習路徑,確實和其他配音員不太一樣。但我覺得彌足珍貴,且獨一無二。這一路上有太多值得珍視的東西。那些在訓練時所流的汗水跟眼淚、在反覆跑跳過程中撞出的烏青與傷痕、那些被觀看時莫名想哭泣的感動與可以再更好的不甘心、那些唱了100次、1000次不斷重複的音符與旋律所噴發出來的情感與詮釋......
都是我的。
只屬於我的,珍貴的聲音禮物。
- Bibi -
*備註1:
直接上麥=不害怕麥克風,沒有適應麥克風時期,菜鳥跟班期就能直接開口配音。
看帶=助理幫配音員進錄音室錄製前的稿子做前置作業:包括替卡通/戲劇標上人名/時間碼/氣音/標註話外各類情緒反應/數嘴改稿以貼合劇中人物說話&嘴型長度,甚至包括音檔分軌錄製標示/雜聲另收/查詢ME(音效是否需另錄)......,是十分考驗細心度的工作。
*備註2:
雖說不再從腦袋理解出發,改由身體先行,但如果行為本身沒有足夠動機,身體無法理解「為何要如此行動」,我也是抗拒的。(結論:我好煩!😂)
你可能也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