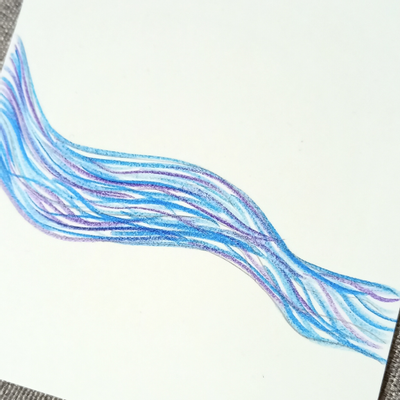【刺客行】第四十三章.刺客出征(下)
呼嚎聲連連不絕,那箭矢居然接二連三的刺穿了數人的眼睛,強烈的痛楚讓他們慌亂的亂揮兵器,在擁擠的人流中造成混亂,上官禦得了先機,自當乘勝追擊,手中匕首猶如流星升降,點點寒光流轉,未見其影破空聲先至,一刀一個準,專門往眼珠上劃,正是為了製造更多破口。
「別慌!拿出一點骨氣!受傷的站在原地別動!後面的遞上!別讓上官大人笑咱們沒出息!」周恆負手站在陣外,沉著的喝令,還不忘諷刺的繼續以尊稱喊上官禦,游刃有餘的態度讓人惱火。
穿梭在黑夜與劍陣裡的飛箭同樣源源不絕,相對於包圍在側的士兵,這些在遠處伺機而動的弓箭手更是煩人,上官禦反手抄了幾隻箭,避過數把劍交織而成的劍網,踏在劍身上借力縱躍,劍尖彷彿劃為雲朵,而他便在其上飛翔!全然無視刀光劍影的威脅!
「骨氣?呵,你還真敢說。」上官禦冷冷一笑,夾在手裡的箭調轉方向,正對著周恆的嘴巴射去,最好能貫穿他的舌頭讓他閉嘴,可惜定會失敗。
上官禦心知肚明,他就是想發發洩而已,周恆哪那麼好打發?
再怎麼說他也是混到如今才暴露身分的人,若只有在旁邊看的本事,那吳煥夷又豈會派他來當暗樁?
想來他功夫肯定不差,至少也比劉宇還要好,會只當個參軍,肯定是吳煥夷要他低調,讓劉宇當馬前卒,才能不耗太多力氣的打進核心吧。
果不其然,周恆輕描淡寫的夾住箭,如同先前上官禦的動作,反手又扔了回去,上官禦單手拋起剛剛收在腰側的匕首抵禦箭勢,另一隻手上始終未放的匕首迴轉得像是風車,收割了好幾條人命。
他沒有哪次刀劈歪,全部刺進鎧甲或頭盔的縫隙裡,又快又狠的凌厲讓人望而生畏,濺上鮮血的英俊面龐鬼氣森森,毫無情緒波瀾的瞳孔卻帶著森冷笑意,早已沒有先前帶兵時肅正的英氣,顯得陌生而恐怖。
此刻,他不是御林軍副統領上官禦,而是刺客門出身的--鬼影。
迷亂的劍陣與箭雨其勢不衰,分明是步步殺機的險象環生,單挑數千人的上官禦卻像是體力源源不絕,一點疲態也沒有,反而藉著「孤身」的優勢,讓眾人疲於奔命的圍攻他。
聯合劍陣當然威猛,可對付上官禦這種比泥鰍更滑溜,比飛仙更飄搖不定的目標, 人數太多反而顯得笨重有餘、輕靈不足。
別說他不時給人眼珠插把刀子,就算是個基本的轉身,都讓他找出能擾亂的地方,硬生生的把劍圈的動向打亂!
他到底知不知道環繞在他身邊的是劍?這可不是樹枝,割到身上是會噴血的啊!就沒一點恐懼?!隨手就撥、伸指就彈,完全不放在眼裡!
叛軍們從來沒想過,這個平時嚴格卻算得上溫和的人,根本從未在他們面前顯露真本事!他們也不知道他還有這一面,宛如鬼神般的煞氣,如果他們早知會陷入如此境地,或許便不會叛變,可惜為時已晚。
上官禦已經決定這些叛賊,一個都不會放過!
「周恆!想要我的命就自己動手試試!你應該知道這些人根本奈何不了我!別浪費彼此時間了!」上官禦游刃有餘的飛躍在刀劍叢林裡,穿梭在細密的箭雨中,傲氣沖天的朝周恆喊。
叛軍身上都穿著鎧甲,亂箭射到身上基本毫無作用,本以為劍陣加箭雨的攻勢能輕易取他性命,沒想到竟是妄想,現在居然還被如此輕視,簡直恥辱至極!
是可忍孰不可忍!非在他身上討回來才行!
不待周恆發令,劍陣自行變了型態,攻擊越發詭譎難測,竟是上官禦從沒瞧過的陣式!肯定是趁他不在皇城時偷偷排練過的,果真奸滑!
上官禦動作慢了一拍,周恆正是在等這一刻,脫手便甩出七八節鐵鞭,耍得虎虎生風,靈活又凌厲的穿插在劍陣箭雨中,成了第三層包圍網!
這下遠中近三方面的攻擊一次全湊齊了,前面的兩種攻擊對上官禦而言不算什麼,可加上了這波鐵鞭的攻擊,就差多了。
周恆的鐵鞭彷彿像是生物一樣,總是從出其不意的地方竄出,末端繫著尖錐狀的秤陀,在重力加速度的甩動中威力暴增,體積雖小殺傷力卻不遜於真刀實箭,位置準了甚至能擊碎骨頭,不容小覷!
可即使到了如此危急的地步,上官禦卻還是維持著原先的從容。
周恆看他不時往奇怪的方向看去,以為他是想引開自己的注意力,便更牢牢的緊盯著他,同時不忘替吳煥夷拉攏強者。
「上官大人,浪費力氣的是您啊,何不投降?像您這般有本事的人,為何不…」周恆溫和的笑語說到一半,便突兀的停了。
不,或者該說,全場所有人包含叛軍在內,大家的動作都停了。
鋪天蓋地的箭雨驟然消失,呼嘯而過的冷風裡傳來奇特的聲音,讓人不禁提高戒備豎耳傾聽,越發不可思議。
軍隊行進聲,正朝著這裡過來。
周恆面無血色,驚愕不定的瞥向上官禦,此刻那人已經好整以暇的降落在地,靠著欄杆有一下沒一下的拋玩著匕首,嘴角噙著冷笑。
「…你真以為,我是什麼烈士,會一個人來找死?」他近乎憐憫的望著周恆鐵青的臉,戲謔的微微歪頭,悠悠問道。
黑甲叛軍呆若木雞的看著火光中漸漸明晰的輪廓,一時五味雜陳。
走出黑暗的人們,正是早被囚禁於宮中某處的「前」同僚們。
也就是未參與叛變,剩餘的御林軍!
黑甲士兵對黑甲士兵,一樣的裝扮兩樣的心思,分崩離析的二者今日又再交會,卻再也不能如往昔那般同飲一醰酒。
上官禦朝著某處揮手,隨即便有東西從遙遠的那頭被甩來,在地上發出沉悶的聲響,骨碌碌的轉了幾下,恰好停在周恆與上官禦之間。
赫然便是弓箭部隊的隊長頭顱!
那顆血肉模糊的頭沾滿塵土,放大的瞳孔仍保留著死前的驚愕,張大嘴似乎有滿腔疑雲想問,卻已沒了性命,淪為一塊無用的東西。
周恆這才明白,上官禦根本不是有勇無謀的亂闖,而是將自身作為誘餌,行了個調虎離山之計,好讓他的人輕易搜尋那些失蹤的御林軍!
本想算計他,卻不料被將了一軍!該死!他暗自咬牙。
御林軍團團包圍著眾人,一語不發,不知隱藏在頭盔下的表情究竟如何。
情況因為這個突發狀況直接一面倒,原先背叛的人恰好是御林軍總量的一半,另一半赴死抵抗的頑劣分子抗爭失敗,被囚困起來。
本來正好的優勢,誰想到被劉宇帶離的兵馬,居然會齊齊喪命在天楓寺!而剩餘者剛剛又被上官禦折損了大半,這下真是偷雞不著蝕把米,現今人數完全壓不過對方了!雖說勝仗未必是靠人多,可在兩方的基礎(同為御林軍)都是一樣的狀況下,誰勝誰負自不必多說了。
這一回合,可算徹底敗了。
「周恆,你還有什麼手段盡管使出來,或者你也可以選擇講出地道出口的位置,好歹還能死得乾淨點。」上官禦明知道答案,但總得走個流程不是?於是他問得漫不經心,甚至還有些無奈。
周恆嘴角抽搐幾下,發出幾聲幽微的笑聲,而後漸漸變成縱聲狂笑。
「上官禦,你知道我不會說,我也知道你不會讓我好死,既然如此又何必浪費口舌?我敗了,不代表輸贏已經決定!若能拖你下水,死又有何懼!」說著他便飛出所有纏繞於臂上的鐵鞭,彷彿扔出七八條毒蛇,兩人中間的旗桿雜物都被砸出破口,粉塵木屑撩亂人眼,周恆迅如雷霆的撲到上官禦身前,當胸一擊!
血泉噴湧,上官禦分毫未動,冷冽的看著面前之人。
數枚箭矢從周恆背後透胸而過,他維持原先的動作僵立著,張開的嘴巴源源不斷的嘔出鮮血,得意的鐵鞭軟趴趴的垂散在地,像是癱軟的無頭蛇,周恆踉蹌幾步,卻堅持不肯跪倒,雙目死死瞪著上官禦,彷彿能把他活活看死似的,執著得驚人。
「你是不是忘了我藏在暗中的人?大意可不行啊,周參軍。」上官禦雙臂交錯於胸,匕首卻還是好好的握在手裡,揚頭親切的提醒。
周恆居然還在笑,這份狂傲當真與上官禦有得比,無光的眼睛燃起狂熱的烈焰,抬手發出一擊!
原來周恆在掌心處藏了一片極薄的利鐵片,尖銳處隱隱閃爍紫光,肯定淬過毒,想來這便是他最後的手段了!
--沒想到,他的攻擊卻不是對著上官禦而來,竟是決絕的割開自己腹部,噴得到處都是怵目驚心的紅!
利鐵片上的毒與血液混合,頓時催化出極為難聞的氣味,大量的紫煙從周恆身上迅速擴散,他的血肉寸寸崩壞廢死,筋脈劇烈跳動全身皮膚都變成紫黑色的,模樣看著已不像人類。
「大意的是您啊…上官大人。」周恆漸漸融為一灘爛肉,掛著血肉模糊的笑容,伸出尚且能動的手指,顫巍巍的指著上官禦,斬釘截鐵的宣告,直到雙腿被融化殆盡之前,他都沒有屈膝。
「撤!」上官禦神情一變,厲聲怒喝,御林軍們不愧是受訓多年的精銳,毫無任何猶豫驚慌,自行分成放射狀的隊伍,動作俐落的往外撤,同時不忘戒備叛軍們,兵器對準的方向仍未動搖。
叛軍進不得退無路,束手無策的被鎖在原地,離周恆最近的那幾個人吸進毒霧,全身肌肉鼓脹起來,皮膚顏色變化,拉扒著自己的咽喉在地上打滾,七竅噴血瞳孔放大,掙扎間又是一團爛肉掉下。
「那毒會傳染!別靠近!」叛軍眾人見狀更是亂成一鍋粥,驚慌失措的想要奔逃,奈何周圍障礙物實在太多,御林軍的包圍網更是密得連隻蒼蠅都飛不出去,只能在原地你推我嚷的鬼吼鬼叫。
「投降!我投降!別放我們自生自滅啊!」
「我也是逼不得已啊!你們不能這麼絕啊!」
「不要靠過來啊!你剛剛直接被血噴到了,是不是也中毒了!」
「啊啊啊啊!我的肉!我的腿…」
「誰來救救我!」
包圍網內彷彿成了人間煉獄,眾人百相盡皆呈於眼前,看來人類不論練得多強,都跟臨死前的模樣毫無干聯,有的人手無縛雞之力卻願傲骨錚錚的壯烈赴死,而有的人即使成了風光無限的御林軍,臨死前仍是如此難看。
果然是些廢物!難怪會叛變!丟人現眼!上官禦臉上殺意更盛,毫不留情的開口訓斥,御林軍包圍網巍然不動,默不作聲的注視眼前一切。
「都叛變了還有膽求饒?!丟了御林軍的臉!你們這些雜碎我一個都不要!誰都不准放出來!若有漏的,軍棍伺候!」上官禦眉頭鎖緊,中氣十足的喝令,揚手朝遠處打了暗號。
御林軍回以肅正的吼聲,千百隻劍震盪聲嗡嗡不絕,包圍圈中血肉橫飛,燃火的箭矢朝著中心處射來,不一會便在空地上掀起驚人火勢,毒霧短暫的膨脹後炸裂,將所有叛軍一齊捲了進去,上官禦擔心火焰有毒,喝令眾人撤退。
所有營帳燃燒殆盡,偌大的軍營只剩一片殘骸,空蕩蕩的讓人唏噓不已。
上官禦遣人收拾殘骸,在整塊校練場的土地繞來繞去,試圖找出蛛絲馬跡,終是一無所獲,頹喪的坐在比武台的台階上,苦苦思索。
有些不對勁…吳煥夷費盡力氣拉攏人,怎麼東窗事發時,他的暗樁卻如此不顧一切的毀掉收攏的人馬呢?見事跡敗露卻不多做掙扎,直接毀了那批人?
明明都是御林軍,奮死戰鬥好歹能多殺我方一些人,他為何卻選擇直接用毒摧毀這個選擇?是以為毒死的人數會比殺敵的人數多?
還是單純是周恆惱羞成怒自作主張?又或者是,他另有打算?
吳煥夷不可能只派周恆與假東宮來拉攏御林軍而已,宮中一定還有他的人馬,他既然會這麼乾脆捨去御林軍這條路,難道說他自己的兵馬更強?
在地道那些人,並不是他的全部兵力?還是說,這些猜測都只是杞人憂天?
上官禦很頭疼,吳煥夷這廝故佈疑陣太多次,居然連自己都已經弄不清他的意圖。
遠處傳來急促的腳步聲,上官禦靈敏的聽覺已知是誰到了,揚首微微一笑。
「首領,你沒受傷吧?」紫櫻領著阿藍快步上前,擔憂的問。
兩女都負著長弓,阿藍的臉色慘白,顯然剛剛的勞動影響了她的傷勢,但她並不多話,只默默站在一旁抹汗,其餘的弓兵在上官禦的指示下去幫忙收拾殘局。
紫櫻站在台階旁,上官禦坐在台階上,恰好成平視之姿,上官禦彎著嘴角,露出一個動人心魄的微笑,不回答紫櫻,只是直直望著她。
「…首領?」對於上官禦歸來後的轉變,紫櫻仍有些忸怩,雙目游移不敢看對方那雙彷彿能溺死自己的眼眸,低頭捏著衣角含糊不清的喊。
上官禦輕柔的牽起她的手,搭上自己的臉頰,那雙溫軟細膩的手雖有些驚訝的顫動,卻並未有掙脫的意圖,上官禦便決定再賴皮一點。
「妳不是問我有沒有受傷?可以自己確認看看啊。」他將她拉得更近,靠在她耳邊低聲笑道,紫櫻聞言整個人都僵住,從頭到腳全紅得像煮熟的蝦。
…這個人真的不是冒牌貨?!他還是那個每次都雲淡風輕避開她的人嗎?!
看她如此,上官禦鬱結的思緒稍有緩解,牽著她去阿藍身邊。
「辛苦妳們了,在哪找到他們的?」上官禦正色問道。
「就在旁邊的廢棄冷宮那邊,真是盲點,沒想到那裡荒廢多年,早就衰壞得跟荒地似的,居然成了這些叛賊利用的地方,馮時晚大人也懊悔不已,他千找萬找就是沒發現那裡,要不是他們也在拼命試著引人注意,我們還沒發現呢。」阿藍疲倦的搖頭。
「什麼意思?當時他們被關著?關押在怎樣的地方?不是說東西都荒廢了嗎?建築物應該也壞得差不多了,怎麼能關住那些人?」上官禦擰眉,嚴肅的問。
「說到這個,還真是佩服吳煥夷,他居然將毀壞的牆壁當屏障,在原先的地基處挖空,然後將鐵製牢籠整個埋在土裡,一旦被丟進去就沒辦法從內逃出,何況還埋在地中,只是從旁經過的話還發現不了機關呢,要不是他們點燃衣服放煙,還真找不到。」紫櫻看阿藍相當不適,趕緊替她接話,並拍她的背幫她順氣。
上官禦臉色又深沉幾分,看來那裡也有調查的必要,但這裡還是得繼續搜索才行,廢冷宮比這裡離中樞更遠一些,而且沒有軍備品等等可供補充的東西,他還是認為地道出口藏在這裡的可能性更高,但也不能否認那裡有可能是他的第二條路,畢竟狡兔都有三窟,何況他?
說到這,無蹤那邊不知道如何了?到現在還沒看到信號,難道他制不住假
東宮?吳煥夷安排的暗樁真的都除去了嗎?是不是該先去看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