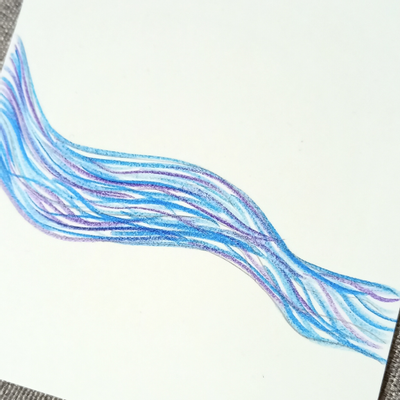「他太黏,她太冷;
他假裝無所謂,她就真的當他不重要。
她不說愛,
是因為她知道
一旦開口,就輸了。」
那天,球王買下了樂凌兒整天的時間。
不是因為許之民霸道地包場,而是他禮貌卻堅定地說了一句:「我想和妳多待一點時間。」
樂凌兒知道那不是命令,但卻沒辦法拒絕。因為對她來說,那是一份足以抵過十個普通客人的酬勞。
我們沒有去遠的地方。他說:「看場電影好嗎?」我點頭。
看電影,是最讓樂凌兒放鬆的活動。
沒有人需要說話,沒有太多眼神交會,也沒有讓我疲憊的表演。
我們坐在影城的VIP雙人座椅上,他始終沒有靠近我,只是在黑暗中偶爾轉頭確認我的表情。
那兩小時,樂凌兒終於像個普通人。不是誰的陪酒小姐,不是誰的客人。我只是個坐在陌生男人身邊,看電影的女人。
電影結束,許之民問樂凌兒:「還可以吧?」樂凌兒淡淡地回:「還不錯。」球王點點頭,沒有繼續追問。
接著許之民帶樂凌兒去101大樓上的法式餐廳。服務生替我們拉開椅子,白色桌巾、燭光與玻璃杯的碰撞聲,每一樣都像我從沒進入過的世界。
那是一種靜得出奇的高級感,燈光不刺眼,餐具無聲落座,連服務生都像訓練過的演員,每一個動作都得體而克制,彷彿連呼吸都是收費的。
我不敢太大聲說話,也不敢太快動作,鞋跟踩在地毯上都覺得吵——
就像我整個人,都太俗氣了,不該出現在這裡。
許之民翻開菜單,看了一眼就說:「放心,我記得。沒有牛、羊、也沒有奶。」
樂凌兒抬頭看他。他的語氣沒有炫耀,只有一種理所當然的溫柔。那一刻,樂凌兒的心,忽然亂了一拍。
「他看得太細了,細到我連撥頭髮的動作都覺得多餘,彷彿我做什麼都逃不過他的眼睛⋯但他從來不說破,只是靜靜地,看得讓人無所遁形。」
他幫我倒水、夾菜。從頭到尾,他沒提酒。
就算侍者詢問是否來瓶餐酒,他也搖頭拒絕。
「除非妳哪天自己想喝,不然我不會讓妳喝酒。對身體不好。」他說。
樂凌兒沒有回話,只是低頭吃著餐點。嘴裡是溫熱的松露濃湯,心裡卻是不知所措的。
球王太溫柔了,溫柔到讓人不敢靠近。
飯後,許之民提議走走。樂凌兒點頭。
但我們沒走幾步,就停在百貨一樓的精品店外。
他問:「要不要進去看看?」我搖頭:「我不需要。」
我不是不喜歡那些包,而是我從小就明白,有些東西不是屬於我的。
雖然父親曾是大老闆,但我從沒享受過什麼好日子。媽媽一個人養活我們姐妹,做著粗重到男人都會喊累的工作。
我從沒幫媽媽搬過馬達,
但我看著她拖著腰、彎下身體,只為了換來我們下一餐的溫飽。
她從不喊累,也從不抱怨,只一句話記了一輩子:
「我們可以窮,但不能沒骨氣。」
這句話,讓我在這樣的名貴櫥窗前,總是本能地說「不。」
那是她的信仰,也是她拿來撐過無數困境的脊樑。
她教我靠勞力換錢、靠尊嚴活著。
她說,做人要站著,不要跪著求。
可我長大後才發現,這個世界不再是她相信的那個世界了。
現金比骨氣有用,鈔票比尊嚴保暖。
那些站得直的人,很多都餓著肚子;
而跪得漂亮的人,反而活得體面又輕鬆。
我不是不懂她的堅持,只是⋯⋯
這種骨氣,在現實面前,太貴了。
不是每個人都能靠清白活得有尊嚴,
尤其是當我們連明天的房租都還沒著落的時候。
我看著媽媽瘦小的背影,常常問自己:
如果她當年肯低一次頭,我們會不會就不用吃那麼多苦?
但許之民沒有放棄,只是輕聲說了一句:
「陪我看一下,我想買點東西。」
語氣溫柔得像在拜託,沒有強勢,也沒有明說目的。
我站在櫥窗前,明明才剛很堅定地說過「不需要」,
他卻什麼都沒回,只是靜靜站在我身側,一聲不吭地陪著我看那只包。
我心裡知道他在等我開口,
可他什麼都沒逼我,只輕輕往前走了一步,
像隨意地推開門,又像給我一個台階。
「陪我看一下嘛,很快的。」
他說得輕描淡寫,但聲音卻低得剛剛好,
像是怕我跑掉,又不敢抓得太緊。
我遲疑了一下。
他沒有拉我,只轉頭看我,眼神裡沒有勢在必得,
只有一點點小心翼翼,像個怕我拒絕的男孩。
那一瞬間,我居然真的走了進去。
不是因為我改變心意,而是
他給我足夠的尊重,讓我覺得這一步,是我自己選的。
樂凌兒跟著他走進去。
才發現許之民沒看任何屬於自己的東西,只是不停讓櫃姐拿包出來:「這個讓她背背看。」
櫃姐一見他就笑得很標準,眼角的角度彷彿被訓練過。
我們坐下後,店員又立刻端出幾款限定的包,許之民指了其中幾款,說想看看「實際揹起來的感覺」。
樂凌兒點點頭,拿起第一個背上身。
走到鏡子前,角度微調,笑得像真的在幫自己挑東西。
許之民坐在沙發上,看得很認真。
連我下意識撥頭髮的動作,他都沒錯過。
樂凌兒一個接一個地換著包。
手裡提的是錢,背上揹的是疑問。
這不是給我的。我不需要這麼貴的東西,也從沒開口說過喜歡。
他要送人的對象,應該年輕、單純,最好還愛炫耀,這樣才不會辜負這麼華麗的包裝。
「這個呢?」樂凌兒試著轉個角度,讓肩線更柔和些,然後看著鏡子問他:「你要送人的話,我建議這款,比較經典百搭。」
許之民抬頭,眼神閃了一下,沒接話。
「你是喜歡經典款的嗎?」他忽然問。
樂凌兒微微一笑,聲音平靜:「經典款適合各種的女生,送人也不出錯。」
樂凌兒站在鏡子前,一個一個地試背那些包。
不是為了挑選,是在猜,他到底要送給誰。
他沒說,我也沒問。這不是給我的,那是肯定的。
我只是個臨時模特兒,一個活體展示櫃,幫他看看哪一個搭起來最好、送出去最不失面子。
越高級的東西,越冷。
像這些包,像他眼裡的溫柔,像我現在的笑容。
樂凌兒試著冷淡:「又不是我要買的,你問我也沒用。」
球王只是笑了笑,沒有反駁。像是習慣我所有的防備與高傲。
最後樂凌兒挑了一款中等價位的款式,想著:這應該是他想送給其他女人的吧。
我以為一切都結束了。
我轉過身,準備離開那間讓我覺得自己不屬於的地方。
但下一秒,櫃姐卻笑著輕聲提醒:「小姐,您的包。」
她動作恭敬地將那只印有名牌Logo的包裝盒遞給球王,而他,只是順手接過來,走到我面前,把它遞給我。
樂凌兒愣了一下,下意識問:「這是……?」
許之民看著我,語氣淡得像風,卻每一字都像靜靜放進我心裡:
「妳的。我早就想送妳,只是不知道妳喜歡什麼,所以想讓妳自己挑。」
樂凌兒沒說話,眼神掃過那只被絲絨緊緊包裹的盒子,像掃過一場精心包裝卻來得太突然的好意。
他沒有等我的回答,只是站在原地,沒再靠近一步。
沒有強迫,也沒有期待,只是一種靜靜守著的方式,好像他早就預料到,我會質疑,也會抗拒。
那不是一場測試,也不是為了討好。
他只是想給我什麼,哪怕我從頭到尾都裝作不需要。
那一瞬間,我沒笑,也沒拒絕。
只是伸手,接過來。
我第一次,真的接住了他給我的東西。
不是包,而是一種不說出口的認真。
他沒有問我要不要,也沒說「這是妳值得的」,
他只是用最安靜的方式,把那只包遞過來,好像不希望我為難,也不忍我拒絕。
這是他第一次,特地為我挑選、為我安排的東西。
不是順手買的,也不是湊熱鬧的禮數,而是在他無聲世界裡,極其慎重的一次靠近。
樂凌兒伸手接過,指尖剛碰到盒子的邊緣,
心裡卻突然升起一個聲音。
他是不是也曾經,這樣對別的女人?
是不是每一次「想送禮物」,都會用這種溫柔又不讓人拒絕的方式?
是不是每一個他靠近過的女人,都曾以為自己是唯一?
樂凌兒不知道。也沒力氣問。
我只知道,那一瞬間,
我既是接住了他手上的東西,也接住了我心裡那道快要裂開的防線。
一部分的我,想退回去。
但另一部分的我,卻緊緊握住了那只盒子,像是在抓住什麼……又怕太快鬆手。
樂凌兒沒有說謝謝,只回了一句:「那下次換我請你吃飯。」
但我知道,那句話不是真的。我從來不請男人吃飯。
我心裡沒有AA制這種東西。男人就該大方,若不是,我根本不想跟他坐上同一桌。
許之民什麼都沒說,只笑著點了頭。彷彿知道我不會實現那句話,也不介意。
在球王的世界裡,女人從來不需要花錢。他向來全部買單。吃飯、精品、旅遊、甚至學習課程,只要他想給,從來不問價錢,也不問妳要不要。
樂凌兒知道他有錢,也知道他把錢當作愛情的語言。
但我還不敢相信,那是給我的。
離開精品店時,他繞過車頭,替我拉開副駕的門。
樂凌兒當下眉頭一皺,語氣比想像中尖了些:「我有手有腳,自己來就好。」
許之民動作頓了一下,手還停在門把上。
但他沒惱,反而低低地笑了聲,語氣像在自言自語:「妳是我見過,唯一會生氣被照顧的女人。」
樂凌兒沒接話,只是坐進車裡,自己拉上車門。
但心裡卻悄悄泛起一陣刺痛——
不是不想被照顧,而是不敢相信有人會一直照顧我。
我習慣了靠自己開門、自己走進風裡,太溫柔的舉動,會讓我懷疑,是不是下一秒就會失去。
所以我拒絕,不是因為逞強,
是因為我怕⋯一旦接受了,就會忘了怎麼自己站著。
樂凌兒淡淡地說:「那你記住。」
許之民點頭:「記住了。」
球王並沒有送樂凌兒回酒店,而是直接送她回家。許之民說:「今天不要工作了,早點休息。」
樂凌兒沒有拒絕,只是帶著包安靜下車。
那晚,我換了包,正式的背著他送我的第一個包包,名牌包包。
隔天我回酒店,所有人都在看我。姐妹們打趣:「哇,球王欸,妳被包了喔?」
阿寶哥更是笑得意味深長:「他點妳名字點得像點燈一樣準。」
樂凌兒冷冷說:「他是客人,不是情人。」
但我心裡知道,一切開始不一樣了。
樂凌兒開始背著那只包上班,不是為了虛榮,是因為她知道球王會看。他會開心。他會繼續來。
我開始知道,他是真的在對我好。我不動聲色地接受,但我始終維持距離。
因為客人就是客人,這是我賺錢的規則。
球王天天來,像是上癮。他總說:「今天我只想她陪。」
樂凌兒不曾說我想他,不曾說我喜歡他。
但我知道,我不說,他反而更深陷,因為這本就是一場愛情的遊戲,鬥智鬥勇的遊戲。
我從來不是一個會為五斗米折腰的女人。
骨氣這件事,我是從媽媽身上學來的。
她從沒教我怎麼撒嬌取悅男人,只教我怎麼在再難的日子裡,撐住不倒。
可就算我再不願意低頭,生活還是讓我學會了妥協。
我必須工作、必須賺錢,不管那份工作是不是我喜歡的。
不管酒店裡的燈光多刺眼、空氣多混濁、笑聲多假,我都要待著,因為我沒得選。
我不是在出賣自己,而是在用我能掌握的一切,換取生存的底氣。
所以,當球王說要買下她的時間時,樂凌兒的第一反應不是心動,是盤算。她想著能少喝幾杯酒、少陪幾個客人,只需要坐在球王身邊,那筆錢,樂凌兒賺得不冤枉。
可樂凌兒沒料到,球王是會那麼溫柔。那種不是刻意的示好,而是把她放在心上、記得樂凌兒不吃什麼、不碰什麼、不愛什麼,並且願意為她避開的細節溫柔。
我開始察覺,我和他的世界⋯⋯有多遠。
不是那種你追我跑、還能開玩笑的距離,
而是我站在玻璃門外,還在考慮值不值得進去,
而他早就走進去了,甚至連價格都不看。
對他來說,這只是順路買點東西。
對我來說,卻是整個月不敢亂花錢的日子。
他想送我一個包,是出於心甘情願;
而我拒絕,不是因為不喜歡,是因為我從沒習慣有人為我花錢。
我們就這樣,隔著一條精品店的門檻,
一個輕鬆、一個緊繃,
他以為我在考慮款式,我卻在想:我有沒有資格接下他這麼輕描淡寫的好意。
那一刻,我終於明白,
不是我不夠好,也不是他不夠誠意,
是我們活在的世界,從來不一樣。
許之民是那種從來不需要擔心明天的人。
他家裡有錢,生活無憂,今天想去哪就訂機票、想買什麼就刷卡,自由對他來說,不是努力換來的結果,而是從出生就被塞進口袋的特權。
而我呢?
我靠的是體力、時間和酒量,把每一晚都當成一場硬仗,
一杯酒換一張鈔票,一句笑話撐一段飯錢,不努力,就沒飯吃;不撐場子,就沒明天。
他用錢買自由,我用錢買生存。
我們都在花錢,但他花的是餘額,我花的是命。
他刷一筆錢是心情,我存一筆錢是安全感。
我們不是不合,而是,活在的世界不一樣,
他的世界不需要計算,而我的世界,連一口飯都得掐時間吞。
我們從起點開始就不一樣。我用時間養活自己,他用時間打發寂寞。對球王來說,一天是可以隨意揮霍的;對樂凌兒來說,每個鐘點都有價碼。
可在這樣的距離之中,他卻小心翼翼地靠近,從不逼迫、不強求、不控制,只是用行動,替樂凌兒撐起了一段不必逢迎的喘息。
樂凌兒明白,球王是真的不同。
不是那種逢場作戲的好,也不是帶著目的的體貼,
而是一種讓人無聲落淚的認真⋯他什麼都沒說,卻樣樣都替我想好了。
我也明白,這樣的溫柔,是他能給得起的。
對他來說,不過是一個舉手之勞的體貼,一個自然到不需要理由的選擇。
可對我來說,卻太重了。
重得像一場只要伸手就能擁有的夢,而我早已習慣了清醒。
我不是不想要,只是⋯我太清楚自己承擔不起失望。
我怕一旦相信,失去時會連自己都掏空。
所以樂凌兒只能後退、保持距離、冷靜回應。
這世上不是沒有溫柔,而是有些人⋯像我,
從小就學會了,不能輕易接受那些看起來太好的東西。
因為我們心裡都知道,
沒有誰會真的一直給,尤其是那些太有錢的男人。
他們可以一開始出手闊綽、溫柔體貼,
包你、寵你、說「你想要什麼我都給」。
可那只是遊戲剛開始時的規則。
一旦你真的依賴了,他們就會收回底牌,開始講條件。
不是因為他們沒錢,而是因為他們從來都不打算⋯⋯無償給誰太久。
愛,是給得起的時候才叫深情;
當你沒什麼好交換時,他們就會轉身離開。
我不是沒被感動過,
只是我太清楚,再深情的金主,也只是暫時的恩賜。
而我,不賭這種不長久的好意。
因為我從來都知道,好,是有限度的;給,是有成本的;愛,是有期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