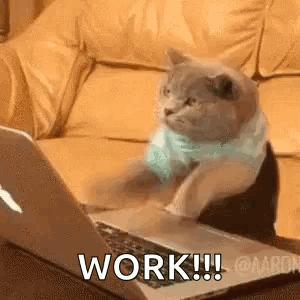※本文標註規則:『』為諮商師對白,「」為我自己。
『你覺得第一次諮商後有什麼改變嗎?』
「我離職了。」
諮商師看起來有點驚訝,因為上次的結論其實是我個人有些問題要解決,即使換了工作一樣會有這些問題,他以為我會進行幾次諮商後再評估是否離職。
這不是衝動下的決定。我去看身心科之前,根據目前的睡眠、飲食、日常焦慮的狀況分析,我覺得情況的確比我想像中的嚴重,就提離職了。
我跟主管的相處、對於工作內容的不適,都大大地加深了我的壓力與焦慮。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即使工作再輕鬆再簡單,我也真的很不爽。
至少在離職這件事上,我很清楚自己在幹嘛。
我的情緒不重要
簡單了解了一下近況,諮商師問我是否有其他想討論的問題,或是要繼續討論上次提到國小的影響及創傷。
我同意了。上次諮商時,我沒想到再次提到小學的事會讓我哭出來,我一直以為自己試圖在理解、拆解過去的事情,我以為當自己可以清晰的、中立的去看待那些過往,我就可以不再被影響。
『你寫的時候有情緒嗎?』
「好像沒有。」
『那情緒就還是在那裡呀,在你的小盒子裡,他還在的。』
好像是這樣。過度壓力、過度理性,雖然寫出來是好事,但我在故事裡的感受呢?我知道那時的我一定很難過、很生氣,但——
我似乎還是覺得那個生氣的我、難過的我並不重要。即使文字上寫了不是我的錯,但我的心裡並沒有變化。
那不重要。
他死了,跟我有什麼關係?
我們談論到我以為已經解決的小學的情緒,是因為那個國小傷害我的老師過世了,這件事讓我非常錯愕,在所有人都在提倡死者為大的時候,我想我是否該讓他抽離我的生活了呢,於是我飛快地寫下他當初對我造成的影響,以為這樣就可以跟他告別。
「但他死了,跟我有什麼關係?」
我突然在諮商室說出這句話,獲得了諮商師的大力認可。
我想正是這句話說出口的時候,我才意識到——我從來沒有欠他什麼,不需要因為他的死,原諒他,忘記他過去的作為,甚至連自己的感受都一併埋葬。
賭桌教室
這時時間已經過半,時鐘擺在我眼前,我有些焦慮。
關於小學的我,我跟同儕的相處似乎也不是很好,他請我說明原因。
「我想應該是我跟他們太不一樣、但我又試圖融入不適合我的群體,這讓我很痛苦。」
諮商師皺眉。
「是有點太攏統了嗎?」
他點點頭。
「好吧,我想想…」
因為諮商師的皺眉讓我有些慌張,我講了一些隨便的瑣事後,才講到比較重要的事件。
三年級時,那位已經過世的老師有自己的一套規則。那時候全班同學把桌椅拼在一起,形成一桌一桌的賭桌, 一整天教室都不開燈,就在玩大老二,或是看電影、玩電腦、打躲避球…
我對那時候其他老師的印象都非常薄弱。在我的記憶裡,我們就像被遺棄的班級,有點像終極一班,可能也沒有其他老師願意踏進這個烏煙瘴氣的地方,一整天的課都被換掉。
但某一天,他突然來了個大反轉,取消了所有的下課時間,要求所有人每天都在教室抄課文或寫罰寫。同學們哀嚎著,但我還是覺得整件事怪異的可怕。
似乎不論是聚賭,還是寫罰寫,所有同學都樂在其中。我印象中同學們還是很樂天,吵吵鬧鬧的,即使是班上比較文靜或乖巧的女孩,也沒對這樣的處置有什麼異議,或許是不敢,也或許對他們來說沒那麼嚴重,至少不像我對於這樣的異樣帶有實際的反彈。
到底有什麼毛病。
『這很明顯是有問題的,這個老師當時應該也是有個人的問題,你只是剛好遇到,我也很常去學校處理老師的問題,我常對那些老師說被你教到的學生真可憐。』
是喔,也對,我當時怎麼會覺得怪的是我,有問題的明明就是他。
下一次的準備
談論到這裡時間其實也經過去的差不多了,諮商師告訴我下次可以繼續就小學的事情、以及家庭的問題來做討論,看起來小學的問題還有很多值得討論的。
他上次也這樣說。
我知道,家庭一定有影響,只是…感覺比談論學校的事還要更難。
也許我需要一點時間,準備好自己,才有辦法往家庭的盒子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