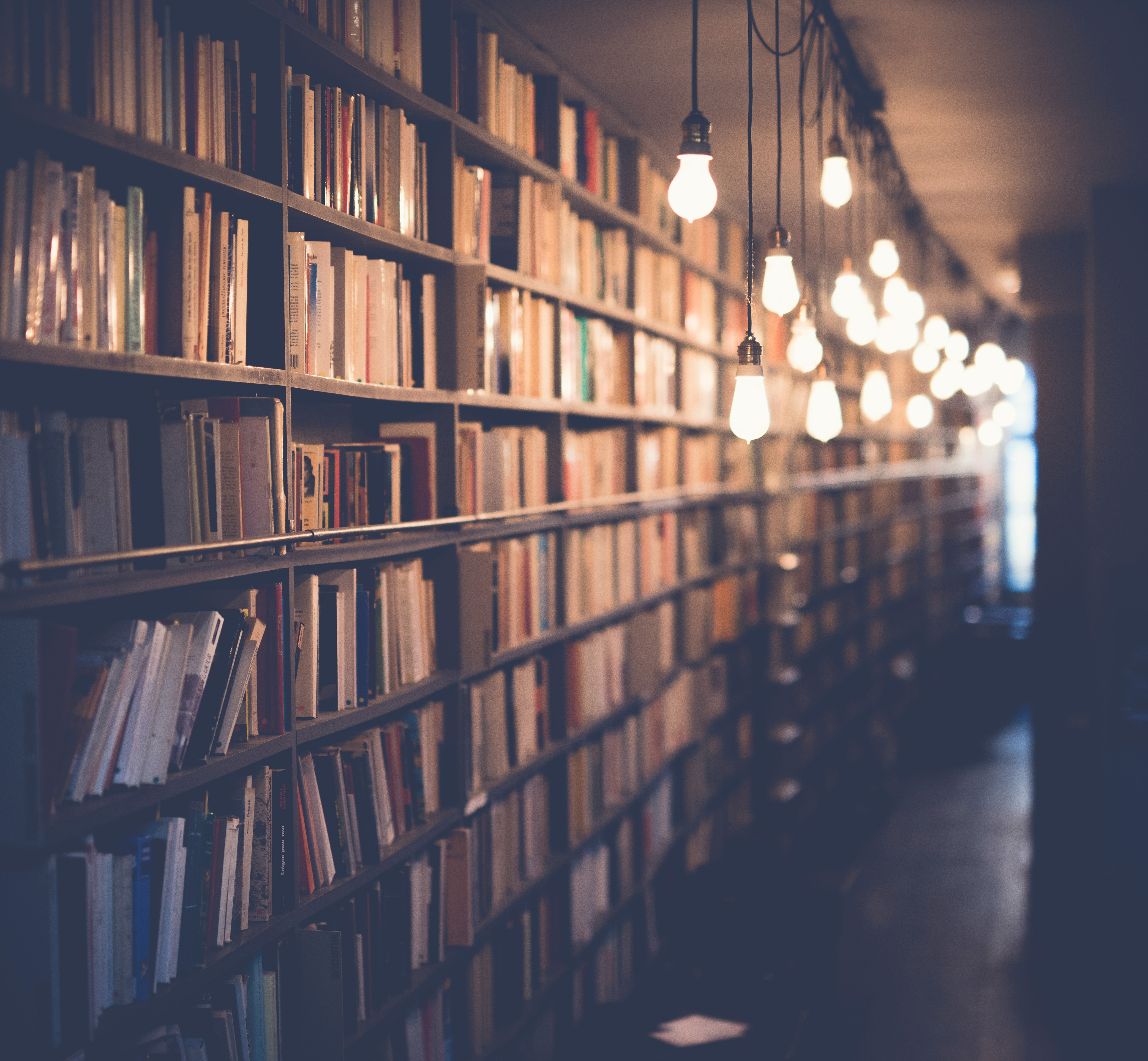如果時間與空間都沒出錯,那麼錯的,只能是我們對現實的理解。
我不是第一次看見屍體,也不是第一次走進一間密室。
但這是第一次,我在一個二十五度恆溫、門窗緊閉、攝影機全程監控的密室裡,看到一具理應不可能腐敗的屍體。
死者名叫顏若恆,年五十七,空間動力學博士,前太空總署實驗顧問,在台灣自主研究高維結構已十七年。警察找到他時,他倒臥在書房地板上,口鼻有乾涸血跡,皮膚皺縮、眼球潰陷,體表的腐爛程度推估死亡時間約在七天前。
問題是,攝影紀錄顯示他昨天凌晨兩點還在屋內來回踱步,甚至沏了一壺茶。
這間屋子是自動化設計。門鎖系統記錄無人出入,窗戶鎖死,氣密窗未曾開啟。監視影像從未中斷,門外警衛與鄰居也未察覺異狀。屋內氣溫穩定,濕度適中,不足以造成屍體異常腐敗,更別說超過五天的時間落差。
當地警方將之初步判定為「紀錄設備故障與病理性加速腐敗造成的誤判」,但我的老同學,刑事局科技顧問黃敬修,卻私下打電話給我,語氣裡帶著某種從未聽過的遲疑:「肇文,這件事怪得不像是生物問題。我想,你得過來一趟。」
我當天下午就搭高鐵抵達高雄。顏若恆的住所位於鳳山郊區,是一棟自建式智能宅,周圍無人煙,僅有單一進出路線。我一踏入那棟建築,心頭便有種壓迫感,不是來自氣氛,而是來自某種空間本身的錯位感。牆面彷彿比平常的牆更厚了一點,空氣中瀰漫一種極細微的延遲,像你說一句話後,聲音稍微比預期慢了半秒抵達耳膜。
我蹲下來觀察屍體。顏若恆的姿勢像是突然倒下,右手半舉,指向牆角。旁邊是一顆玻璃球般的金屬裝置,嵌在地板之上,半埋,表面布滿類似斐波那契螺旋的凹槽與銅線紋路。我從未在任何公開資料中見過這種東西。
我將手掌靠近球體,竟感受到一種不自然的微熱與脈動,像是微弱心跳,但不屬於任何生命。
「你看過這段錄影了嗎?」我問黃敬修。
他點頭,遞給我一支備份隨身碟。
我打開錄影畫面,2月14日凌晨2點18分,顏若恆坐在書桌前,翻著一本封面為黑色的筆記本。他停頓片刻,抬頭,目光凝視鏡頭的方向,然後……
他突然起身,走向牆角那顆球狀裝置。
下一幀畫面,他消失了。
不是走出畫面,不是閃避鏡頭,而是,消失,就像原地被擦掉。
我倒轉、重看、放慢,每一次的消失都如出一轍。
接著畫面空了幾秒,再跳到早上八點,警衛例行性開門查看時發現了倒臥在地的屍體,七天屍斑,兩小時前才消失。
邏輯無法解釋這一切。
所以我知道,這裡的空間出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