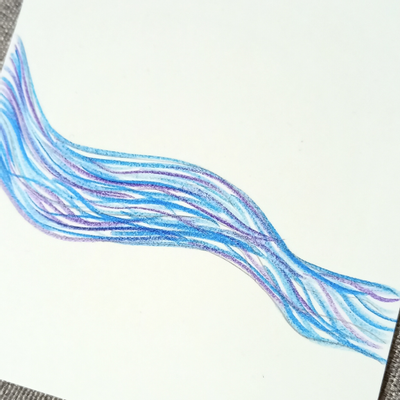[法國]
雨停得像是誰忽然按了暫停鍵,整個蒙馬特亮晶晶的,石板路反射著教堂的白。
我和長谷川並肩往下走,傘收起來,卻還是忍不住低頭看鞋,怕它再一次泡水。蒙馬特,字面意思是「殉道者之山」。
因為一千七百多年前,巴黎的第一位主教聖狄奧尼修斯在這裡被砍了頭。傳說他撿起來繼續走了好幾公里才倒下。
長谷川「嗯」了一聲,像是真的在聽。但他的「嗯」太有鼻音,聽起來像法文單字。
這座小山坡不只因為宗教而有名。
1871年,巴黎公社的火苗也在這裡點燃。當時政府軍想奪回大炮,結果士兵直接倒戈,人民開始自治。短短兩個月,巴黎嘗過革命的滋味。最後鎮壓血腥,蒙馬特的土也混進了不只是雨水。
我們走過一排濕漉漉的石牆,我忽然覺得,這山坡比巴黎其他地方都「重」。浪漫與慘烈,像是同一顆硬幣的正反面,丟上天空,永遠不知道會落在哪一面。
墓園就在山坡的一角。鐵門後面安靜到極致,安靜到你會不小心開始算裡面躺著的人頭數。
左拉在這裡,「萌芽」的那個左拉。
還有德國詩人海涅,死在巴黎,但靈魂大概還在德國罵人。
大仲馬的兒子也在這裡,「茶花女」的作者,他筆下的瑪格麗特哭到讓世界各地的劇院都 忘不了他。
還有貝爾里奧茲,那首史上最變態的交響曲--「幻想交響曲」的作曲家,如果地下真有聚會,他大概是DJ。
我站在鐵門邊,突然覺得這裡比任何咖啡館都更像「文藝沙龍」。只是,他們的對話永遠不會傳出來。
地上的世界卻完全不一樣。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蒙馬特幾乎成了貧窮天才的集中營。梵谷窮得快餓死時在這裡畫過天台,畢卡索則在這裡用幾毛錢的顏料顛覆了藝術史。雷諾瓦、圖盧茲-羅特列克、莫迪利亞尼,他們的工作室比現在的青旅還擠,卻硬是把畫布曬成了傳世之作。
長谷川聽著,忽然說:「所以蒙馬特幾乎是當時文化界的『先修班』?」
我想了想,點頭:「對。只是這裡的學費不是錢,是比比看誰能沒餓死撐過去就贏了!」
我們穿過畫家廣場,年輕的畫師正把一張張遊客的臉定格在紙上。
有些畫得栩栩如生,有些像漫畫,但不管怎樣,每一張都有人買單。
廣場一角,有人開始唱「La Vie en Rose」。聲音不算完美,卻有種傻氣的真誠。
我看著街燈下的水痕,忽然懂了:巴黎的浪漫不是因為男人,不是因為女人,也不是因為誰的吻。
它來自那些活得太拼命的人,他們窮,他們失敗,他們醉倒在街角,可他們依然把人生丟進畫布、文字和音符裡。
蒙馬特不浪漫的時候,才是真的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