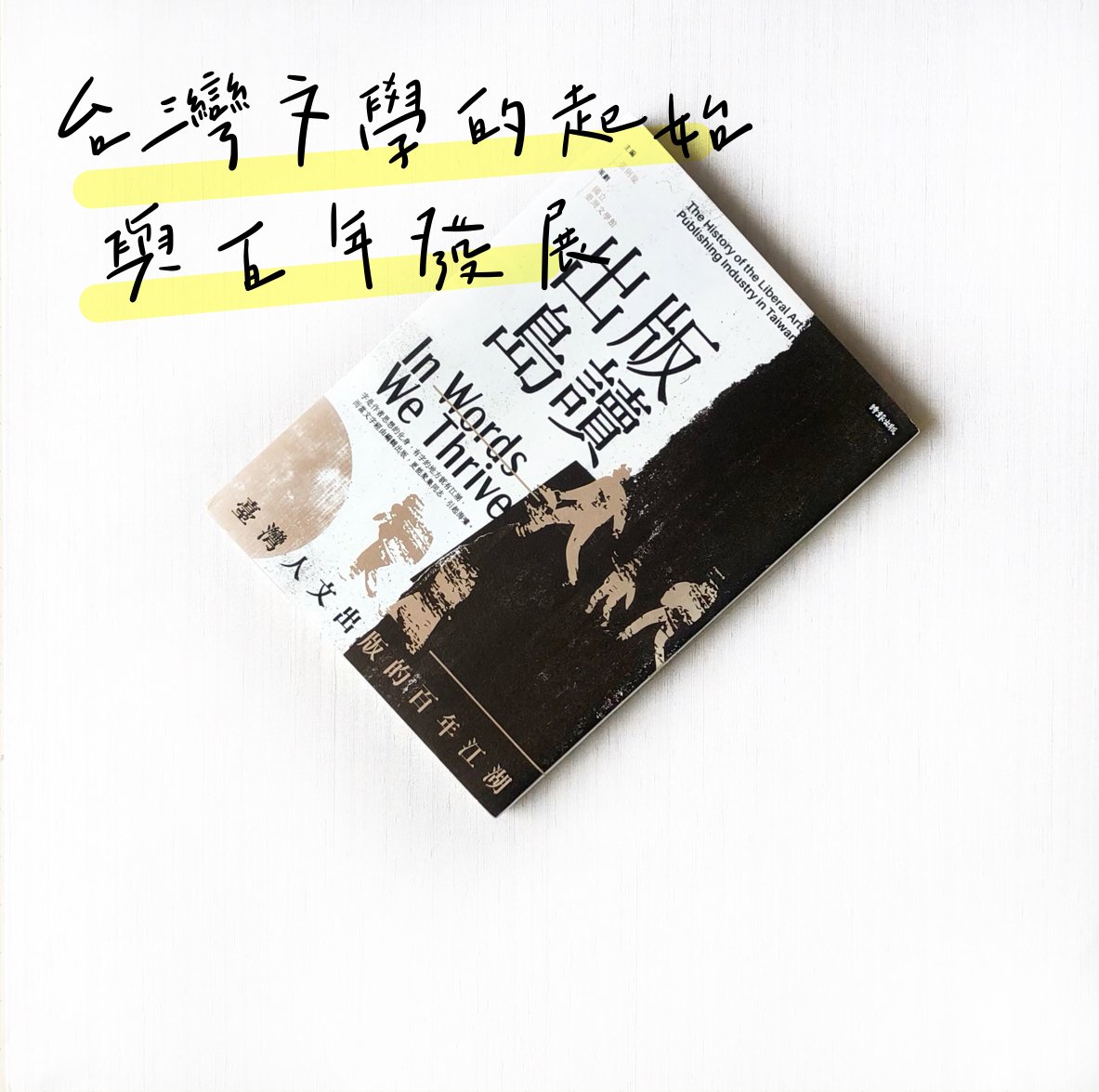「台文天文台」第一季35週的連載,正式告一段落。有23名新生代作家、文化人和文學研究者接力書寫,篇數共達33篇,而文章當中所提及的重要文學藏品,超過30件,這些寫作者所試圖連結、反應的觀點議題,都被保存在這裡。
而這一切是怎麼開始的呢?
隨著新的一年開始,「台文天文台」第二季緊鑼密鼓地持續籌備中,在新一季連載開始之前,「拾藏:臺灣文學物語」推出新系列——「拾藏幕後」,此系列將不定期更新,在「拾藏」背後,團隊對於文學、博物館與社會之間的連結觀察、書寫者對於轉譯的理解,和從過程獲得的心得,如何化做平台的想像與期待。文學館與館藏的「存在」哲學
2003年,國立臺灣文學館(以下簡稱臺文館)開館,可以說是臺灣文學史上極富時空意義的里程碑。從時間而言,臺文館的成立,意味著「臺灣文學」在歷史上終於獲得正名,並伴隨體制化成為知識學科的歷史時刻;從空間而言,臺文館接合「臺南州廳」的百年建物,並以相對有利的館舍條件,成為具備典藏、展示、研究與各種教育推廣功能的文學地標。除此之外,臺文館也藉由「文學迴鄉」系列活動、文學旅遊專書採編出版、文學館舍調查等相關計劃,積極推動文學館家族的館際網路整合,並嘗試各種跨領域合作的可能性。

做為全臺灣第一座國家級的文學主題博物館,臺文館試圖在有限的經驗和資源中,摸索出前進的道路。在這樣的脈絡下,臺文館與眾多文學館舍的成立,並執行上述各種研究推廣的事業,似乎也是一件相當自然甚至理所當然的事情。然而換個角度思考,對於作家、家屬、文學愛好者(文青)乃至於一般大眾來說,或許這個問題遠比想像的要複雜許多。
誠如作家朱宥勳在《遇見文學美麗島》一書總論中所提到的,臺灣文學在過去半個多世紀的尷尬處境中,「當代的作家寫些什麼鮮有人知,過去的作家寫些什麼沒人記得。在這樣的背景下,民間自發籌組的『文學館』,就變成非常重要的物理據點了」。回顧許多作家紀念館或文學館的成立緣起,可以發現這些館舍在相當程度上,的確是基於對作家手稿、文物等資料的保存需求而來的,也因為這樣的需求,文學館通常也被賦予博物館的使命,必須具備若干典藏的機能,並據以發展出研究、展示與教育推廣的運作模式。
換句話說,館藏終究是一間文學博物館的靈魂所在。或者退一步說,對於一個實存的空間而言,來到現場可以看到、體驗到什麼特別的內容,本身就是一個攸關場所存廢的重大問題。

但是,這些館舍與文學館藏,對於所有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到底意味著什麼?文學館的建設如何重要?又為什麼有些東西必須被大費周章地保存下來呢?或許我們必須承認的是:即使文學館策劃了許多精彩豐富的展覽、講座、出版品與各種跨領域活動,但文學館的成立,以及為什麼需要投入資源去典藏,甚或盡力修復某些文物,至少從非文學愛好者的一般人角度觀之,這並不是一件不證自明的事情。
也因此,包括臺文館在內的文學館家族們,乃至於包括文學館在內的所有博物館與相關單位在內,或許都是帶著這樣的根本而焦灼的問題意識,不斷思考著如何妥善運用受捐贈或蒐集入館的館藏,創造與一般民眾直接、間接的連結,以及線上線下互動、參與的各種形式,進而達到推廣教育的目的,讓這一切具備圓滿的意義。
但這看似簡單的一句話,卻又是所有博物館最沉重而艱難的挑戰。
我們可以嘗試思考的是:近二、三十年間,各種科技的快速成長與發展、物質生活的劇烈改變、人際之間溝通相處的方式,都已經超乎過去的想像。但每一間博物館都無法自外於現實,只能基於一個時代斷面的想像、需求與資源的限制而存在,試圖在有限的當下收集、凝視過去,追求無限的永續。而如今的人們,置身於大量知識高度開放且流動的資訊流中,進入數位化、電子化的生活型態,在這樣的時代裡,可以基於什麼樣的動機或欲求,願意主動去參訪、認識博物館內的藏品,及其背後所蘊含的各種知識與歷史經驗?至於館員們,又該如何基於專業,多方嘗試,才能在新的時代裡創造人們對於新舊物件的好奇與探索,並投入歷史與人類文明的洪流中?這或許是全世界所有的博物館都在不斷思考,並試圖超越的課題。
此外,在臺灣在地的歷史、政治與社會脈絡中,「博物館史」與「臺灣文學史」都是各自獨立且可以深究的問題。眾所周知的是,「臺灣文學」經歷了殖民統治的長期壓抑、各種意識形態的交鋒與爭論,直到近二、三十年間,才隨著臺灣主體意識的抬頭,民主化、自由化、本土化的覺醒,成為學術體制的一環,並逐漸為社會大眾所知。但是,這些文學經驗與文本累積的斷裂與空白,至今仍尚未重建完成,以至於目前仍有許多民眾對「臺灣文學」和作家所知甚少,遑論對館舍與典藏發生興趣。
因此,回過頭來重新思考文學博物館做為一個需要空間的「物理據點」,如何又為何存在──對應這個問題的詰問,可以是「為什麼館藏不完全數位化就好?」「為什麼需要保存文資?」等等──以及館舍據以成立的館藏物件,做為一時代「生活物質」的跡證,對於當下的現實可以產生哪些刺激與反饋,或許有助於我們掌握文學博物館與館藏文物的「存在」,在資訊超量、娛樂多元的網路時代中,還有什麼樣的意義、價值,以及物質上的不可取代性。
「文學物」的特殊性
無論是近年來興起的「文創」商品熱潮,或是臺灣博物館社群經過長期的耕耘和努力,以及《博物館法》專法通過後所帶來的新動向,我們不難發現近期有不少博物館,已發展出更加精緻而活潑,嘗試跨界結合科技,進而面向大眾的展覽活動與社群互動。例如近期有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與國立臺灣博物館合作的「漫筆虛實」特展,將CCC經典漫畫作品透過擴增實境AR技術加以再現;「故宮精品」藉由專業行銷團隊發想社群話題,引起粉絲對商品與藏品的興趣;故宮南院則是與「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團隊合作,企劃能親近一般民眾的線上內容。
然而,即使當前已經有這麼多案例可供參照,但對於文學博物館社群而言,同樣的策略卻未必能一體適用。就臺文館而言,在臺灣當前的博物館社群中,臺文館自然是以臺灣文學作家相關文物之典藏為主要特色。但這些文學相關的文物,與其他博物館藏常見的歷史或藝術物件不太相同,有關「文學」的抽象感知,必須經由作家生產的大量文字與相關脈絡,甚至放在文學史上才能加以構築。此外,無論是手稿、信札、書籍或相關書畫,其物質形式多為紙張、筆墨,偶有相關器具或延伸物件。

和其他便於直接理解、容易應用或引起興趣的器具或藝術藏品相比,這些以「文字」和「紙」為主的文學物,本身在視覺方面的直接張力較弱。若非經過文本的「符號化」加以轉化,並移轉到適當的物質媒介上來表現,否則較難透過復刻或簡化再製的方式,將這些藏品所搭載的內容表顯出來(或用比較年輕的說法來詮釋,就是要「有哏」),進而轉變為主打趣味、意旨的情感商品,或同時具備日常實用性的物件。即使有轉化為實用器具的可能,形式上也以文具為多。
這或許是文學藏品的侷限,但卻也是最重要、最有鑑別度的物質特性──一種極度需要時間與沉澱,才能從文字或歷史脈絡中,獲得知識、體驗,進而產生情感認同基礎的物品。而無論是策展、商品開發、文學旅行、戲劇改編或實境遊戲,所有的延伸,都必須建立在這個細緻漫長的基礎之上,才可能透過精準的轉化,在不去脈絡的狀況下,設計出能夠有效承載知識與內容的活動與商品。
其次,以紙類為主的藏品,同時也會藉由「文學」創作的物質條件變遷,突顯出文學創作的世代/時代性。舉例來說,過往的創作者自然是以紙筆直接寫作,並透過報紙、雜誌與書籍等傳統紙媒發表作品;但如今的創作者甚至一般大眾,幾乎是全面以電子化的方式進行日常生活的文字交流,乃至於文學作品的生產。如果不同世代/時代的創作者甚至一般人,其寫作與閱讀的媒介與習慣,在近二、三十年間已然發生劇變,那在出版品、報紙、雜誌等傳統紙媒沒落的時代裡,又該如何吸引民眾重新進入文學博物館,參與這場以手稿、報紙、書籍、書畫與相關文物所建構的博物視野與文學世界?
「港口鑰」:「館藏近用」的奇幻異想
正因為每個人對文學的接受程度有高有低,對臺灣文學的理解也不盡然相同,倘若要跨出學術圈或舒適圈,真正從一般人的角度思考最大普及的可能性,我們或許要賦予藏品做為「物件」,以及文學館做為「空間」更多的想像和詮釋。為此,我曾在一場對高中生的演講中,試著這樣描述文學館和藏品的存在。
我想起在膾炙人口的奇幻小說《哈利波特》當中,有一種魔法道具叫做「港口鑰」,它的功能是可以一次將接觸到它的所有人傳送到指定的位置,不用像其他的傳送術一樣需要經過特殊訓練,也沒有風險。而且,為了防止「麻瓜」(不會魔法的人)誤觸,「港口鑰」通常會是一般人不會特別注意或不太起眼的日常物品,只有魔法世界的人才會知道這個機關。

「港口鑰」這玩意兒聽起來,是不是和文學館裡面的藏品非常相似呢?在文學館中被謹慎保存下來的手稿、書畫、報紙、信件、書籍與相關文物,其實多半就是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過的物品(紙),有些東西甚至我們如今也越來越少使用。若非經過作家家屬悉心保存,或是經由學術研究發掘其重要性,對一般人而言,或許就真的是不太起眼,可能下一秒就會被拿去資源回收的東西。
但是,只要有文學的知識做為魔法基因,身為一個讀者,就能看出這些看似平常的物品,其實都不只是一般老舊的物件而已,它不但可以讓讀者因為某些故事、展覽或活動內容,在當下就進行一趟文學的移動,更可以跨越時空,把讀者迅速傳送到臺灣文學史上的每一個精彩的場景當中!
這些數量龐大的館藏,不但是文學博物館賴以存在的重要基礎,重要的是,館藏物件本身豐富的資訊、內涵與價值,如何在臺灣文學的學術專業、跨領域對話、跨產業合作的各種層次基礎之上,被轉化為現代的語言和形式,透過文化商品的再現與傳播,成為一把能夠打開大眾心中那道文學之門的鑰匙?
生為創作者,作家們用紙和筆充實了自己的生命,完成了寫作的使命。作家的家屬後代,也完成了守護這些寶貴資產的任務。剩下的,就是我們如何找到這些「港口鑰」,開啟一趟尋找文學與歷史靈光的航程。
——原刊於《台灣文學館通訊》59期「交流與對話」
★鄭清鴻@拾藏
★作者簡介
鄭清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語系學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文系碩士。現為前衛出版社主編、「藏品故事轉化行銷計畫」主持人,曾任永和社區大學臺灣文學課程講師。學術興趣為臺灣文學本土論、文學史、本土語文與文學博物館。目前把臺灣文學出版與教學當成社會運動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