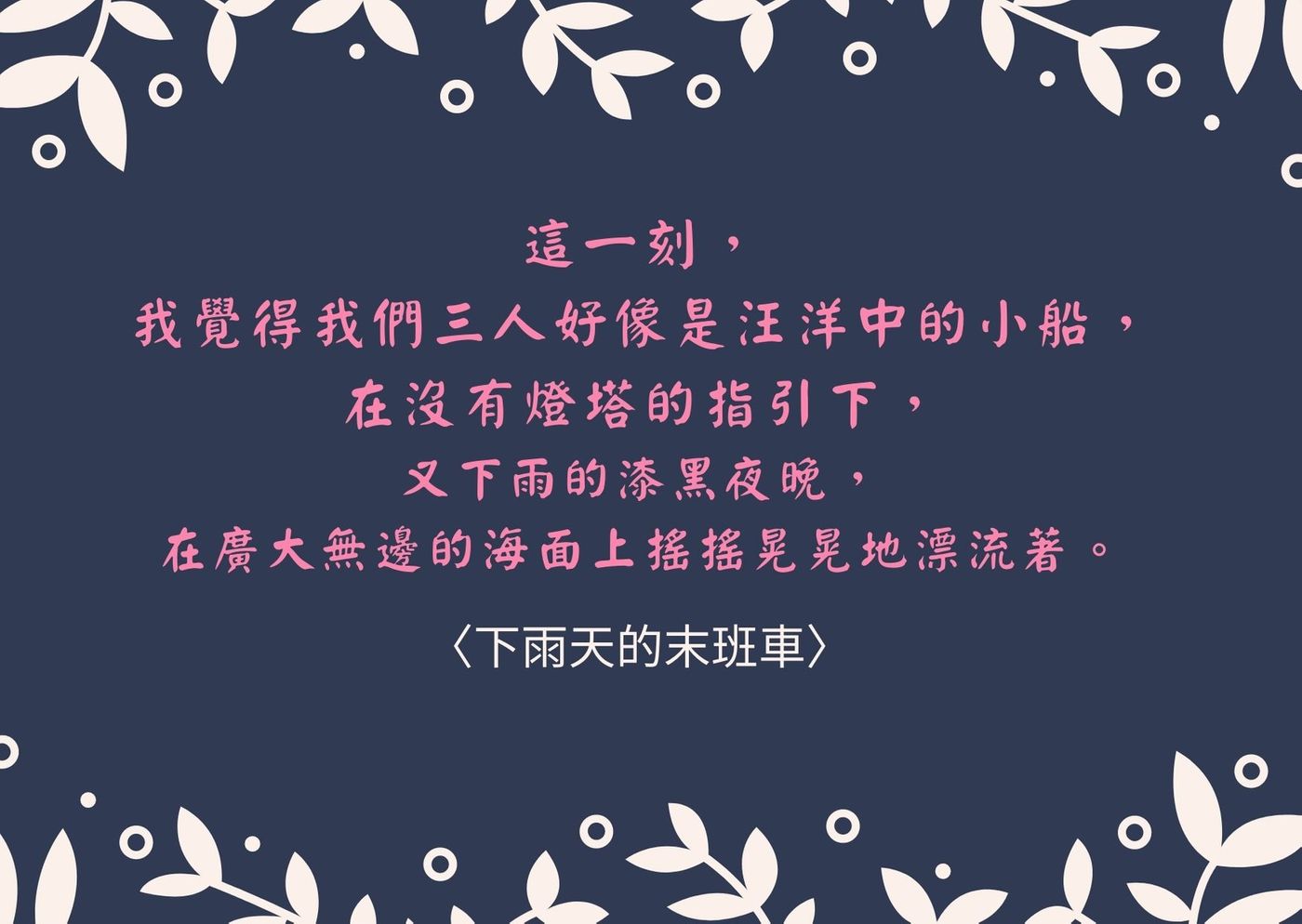昨天的告別式,是個好日子,天氣晴朗,園區內的車格都被停滿。隨著家人來到禮堂,和姑姑長輩們打招呼,對他們大部分的印象都存在我兒時的記憶裡,因為某些因故後來便漸少往來,這段時間都十年有了吧,只能偶爾聽我媽轉述她們的發展怎麼樣。
儀式要開始前,我媽對我招手示意要我一起跟著禮儀人員入廳堂,我聽到她們稱我為「長孫」。事實上我不是,長孫指的應該是大哥的兒子。後來問起,我媽只輕聲地說「He is not coming.」或許世故的人可以解讀出一些其他涵義,成為一兩個茶餘飯後的話題,但那些我是不懂的。也好,我並不排斥在這段儀式上多承擔一點責任,扮演一個和長輩關係深厚的送行者角色。再加上我穿的體面、精神奕奕,我想讓我來是很好的安排,奶奶看見我這樣便可以放心,風風光光的給外人看見,奶奶也會很有面子。
我穿上麻衣,跟著禮儀人員進行一段段的流程,手持線香捧著神主牌。其實我最擔心的部分是萬一某些時候太過冷靜怎麼辦?我這個人總是理性跑在感性前頭,情緒要很慢很慢的時候才慢慢浮現。萬一我演不好長孫該有的悲戚怎麼辦?一直處於冷靜狀態觀察別人的反應是很糟糕的事情。在地下室認親時,我聽到身後的長輩一聲聲情感深厚的「媽!」脫口而出。我仔細端詳奶奶的面容,躺在棺木裡的她瘦削許多,一時不容易辨認,我輕輕地喚了聲「阿嬤,我來看妳了。」
在廳堂後面的入殮室,披麻戴孝的兒女子孫們圍繞著奶奶,時而唸幾句經文時而作拜。而在某一段儀式中,禮儀人員讓我們幾位穿著麻衣的親人圍繞在奶奶身邊,向我們說明,等一下要用手接觸往生著的身體,向她說一些話,如果有宗教信仰或是生理期的人,這部分可以省略不用做。我並不忌諱這樣的儀式,因此我把手指稍微攤開來,隔著一層布,碰觸了奶奶額頭的位置。「好硬」那是我當時心中的想法,像是摸到一塊年代久遠木質長椅的椅背,但是我知道在這個位置不久前蘊含著深厚的生命力。禮儀人員帶著我們一句一句的念:「妳現在身體的病痛都好了,可以好好休息了,我們都已經長大,不需要再為我們操心了,我們會好好照顧自己。」念這段安慰話的時我感覺同時也在安慰著自己,試圖傳達的溫和情感經過我時劇烈震盪了起來,口罩內完全化作一團濕氣,每個吐出口的字音都不再正確的位置上,鼻酸的讓我沒辦法好好講完。
回到大廳,就是跟著師傅念長長的經文,經文內容大概是在說一個遙遠的奇幻國度發生的故事,長到讓人不禁懷疑這有考慮到家屬的感受嗎。我擅自微微擺動著下肢,試圖加入一些韻律感,好讓漫長的經文顯得不這麼難受。後來便是一些縣民代表前來奉花獻果。儀式雖然已經盡可能簡便,但時間也長得讓人胡思亂想。像那親切挽著我手的大伯,殷勤地告訴我接下來會有哪些人來上香,家屬需要答禮等等。我幾乎不確定他是不是當年那個欠了一屁股賭債,跑路害的上一代家人都活在恐懼之中的那個大伯。我望向奶奶的照片,她的五官是剛毅的,不帶喜怒的望向前方。我想著我爸也有這樣的五官,脾氣十分爆烈,奶奶據稱卻是個沒有什麼脾氣的人,大伯留下債務,她卻安安靜靜的到工廠打工維持住整個家。中間的休息時間,大伯都在桌前啜泣,背脊微微的聳動著,那些鮮花水果啊,擺得真是很漂亮。
儀式的尾端,我捧斗撐傘,看著奶奶上車,跟著車子送了一段,然後便將我們載往鄰近市郊的火化場。要過一座橋,司機不忘記回頭提醒我們喚奶奶過橋。火化場的環境是很清幽的,四下無聲,樹木環繞茂盛,幾隻狗兒窩在廊下享受一些午後陽光的暖氣。家屬集合,我跪在室內冰涼的花崗岩上,齊聲提醒奶奶她即將要去西方極樂世界,請不要有牽掛,等一下火來了要快跑。我知道這就是最後一站了,從此天人永隔。其實我不知道您是否早已遠去,在那認不得人,臥病在床的最後三年。我沒有這樣跟任何一個人道別過,往後的記憶將逐漸淡薄,神明都在看,陽世陰間的距離彷彿就隔著薄薄的一片玻璃窗。我畢恭畢敬的磕頭,我不在乎別人怎麼看我,像以前我從遙遠的人群觀望長輩們服從禮儀。我深深的將額頭碰觸舖有紅地毯的地面,這樣的肢體動作所要傳達出的訊息使我由內而外都微微顫動著,如果能將我的訊息傳得更遠,那就這樣吧!起身時眼淚從我臉頰筆直滑落,我不曾感受到這麼情緒滿溢的時刻。
再見了阿嬤ㅡㅡㅡ 謝謝妳賜給我生命,讓我能感受一切的苦楚和悲傷 ,還有自由自在選擇生活的權利,再見ㅡㅡ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