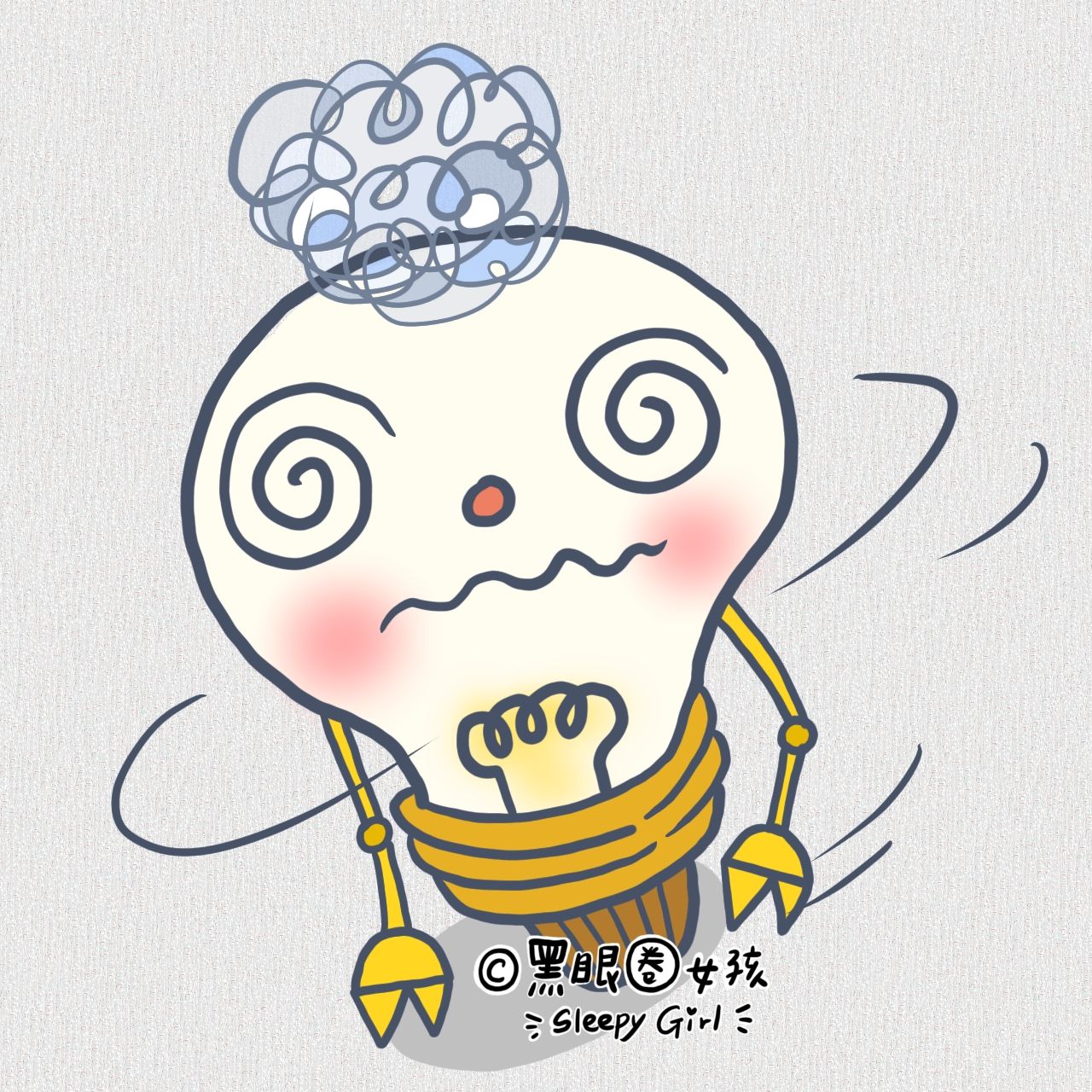逼!逼!兩聲開車鎖的聲響劃破寧靜的夜空傳來,直搗耳膜。我心裡一驚,低頭看了看時間,凌晨00:13,才疑惑阿爸為什麼在這時間出門?下一秒又恍然。
*
那天中午下樓吃午餐,阿母說,阿嬤狀況不樂觀,飯後大家去探視一下。我夾菜的筷子停頓了幾秒鐘,輕聲回了句:「好。」疫情期間有管制探訪人數,一次只能兩人進房,我和妹妹穿好隔離衣、噴了酒精後,走了進去。
看到阿嬤的那一瞬間,心無預警地揪在一塊。帶著氧氣罩的阿嬤雙眼緊閉,胸脯以極不自然的大幅度上下起伏,帶動空氣振動,發出不順暢到令人心慌的呼吸聲,好似下一秒就要喘不過氣來,連帶我都覺得空氣變得稀薄。視線由上而下緩緩掃描而過,阿嬤原本乾瘦的雙手雙腳都因為各種藥物注射而嚴重水腫。
我不禁移開視線,假裝查看一下房間內部,思緒神遊。
我以後會怎麼離開呢?我不想因為意外而失去自理能力、不想為失智症所苦、不想在病榻上煎熬、不想在病痛中反覆折磨,但是,除非自殺,又有誰可以選擇怎麼死?
拉回思緒,深吸幾口氣後,視線再度回到阿嬤那爬滿皺紋的臉上,猶豫片刻,我把手搭在她肩上,輕聲叫喚,再輕拍幾下,阿嬤的眼睫毛顫動,眼睛慢慢睜了開來。
「阿嬤!」我靠近她耳邊,不自然地用台語說,「我是XX啦,我來看妳了。」
阿嬤無法說話,我甚至不確定,她那混濁迷濛的雙眼裡,是否真的看到了我們。
無措地對著她說了幾句話後,我幫她拉了拉被子,說了聲「阿嬤,妳繼續睡,好好休息,我們下次再來看妳」,便靜靜地離開。
狀況不樂觀,危急,這幾個字眼在這幾年反覆了幾次,但是那日的轉身,直覺在我耳邊私語,這次大概真的是最後一面了。
*
阿爸車子駛出後不久,我接到電話。凌晨12點整,阿嬤離開了。
我走出房門,喚妹妹一起下樓,在客廳等著。
妹妹哽咽地說著難過,我無語,怕一開口會淚崩。
原來人可以內心天翻地覆,表面卻仍平靜淡然無波。
外面人車嘈雜起來,我起身開門讓弟弟進來,按吩咐撕掉家裡樓上樓下的春聯,那乾掉的漿糊竟是頑強,怎麼也撕不乾淨。弟弟爬上爬下時,脛前被陽台上剝落的磁磚劃出一道長達十幾公分、寬兩公分的傷痕,即便在夜裡,那血痕還是怵目驚心。
很多人進進出出,我認識的、我不認識的、認識我而我不認識的、彼此不認識的。
聽從各種指示跪著對阿嬤說話,看著躺在眼前的軀體,還是有種不真實的抽離感。
長輩們討論著事情。我們兄弟姊妹四人站在旁邊一角候著。凌晨兩點多,不太怕熱的我竟不斷冒起汗來,腰腹側也莫名陣陣抽痛,我微微曲著腰,用手抹汗、搧風。弟弟悄聲說,妳可以先回去休息。我不確定,仍待在原處不動。後來哥哥也說,妳們先回去,沒關係。我才與妹妹慢慢踱步回家。這種時候覺得,嗯,有兄弟姊妹,真好,當女生,也是有一點點好處的。
不知道是因為弟弟腳上那傷痕讓恐血的我產生身理不適,還是因為阿嬤的離開造成的情緒波動,一夜因反胃想吐與全身痠痛而輾轉反側,直到天光亮起才昏昏睡去。
近午時醒來,覺得幾小時前的事情恍如夢。
*
在電腦前努力敲著鍵盤趕稿,阿爸叫我下樓陪小蠻牛去上香,明明好幾人,幹嘛非得要我跟著去?
原來是要我扮演安撫的角色。
一踏出門小蠻牛似乎就感應到了什麼(是什麼?),一直想往回跑,大夥兒來回抓了好幾次,快到時,他腳下生根似地不肯前進,十分抗拒。要上香時更是雙拳緊握在胸前,一臉泫然。
「不要怕!」他突然語帶顫抖地大喊了一句,好像在跟自己打氣,實在可愛又可憐,我蹲下身緊緊抱著他,拍拍背說姑姑在不要怕,他又說了一次「不要怕!」這一聲帶哭腔,緊接著便嚎啕大哭起來。
看來是真的怕極了,讓我好不心疼,趕緊匆匆上個香便帶他回家,也跟大家說好,還小,就不要再勉強他了吧。
*
阿母很開心地說,她要到一張把阿嬤拍得很好看的照片,製成立牌擺在阿嬤靈堂前。
去上香,我遠遠便看到了。
真的拍得很好看,滿臉的笑,那是我從未在阿嬤臉上看到的,原來我的鋼鐵阿嬤也曾露出這般幸福的笑容。
我不禁想,我們的不親,是不是我也有錯?
我問,照片哪來的,阿母說是向堂姐要的,很久以前有次跟團揪阿嬤出遊時拍的。
我問,我們有跟阿嬤出去玩過嗎?阿母說有,但那時我還小,沒印象了,所以我沒有跟阿嬤出遊的記憶。
我問,照片呢?我們有跟阿嬤拍過照嗎?阿母說有,九十大壽慶生時,在客廳拍了幾張全家福。啊,對,這我想起來了,那時喬位置喬了好久,一家十一口前後排兩排,或坐或站,所以人臉都小小的。除此之外好像就沒有了。我沒有跟阿嬤合照過,一張也沒有。
想來有些遺憾。
在死亡面前,再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成奢侈。
*

說好了這次要走極簡路線,相較於多年前阿公那鋪張到讓活人沒活路的畢業典禮,這次的確簡單了不少,以我的標準來看仍舊是繁複到沒必要,但,至少不那麼虛偽。
對於傳統喪禮一直有各種不解,比如,孝女白琴是哪招?還記得小時候參加外公喪禮時,看著一個不認識的人拿著麥克風俯著棺材哭天搶地,小小年紀的我滿頭問號。
幸好如今不再固守那些古禮。
我家早就說好基本上人走了燒了送走,錢留給活人用,其他沒必要,孝,得生前盡,而不是死後做給人看。
無奈這是阿嬤的畢業典禮,有大批親戚在,嘴巴多,誦誦經摺摺蓮花拜這拜那有的沒的還是免不了。
最累大概是守靈,這是阿爸擔當,哥哥弟弟抽空輪替。女生不必,看,當女生也是有好的時候。
最耗時間的還是誦經。
誦經,一次三四小時起跳,幸好如今是站著聽經,還有椅子可以偶爾坐一下,不必像小時候阿公過世後那樣跪不停跪到膝蓋都瘀青。
第一場,我刻意坐在最後方,聽了快兩小時,已過九點,阿母轉身打暗號,我和哥哥便先悄悄離席,哥哥回家還有段路程,隔天一早要上班;而我,自然還是要趕稿的,自由工作者可沒有喪假可請,截稿日還是繼續在後頭緊追不捨。哥哥陪我走回家,確認我鎖好門才離開,難得暖心。
第二場,頭七,待了一上午。不得不讚嘆誦經的人好厲害,這樣又是念又是唱的,那些經文都充盈在舌尖般順暢地流洩而出。經文為什麼聽起來像中文又像台語呢?要不是有本子可看,光聽還真的聽不出所以然,如果不專心聽,分神一秒鐘就會不知道這文念到哪一行去了。啊,聽完的收穫便是,原來菩薩有分這麼多種,長了好像蠻無用的小知識。
第三場,出殯前日,從早到晚折騰了一整天,累爆,膝關節處隱隱作痛。我懷疑這些喪禮法事大概是為了讓人沒有餘裕和力氣去悲傷而設的(並不是)。
慶幸疫情期間口罩不離口,可以毫不顧慮地面無表情,不必勉強自己控制面部神經去應付親戚。
*
出殯。與阿嬤生肖相沖,這最後一程,我和阿母是不能送的。
於是由我負責送小蠻牛去上學,阿母說我可以睡到七點,不必像大家一樣早上五點就起床。結果一早卻在睡夢中被弟弟的吼聲驚醒,以為鬧鐘沒響或被我按掉了,驚慌地衝下樓,結果根本還沒七點,卻還是被念了一頓,這跟原本說的不一樣呀,我委屈。
一再確認,最晚8:20要到校。在那之前便是先看顧小蠻牛,陪玩。
學校不遠,07:50再出門也綽綽有餘,但這可是姑姑我第一次送小蠻牛去上學,好緊張,坐立不安,決定還是早點出門,還沒7:30便催促小蠻牛穿襪穿鞋穿外套拿書包。
要出發時怎麼也找不到機車鑰匙(慌),只好騎另一台,結果踏出家門傻了眼。好多車,好多機車,大概都是來送阿嬤的人停的。弟弟不是說已經幫我把機車移出來了?在哪裡!?(慌)
牽著小蠻牛找了半天,盤算著該打電話給誰求救才好,可這時根本沒有人可以接電話呀。都急出一頭汗了才終於在機車海中隱約看到熟悉的車影。原來是被人推進去車庫最最最裡面,車庫裡暗,機車又是黑的,難怪找不到。
找到了,問題也來了,被一大堆機車外加一輛斜插的汽車給擋住可怎麼辦!(慌)只好叫小蠻牛坐在別人機車上等,我使盡全力一台又一台地挪阿挪啊,還要小心彼此不刮到車身,滿頭滿身汗涔涔,如摩西分紅海般在停得亂七八糟的機車海中開闢出一條小道……
天啊,還好我有提早出門!
在這一陣慌慌張張中,我終於坐上了機車,再伸手幫小蠻牛上車,接著扣好固定背帶,發動機車後,發現了一個問題:這台機車不是我的,本就騎不太習慣,再加上座椅有個弧度,前低後高,前面坐處稍稍下凹,而小蠻牛上車後便往前滑,把我的屁股也往前推,我倆一大一小的屁股就擠在那個圓弧下凹處。試圖用手把小蠻牛往後挪,卻是怎麼也挪不動,口頭跟他說,他也不明白。不得已,最終用一種四肢擠壓在狹窄空間般詭異又好笑的姿勢,勉勉強強出發了。
每次載小朋友(姪子姪女)都壓力山大,畢竟背負的是寶貴的小生命,出了什麼意外,我無家累,死了也就死了,其他生命我賠不起,也承受不住。所以除非必要,我真的很少騎機車載他們,如果要載,都會謹慎至極。出發時,會姑姪一起喊著「小心小心再小心」,以時速大概2-30的龜速前進。
結果騎好久,到校停好機車後才發現,那個詭異的姿勢讓我整個肩頸背部都痠痛!幸好沒遲到。
騎回家,又是在一堆人海中不斷「不好意思借過一下」才好不容易把機車塞進車棚裡……。
沒想到最輕鬆的接送任務竟搞得我一大早就虛脫!
*
《每天,回家的路就更漫長》中有這麼一段話:「幾乎所有在這裡走來走去的大人,都因為某一次沒能好好說再見而懊悔,他們都但願自己能夠回到過去,把那次再見說得像樣一點。」我後來總會回想起病榻旁的那一面,覺得自己因為當時過於徬徨而沒能好好道別,話全卡在喉嚨裡出不來。
我很慶幸來得及見她最後一面,卻也因為那一面,讓我心緒遲遲無法平復下來,沒有肝腸寸斷也沒有撕心裂肺,卻有一股吐不出來的氣堵在喉頭,說不出的哀傷壓在心頭。
阿嬤出殯的那天傍晚,用LINE告知好姊妹,只是敲下「阿嬤今天出殯」幾個字都覺得難。字句的力量,將幾天來在胸中盤旋不去的那股悶氣具象化,是真真切切的悲傷二字。
即便我知道離開是一種解脫,即便大家都說阿嬤是去了更好的地方,即便我從不認為我們有多麼深厚的情感,即便這一刻來得並不突然,情緒還是來得比我預想的還要兇猛很多,很多。
人在面對死亡是孤獨的,面對他人的死亡時也是,離別這件事,果然無論怎麼練習都沒用。
*
姪女和「阿祖」相處時間極少且交流次數寥寥可數,在一次法事結束後,她問:「剛剛是誰在哭?」
「阿嬤吧?」我沒承認自己的眼淚也沒把持住。
「為什麼要哭呢?」她疑惑。
是啊,為什麼呢?別說小小年紀的她不明白了,我自己也對這樣的情感很是迷惘,畢竟我不認為自己有那麼愛阿嬤,時不時的恨意倒是頗為明確。
想了想,盡量淡然地回答她:
「因為住在一起太多太多年了,有感情呀,有感情的人離開了,會傷心嘛。」
*
韓劇《海岸村恰恰恰》完結了,打開追完最後的那兩集。
「我感覺她好像還在我身邊,我還不想送她離開,希望她能留在我身邊久一點。」
「失去心愛的人時,必須徹底難過個夠,否則悲傷會佈滿全身,最後爆發。」
為期整整兩週的治喪期間,我幾次哽咽,幾次紅了眼眶,幾次默默掉淚,情緒是內斂的眼淚是克制的,送阿嬤離開後,自以為已收拾好了心情,卻在觀劇時的最後這兩集裡眼淚大潰堤。
當然,任眼淚恣意縱情開完派對也就是一晚的事,日子總是要繼續過。
阿母說,阿爸那天上班前先去看阿嬤,要離開時跟她說晚上再來看她,阿嬤搖頭不願意,阿爸只好請假沒去工作,也吩咐大家分批去探視。
阿母說,那天在病床旁跟醫生談話時,阿嬤眼神一直追著她,似是有話想說,卻已無法言語,只能用猜的用問的,阿嬤搖頭點頭來示意,雖然沒能親口聽她說,但阿母說她知道,阿嬤跟阿公一樣,想在離世前對她說謝謝。面對阿母的肉麻問話,阿嬤竟是激動地點頭。
從阿母訴說時的表情,我知道,她跟阿嬤和解了,這麼漫長歲月裡的愛恨都在那一刻輕輕放下了。
我知道這對阿母來說有多重要,至少在我看來,阿母是阿嬤一生中共享過最多情緒與時間的人,多過其他兒女子孫,即便這兩人一滴血緣關係也沒有。
我的鋼鐵阿嬤,走到人生盡頭處時,內心是否也對我們有情了呢?我的鋼鐵阿嬤,在最後那一刻,內心是否像坎離奶奶一樣平靜而富足呢?
這我永遠不知道,只想說,阿嬤,一路走好。
_金魚腦,隨手記09(202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