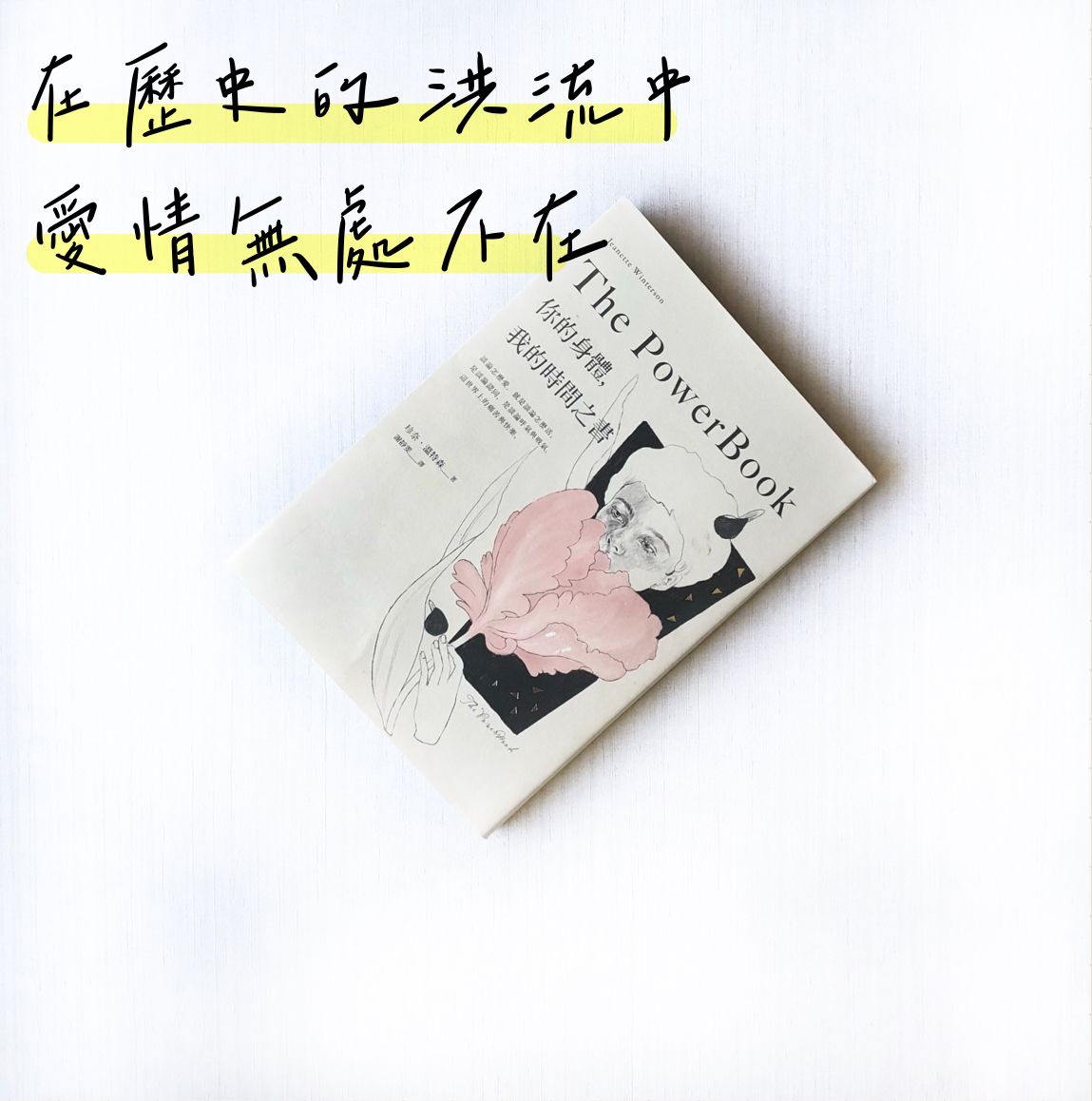圖片來源:木馬文化
❝ Book of Hours 又稱「時禱書」或「禱告書」。中世紀在北歐基督徒之間盛行的私人祈禱書,是附有彩繪裝飾的手抄本。❞
──《你的身體,我的時間之書》譯註 44 號
一個書寫者激動不已的捧讀。一個情人放逐了自身附屬的對象。一個故事反芻另一個故事,致使歷史與記憶的臟器翻攪不寧。還有,愛情何以殲滅獨有的肉身與現實,讓你我成為世界的風⋯⋯關於這一切,《你的身體,我的時間之書》(下簡稱《時間之書》)顯然不僅是一本書,而如原文書名《The PowerBook》* 所暗示的,是一股力量:創造的力量,虛構的力量,感受,以及信仰。它推動故事,猶如擠壓板塊那樣塑造海陸、皺褶與斷層,亦如星辰之間的斥引,陷落時域之差,迸裂銀河之流淌。
《時間之書》是以故事為原料的建物。神話、寓言、傳說、新聞報導、童年回憶,以草圖的模樣串聯展示,猶如沒有覆面、筋骨裸露的建物。這些故事講述者不明,而盡頭虛隱,它們攢蹙累積,藉由流傳與變異,掙脫凝固的僵局。閱讀行文如同走入滿廳浮雕與琳瑯壁畫,豐盛的視聽效果不仰賴細膩的寫實描繪,反而來自一種跳脫的幻知:心靈諸多所見,莫衷一是。因而恣意陳列,因而築起擺放多重人生的博物館,從史前到有字,一個書寫的人渴求遍覽。
作者珍奈.溫特森(Jeanette Winterson)或許是一個經常對現實起疑的人。她相信生命不只有一種經驗版本,所以時時留意日常縫隙閃現的綻口:鏡像,雨滴,水窪,愛人之眼 ── 每一,都映射出萬千。
「陌生人是個安全的所在。什麼都可以對陌生人說。」
「要是我把它寫進我的書裡呢?」
「你寫的是小說啊。」
「所以?」
「所以你不會把我和事實拴在一起。」
「可是我可能會說出真相。」
「事實永遠不會說出真相。連最簡單的事實都有誤導作用。」
「像是火車的時刻。」
「還有你有過多少情人。」
寫故事的人善藏。最淺薄的書寫者在幻象世界裡自我滿足,最嚴厲的書寫者則在推翻現實的同時粉碎了遐想,將每一寸自我的感知當作獵物,藉敘事的網羅,捕獲關於存在、關於此時此刻的真貌。非如此不可。非用盡氣力、毫無保留地將那些熱烈與懊悔織進字裡不可:援引虛構之柴,在自己的人生裡縱火。為什麼?《時間之書》最後一頁寫道:「回家吧,把那個故事再寫一次。繼續寫,因為總有一天她會去讀。」可我認為,與其說是繪者為挽留被畫者最後一次穿透帆布的凝視,而反覆塗抹,「界定生命的疆域」,大概才是書寫這個並不唯一的故事的真實目的。
書中舉例了林布蘭。珍奈.溫特森定義那些變化多端的自畫像不是照片,而是劇場。「定點就是藝術家本身,可是定點只是大本營,從那裡出發的旅程才是讓人饒富興味的。林布蘭的畫作是往外的旅程,而途經的心靈距離可以用光來測量。」如同拋甩釣繩,你以為銜鉤之魚才是世界的實心,但那飛線的弧度已然醞釀啟動整個宇宙的能量。冒險者需索的是尋覓的征途而非寶藏,而看穿這一切的書寫者,選擇直搗故事之核而非鋪設它的嚴整外殼。另一種身分、另一張面貌,都不是林布蘭或珍奈.溫特森透過解構自身意欲抵達的平行時空,他們渴盼的就是崩解本身 ── 崩解侷限與封閉的述說法則。創作者緊握異名和分身的特權,為的是更祕密地經歷真實生命。
「戀人們都覺得自己是創造者嗎?」電影《燃燒女子的畫像》如此問道,比起叩問,更像宣言。《時間之書》可能會這麼問:「創造者都覺得自己是戀人嗎?」當字句調度起記憶和感觸,它們將抽長、凋零、復甦、更新,變得自成一格,運作眾多分分合合,將不存在的親密時光、或者一個房間的淪陷給寫「實」。「為什麼你好像在書寫『我』給我自己?」作者與角色的幽微關係,在鬆動虛構與非虛構邊界的文體演化史中有著持續不歇的探討,《時間之書》便具有此強烈的後設特徵,當它詢問愛情的本質,其實也在詢問創作的本質。
❍
這本奇異的(queer)小說所創造的,是一個隱身於電腦螢幕後的作者,接待每一則渴求「一晚的自由」的訊息;她為他們量身訂製虛擬的劇本,當然也為捧著這本書的我們。那些能言善道的敘述者隨著時代與場景不斷更迭,維繫彼此的,是跨越時空的永恆愛戀 ── 暴烈又溫柔的愛情,刺穿雙手雙腳的愛情,讓痛苦成為感官受器的愛情。身體作為盛裝慾望的容器,鄙陋同時純潔,如水火,無定形,以千萬種面貌停留於世:「死亡會將我擊潰。但為了服務愛情,我已被擊潰多次。」是的,「平靜地愛你,等於完全不愛你。」本書主軸正是以精簡筆觸速寫的,一段又一段燃燒烈愛。
土耳其少女艾利流變為男體,將鬱金香球莖假扮為性器偷渡至荷蘭引發園藝狂熱。湖之武士蘭斯洛特因為愛上君王的妻子悔罪七年,將心靈鍛鍊為抗衡死亡的哀婉之愛。囚於石堡多年的公主弗蘭茄斯卡被迫接受政治聯姻,她願為此生一瞬的、愛人與被愛的自由賠上一切。卑微的獵人化作更卑微的獵物,化作一隻毛色火紅的狐狸踉蹌奔過雪地,換得公主的登高等待卻仍舊得不到她的垂憐。心愛女人被劫走的奧蘭朵,在液態的森林和幻影宮殿尋尋覓覓,逐漸發覺此地沒有別的,只有無數個遁入死胡同的想望⋯⋯但更多時候,故事的述說者與書寫者,是一名介入他人婚姻的第三者,她輾轉於古老的城市,和昔日那尚未迎面而來的戀人重逢,性慾與愛意猶如電流,讓她久久顫慄。
紛雜支離的時態運用,在《時間之書》內起了非凡效果。除了相異故事之間的跳躍與互文,單一敘事線同樣充滿分叉和毛球。譬如主語的切換,有時是第一人稱,有時又似全知觀點。譬如順敘法的出格,當書中人物漫步城市、彼此對談,述說者卻冷不防推移了位置,從某個讀者對其全然無知的未來回顧:「那就是我記憶中的她,在巴黎的木橋上笑我。」── 我說過,書寫者善藏,越淡描的往往越深刻。而「過去中的過去」亦在行文之間繁複閃現:「我們趕上駛向羅浮宮的一班火車。你想穿過大玻璃金字塔、走到地平面上。你說那就像重生。你說那讓你覺得自己是埃及公主;一時半刻,我還以為自己當初在卡納克神殿旁邊的河流就認識了你。」
如此敘寫,深情且美。往事總挾帶著其他往事:建築師在城市種植宏偉卻終究湮滅的沙漠文明,小說家在垂直壁立的光陰之側摸索一道潘洛斯階梯;受苦的愛人為了再次撫觸彼此的脊軸,拒絕擺脫輪迴。而這裡,就是這一日,無論是羅浮宮或尼羅河,一絲雨都足以召喚一座海。古今皆然的光線玩弄著事物的表面:虛像,投影,模糊淡出的場景,一切同時存在。書寫與愛,讓我們貼近永恆。
❍
《時間之書》所要談論的綿密,並非結實的文句得以砌鑿,但我們依然可以試著簡單收束這本書的主旨:愛情如何作為人類生命中的靈異現象,然後成為命運,成為歷史。
愛情與死亡平起平坐,予人難以迴避的絕境,以及真正自由的契機。愛情也將生命的遊歷絲絲入扣,在時光裡注入無限的交錯對視,讓一日之內的尋常景物,印記無須註明日期的承諾。「沒有懊悔能夠平定愛情⋯⋯我曾在敞放的天際之下愛上你,死亡也改變不了此事。」蘭斯洛特如是說。而那名與有夫之婦豔遇的小說家,在床榻性愛之時傾聽廉價水療旅社的噪音,乞求私奔之時留意火車乘客的反應;巴黎午後燦爛的約會,她記得暴雨放晴之後的路面如同鍍了水銀,記得地鐵站奔湧而出的弦樂四重奏;而在卡布里賽馬場,燭台放置路面使得行人似雙足燃燒的神祇,入夜的曲巷如同黑貓細瘦。她對這些事物描述地那麼仔細、那麼逼真,卻從未坦率地寫過愛人的身體和臉龐。
曾經有過那樣的瞬間嗎?記得一切,就是不記得你。愛情的席捲與豪奪,讓每個置身其中的人掘開屬於自身的傳奇,將眾多「偉大且具毀滅性的情人們」烙印在自己的影子上,拽著它倒向每一日的太陽。然後,也許,日全蝕就發生了,讓習於白晝的眼神,窺見了不同凡響的另一種天空的容顏。
「而愛情只不過是、向來都是:你看著我、渴望我,而我並未轉身離開。」
當書寫者凝視空白,隱形的字句同時凝視著她。當戀人相對無語,其力量,令時間動彈不得。《時間之書》匯集滴水穿石的故事,打通所有的孔穴,讓流過的風成為音樂,讓一瞬的懸念,綿延至心的盡頭。它理應是紊亂的。它也必須是歪曲的、斷裂的、解構的、散射的、自我重複的 ── 為了觸及真相,而不只是說出事實。熱愛虛構的人比誰都熱愛真實,他們將用一生書寫同一個故事,直到那故事自動書寫了它自己,而反過來勾勒、連綴所有踽踽獨行的人生。
「跟著它走,我就可以找到時光停止的地方。死亡停止的地方。愛情所在的地方。」珍奈.溫特森寫道。向內,果真是唯一的路。《時間之書》是獻給書寫者的讀物,是抵抗空無的斑斕創世。閱讀此書,我無數次感覺能寫真好 ── 能寫,真美。就像擁有特異功能或魔法那樣,書寫拓延存在的疆域,讓灼燒不盡的事物繼續燎原,讓珍奇瑰麗的珊瑚擁有一片溫暖的海域。在那裡,你將展開愛人的軀殼,細讀每道刻度。
是什麼,讓時間成為一本書呢?或是,成為一曲吟詠、一則傳說、一篇詩歌、一張圖像⋯⋯總之,一場虛構?是愛情吧。是愛情嗎?我猶疑著這樣的問題是否經得起邏輯推敲,忽然想起《時時刻刻》最後一幕,維吉尼亞.吳爾芙留給丈夫雷納德的遺書寫道:「Always, the love. Always, the hours.」── 原來,她好久以前就告訴我們答案了。

Theodore Ralli《Veiled Woman》
* PowerBook 指的是一款九〇年代流行使用的筆記型電腦,為書中主角寫作和通訊的工具。此書寫於 200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