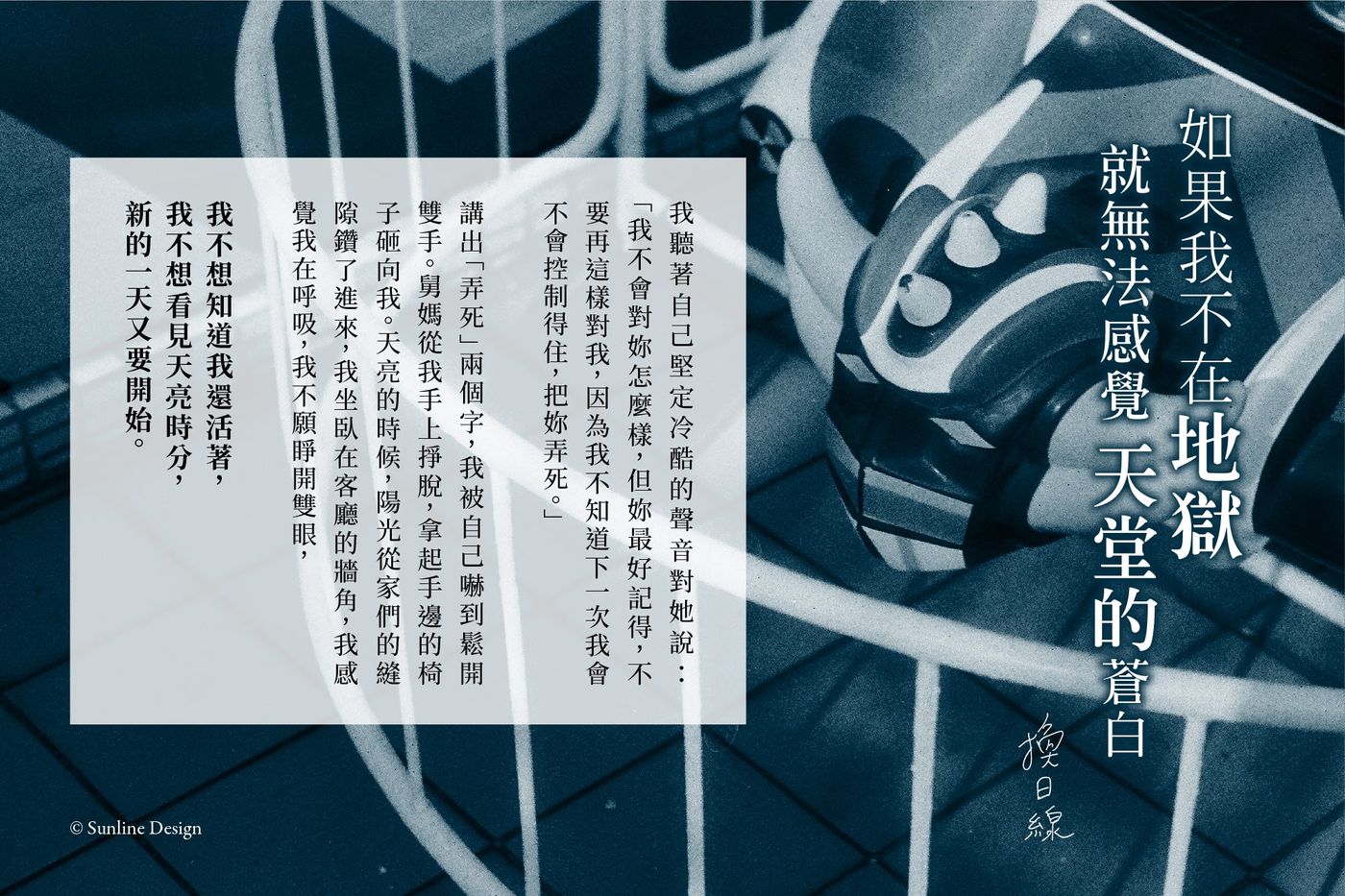設計/高澄天
(本文入選<Youth show>,發表於幼獅雜誌2019六月號)
疑夢書 ∷ 祝福貼(李洛克、王離、李健睿)
疑夢書 ∷ 姊姊在中陰:評高澄天<疑夢書>(盧郁佳專文評論)
疑夢書 ∷ 相互指涉的文本、文字本身的可能(後記,兼回覆盧郁佳評論)
天,你活著的時候姊始終想不明白,你是個男孩,為甚麼偏要去喜歡另一個男孩呢?姊絕不是反對,只是不願看你一路這麼痛苦壓抑,到最後粉碎自己。現在姊似乎懂了,你就跟《像霧像雨又像風》裡邊那個杜心雨一樣,受了太重的傷,只得把自己關在一個花園兒裡,握著手上的筆對著同樣景物刷刷刷畫到死去。你的心思比誰都要清澈、都要孱弱,也許任何一個骨頭硬的修錶匠或著大和尚闖進來,就能輕易把你帶離那樣的自傷之境。
不是你非得跟著誰走,而是誰先朝著你的光走。
還記得你在醫院裡的模樣,因為不吃飯,所以瘦成一片人乾、因為曬不到太陽因為被「關」,憔悴而且蒼白。媽說你瘋了,醫生也這麼說,可是姊清清楚楚地知道,是這個世界虧待你,是你被那個男人傷害,所以失控,才不得不吃藥住院。姊不知道你的躁鬱症要怎麼治,姊跟媽吵,吵到聲淚俱下,姊哭喊說你沒有病、你好好的,可是媽不信,媽說你只要對她表現出一丁點的不耐與敵意,就是「發病」;因為從小到大,你一直那麼溫柔、那樣順從。媽說:「你不懂,小天的個性不可能說出這種話!」媽說得好像她十二萬分了解你,好像你永遠不會長大、人永遠不會變。而現在,你確實再也不會長大了;因為幫不了被媽徹底否定、被精神病院折磨的你,因為你頭也不回決絕地離開這個還有姊信你的世界,我經常感到痛苦。
可是天,不要怪媽好嗎?沒錯,是她親手把你送進那間可怕的醫院;是她主動配合那間可怕醫院的爛醫生關你,一個月、三個月、將近五個月,是她說:「沒有醫生的許可,休想踏出醫院半步!」;是她在得知醫生終於要放你走的時候,寧可讓你多住幾天,也不願早點接你出來。她說她要想辦法治好你,可是她不斷傷害你,要你毀棄學業、人際、愛情,是她說健康第一,你在家當個三十歲的媽寶勝過去追求自己的人生志業和另一半,是她,說你鍾情的寫作無益、文學無益。是她用她偉大的母性來包裹你的生命⋯⋯記得姊跟你聊過嗎?姊是在離開她的「關愛」後人生才越來越順遂的,希望有一天你也可以靠自己的力量離開她,只是,我萬萬也沒想到,再也不會有那一天了。但是我們都別怪媽好嗎?她也不過是用她懂得的方式來愛我們,即便在千萬種愛的形式中,她選擇的那種是如此銳利。
姊知道你燒得太久,焚毀整座花園全成了灰,卻等不到一個嘻皮笑臉的陳子坤,他多好,他要討你開心只要對著你笑,可我連護著你這麼簡單的事,都辦不到。
天,你的愛那樣純粹、熾烈,有時幾乎使人感到害怕。大學那幾年,你和一個不斷劈腿的男人同居,姊想不透你為什麼要選擇不斷原諒?難道因為是初戀、難道這個世界上只剩他一個同志?你明明生得這麼美,性格溫柔、聰明幽默,你最大最大的缺點是太過自負,也許就是這點害了你,因為自負於自己的愛是最珍貴的,所以相信給了出去,得到的人必然會寶愛且珍視之。你說你一開始就知道這個男人是百人斬、性愛經驗遠勝戀愛經驗;你一開始就知道這個男人過去沒有定下來的習慣。你知道你都知道,可是你卻做出這樣愚笨的選擇,就因為他先闖進你的花園?天,如果每個人的愛情都有幸與不幸,或許你的愛情就是不幸的那一種。我後來聽一個教會的姊妹說,這是「家族咒詛」,一如母親,你承接了這樣的咒詛,要被一個男人傷了又傷。
愛情有時像賭局,天,你何必一進場就梭哈呢?你從來不是籌碼最少的那一類人。
天,昨天晚上你到夢裡跟姊說那些,你說:「姊,我去了金城武家裡,我看著他洗澡看他刮鬍子,還看到他跟另一個人⋯⋯」我敲了敲你額頭,你怎麼這麼壞!但看你開心得一張臉紅暈暈的,那麼湛亮的笑容,從你離開這個世界以後我就再也沒從其他人身上看見過了。
這個世界忙碌,而且無情,所有人都為了被其他人記得而努力著。可是天,你被忘記了,因為這個文明的社會容不下你的不正常。你的眼睛從來就是夜空最閃亮的星、你的笑聲一直都讓圍繞著你的人們感到歡愉;可是,自從「躁鬱症」三個字符咒般緊黏在你額頭,所有人都轉身離開了。他們去追逐曾經跟你徹夜長談的夢想,他們去愛,他們工作生活、結婚生子,你就此在他們的生命裡永遠淡出,成為臉書上一個被設定成「點頭之交」的帳號。姊知道,你在醫院寂寞非常,你是一個如此愛美的人,如何接受長期住院那個衰頹而病弱的自己呢?你如此愛美,如何能開心地和其他衰頹而病弱的病人相處呢?把一個愛美愛笑的你關進這樣的地方,等同一場慢性謀殺,而他們成功了,媽跟那群爛醫生終於送走你了。天,我們從小一起拉著手長大,姊的童年因為你而豐富多彩,可是姊的未來卻永遠都沒有你的參與了,我後悔、我恨,恨自己沒有足夠的力量拉住你,恨自己沒有果斷且堅決的阻止媽那樣無情地關你,真的恨。
但姊知道你不喜歡人家說「恨」,你是《曼哈頓奇緣》裡那個從童話裡穿越到現實的,每天早上會用你美妙的歌聲,和鳥兒、松鼠、各種可愛動物一起迎接早晨的白雪王子,你的字彙裡最多最多只有do not like,沒有hate。
記得前幾次的夢裡你帶姊去玩嗎?你在空中飛著,一會兒東一會兒西的,看得姊眼都花了,你問姊想不想飛,我說好,然後你把一條繩子纏在姊腰上,突然這綠丘以你為中心擴散,化成一座沒有邊際的沙漠。你要姊跟著你跑,我跑,你扯著我腰上那條線,一開始我覺得四周滾燙,過了不久卻突然清涼了起來,我真飛上天了!你在地上邊跑邊對著姊笑;我越飛越高,比雲還高,你愈跑愈快,我漸漸看不清你的臉了,嚇得,急著吆喝著:「別再飛了,太高了,快放我下來!」可是你聽不見。
線斷了。
一如那次姊不斷撥電話給你,是要告訴你,媽準備上台北中斷你的研究生生活把你送回那間爛醫院,姊勸阻無效、反對無效。你從來不教姊失望,大學因為躁鬱症沒有念完,卻又憑自己的力量以同等學力自修考上研究所,多麼勤奮、多麼聰明。你終於靠自己的力量告別高雄,告別這個潛意識裡已經把你當廢人的媽,告別你不幸的大學生活,告別所有離開你的人去接近另一群新的人。還記得你雀躍地在電話裡跟姊說這說那,說三峽校區如何大、建築如何新,說社會所的老師同學如何溫柔待你,說你同宿舍的越南僑生寶國如何友善,對,那就是你該過的生活啊!你這樣一個有愛、可愛又渴愛,而且從不吝於付出愛的男孩,就應該被愛環繞啊!可是你切斷電話,後來姊才知道,那時三峽N醫院主任醫師開給你的藥實際上對你是沒有效果的,你切斷電話是因為你已進入輕躁,你以為姊要來干涉你,說你「有病」。天,姊從來就是所有人裡最相信你的那一個,勝過相信媽相信醫生、相信鬼神。姊也是永遠不會背叛你的那一個,永遠。
線斷了以後我卻沒有下墜,我一直向上升一直升,離開這顆蔚藍的星球朝那球火焰接近,我很害怕,那是太陽啊!幾千幾萬度的高溫和滾燙岩漿,我會死的,我全身都在發汗,怕你又去了金城武的家不來理我了。幸好你追了上來,笑著對我說:「姊,他們騙人的,太陽一點都不熱,你躺進去試試。」
姊信你。
從小,你說什麼姊都信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