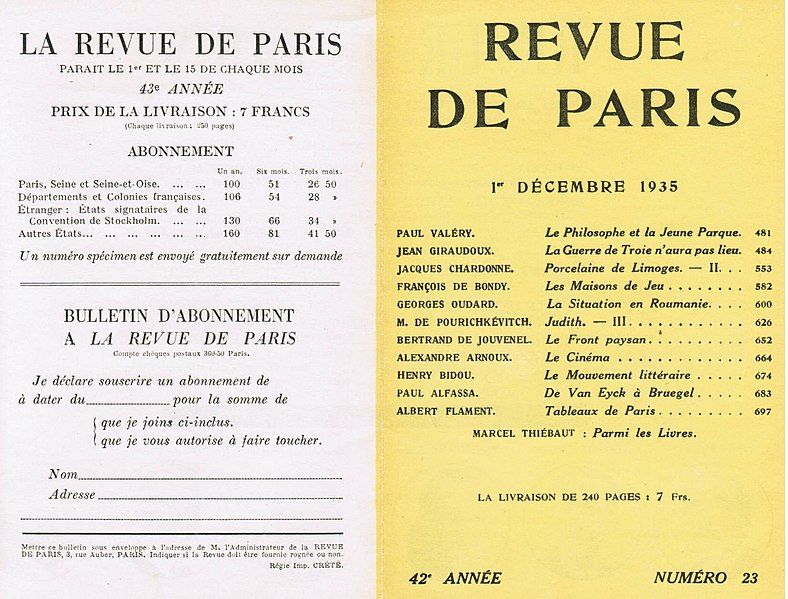Paris,從此像一座危樓02
閱讀時間約 10 分鐘
她在心中盤算著打開車箱拽著背包奔跑並遠離他到可能性有多大。他會不會鎖上了車箱、車箱是自動上鎖嗎、我能跑出幾條街、我要往哪個方向跑、我現在拿出手機查詢來得及嗎。
太多念頭在跑馬,她悲涼又狼狽的佇立原地,她終究是沒能離開。她怕沒徹底逃離就算了,要是激怒他,她該如何是好。
望著他緩緩走近,心一點一點下沉,她認命,又得提出十二萬分精神應對。
「我們現在要去哪?」
「去⋯⋯(似乎是個公園)。」
「去那裡幹麼?」
「那裡安靜啊,妳去過了嗎?」
「可能有喔,我有點忘記名字。」她真想抽自己的嘴,這該死的老實。
她怎麼就不直接說我去過了。
她就該指引他讓他帶她人多點的地方。她好想哭,好想打自己一頓。
卻還要若無其事談笑風生。
一路忐忑,疾行的單車終於在一座巨大公園中間停下,眼光所及只有兩三對情侶老夫婦走過,且越走越遠,她莫名感覺腿軟。
他倒了小杯酒給她,在他殷切目光下,她不得已抿了一口,只稍微沾上嘴唇,只有一個苦字可以終結,她很真誠表現出不喜歡,將大半杯遞了回去,他不接她便放在石階上。
又絮絮叨叨隨意說了些話,他看來是沒有醉,但她真害怕所謂喝酒壯膽,不知道該低估或高估歐洲人的酒量和酒品。
他伸手拉了她的臂膀,他斜斜倚靠著噴泉矮圍,半坐姿態,將她拉到他鬆開的雙腿間的空間,這種她看來親暱的接觸,她感到不適,下意識一縮,沒完全躲開,她憋著氣隱忍。深怕被看穿,被看穿她其實很保守、有接觸潔癖。
他低著聲音。
「妳有男朋友嗎?」
心裡一涼,她沒有遲疑,故作鎮定,儘管在幾天前她才親自提了分手,此刻情況,她卻覺得她該說有。她有男朋友。
「妳知道嗎?我說給妳聽,妳相信上帝嗎?」
⋯⋯不,她不信,她沒有信仰。但她點頭。
「對,妳相信上帝,妳也相信我對不對?不然不會讓我帶著妳參觀。」
⋯⋯沒有,她只是盛情難卻,她一點都不想。
「妳在德國念書,我在巴黎,我們能遇見,很難得對不對?所以該相信和感謝上帝,在這邊,在這邊的發生是可以完全跟妳過去不相干的。」
然後,然後,他抬手觸上她的臉龐,撩過她的瀏海,說她喜歡亞洲人蓄著瀏海的樣子,順著拂過她的眼睛,點了她的鼻尖,她多努力才能忍住力氣打開他、多努力才能忍住所有情緒。
整個心都在顫抖,即便她看起來如常,她自覺如常,沒有發抖。
「在這裡是跟妳在、妳說妳家在哪?哦,台灣,這裡的事跟台灣是分開的⋯⋯」
她的腦袋鬧哄哄的,再也想不起他究竟還說了什麼噁心人的話,滿腦子滿記憶都是,他說這裡發生的事與台灣她的現況無關。
這個人到底胡說八道什麼⋯⋯。
她不傻,她知道他意有所指。
她沒等到自己找回聲音反駁,卻是等到他偏了頭靠近,親了她。
親了她。
她覺得整個世界都在崩潰。
碎掉,一點一點,她的信念、她的驕傲、她的價值觀、她的自尊心。
察覺到她真實的害怕,他拉住她的手,已經凍得涼,他沒勸成功她喝酒暖身,低啞著嗓音繼續說:「妳還不相信對不對?妳聽我說,真的是這樣的,妳是相信上帝相信我的,我不會傷害妳,所以妳才跟我來不是嗎?」
⋯⋯不是,她是逃不開,她真的不知道怎麼逃開。
好髒,她好髒,這個世界又黑又髒。
他又靠了過來,撲鼻的酒氣,倒像是一氧化碳,她感到窒息,感到暈眩,感到暗無天日的難過與悲憤。
巴黎跟台灣是分開的,妳男朋友不會知道,妳沒有對不起他。他說。
說完,他又親上來。她像是被按下靜止,不動,他似乎不滿意,繼續試探著她的害怕和疑慮。屬於這裡的隨便文化,她的這份潔癖不會有人理解,他不會明白,他只想著一親芳澤,以為她跟他有一樣的情慾。
推搡了許久,他終於願意帶她離開這個僻地,往市街人嘈區域接近。
「我們去我朋友那邊坐坐,妳很冷吧?那裡是小餐廳,可以暖暖。」
「⋯⋯不用,我想回去了,好晚了⋯⋯」
「還不晚,再陪我吧,我們見面這麼短,去吧,那裡溫暖。」
她不再說話,有點氣惱,也不再帶著刻意開朗的笑,維持著不會激怒不會引起他注意的禮貌,她好像能聽見自己的心跳、聽見自己的破碎。她想不出任何辦法,或許她就是卡在這個情境,越掙扎越陷落的泥淖。
坐在放送著暖氣的餐館,他與朋友噓寒問暖幾句,她絕望的發現她的手機、她的兩台行動電源,都瀕臨沒電,已經不是喪氣可以形容,湧起更深一層的害怕,她不知道這裡是哪、不知道旅館在哪、甚至不記得旅館名稱,她不知道怎麼回去,或者,她已經回不去了。一切再也跟過去不一樣了。
她連忙開了定位,為著毫不留情掉的電感到焦急,壓抑住眼底的淚意,她擔心楚楚可憐的模樣更引人遐想。
還要待多久⋯⋯還要多久可以結束⋯⋯
她不斷不斷默數著時光,甚至祈禱末日快來,她好怕還沒分開就電量耗盡,她會不知道怎麼回到旅館……對,她得先記得旅館名稱,還可以搭計程車,可計程車的危險性又讓她遲疑。
她怎麼就把自己逼近這樣的窘迫。
唇碰著杯緣,假意慢吞吞喝著酒,她盡量不著痕跡的要告訴他,她該走了、她累了,她的眼光逡巡,卻找不到值得信任能伸出援手的路人。值得信任,還有值得信任的嗎。
她擋不住心裡掀起的漫天塵埃。
終於等到他說要離開,她多費力才按捺住激動,連一顆行動電源浩劫、另一顆岌岌可危,都不能淹沒她的喜悅。
他一樣讓她上車,她不再乖順的將背包放進車箱,不論他如何巧辯。
他說要去停車,路途又出發往人跡罕罕的方向,她鬆了些許的神經再次繃緊,偏頭望著掠眼的景,車咚咚顛簸,沿著下波行進一片偌大的地下停車場,那種無法逃脫的末世感毫無預期湧上來。
她眼底一片的死灰。
停好車卻得不到他說下車的應允。
「我們在這裡坐一下吧,我們遇見這麼難得,我還不想分開。」
……不,她想分開,想要斷得乾乾淨淨,想要所有發生都刪除。
周遭一片可怕的寂靜,喊破喉嚨也得不到救急的空蕩,她只有自己,只有自己一個可以依靠,但她別無辦法。
她不得不面對與意識到自己多麼弱小。
他播放的音樂都是左耳進右耳出,她只拼命計算該如何影響與改變現在的處境,她要強硬或是柔弱,她能往哪裡逃。
他拉了她貼近,她憋著氣,深怕呼吸與眼淚同頻率,他身上不懷好意的氣息她不敢正視,生理逃不開,便希望心裡能逃避。
說服自己人性依舊是善。
耳邊嗡嗡作響,歌曲不像歌曲,他的低語不像人話,反覆催眠似的要她妥協什麼、接受什麼,甚至丟棄什麼。
他的手還在她手背上,他的指尖才拂過他表白過的瀏海,他輕盈的觸碰都讓她反胃。他又不知道幾次的親過她的臉她的唇,她深刻體會到生無可戀,她彷彿能讀出他眼底的滿足或喜愛,她藏住自嘲與恐懼。
「妳要不要主動親我?都是我,妳也親我。」
她一愣。眼眶與腦袋都衝上熱氣,她多想哭,她多想愚笨的腦袋趕快想出救贖的方法,四肢卻冰冷無比,屍體一般的僵硬。
「不……我不行,我會怕。」
他不相信。他不相信有男朋友的她怎麼不會親吻不會耳鬢廝磨。
但是,這樣的親密不是要跟喜歡的人發生嗎?
她情事冷感,與前任相處也從不主動或需要,有時候前任的靠近她也會退卻會承接不了,她曾經自責是不是自己不夠合格不夠上心。
此刻感覺更強烈,他的索求像是一把刀,將她的防備和堅強狠狠切開,她的脆弱被攤開,她無所遁逃,她縮起身子,退不開的惶恐讓她近乎要語無倫次,只能一遍又一遍用「我很害怕」來回應他一遍又一遍的探求。
他終於流露不滿,不耐藏著語氣裡,她感情經驗不多,但也是讀過許多小說,欲求不滿的暴躁閃現在她腦海,害怕呼之欲出。
她只能小心翼翼靠近,不帶絲毫情感只有速戰速決的念頭,冷硬的唇貼上他的,蜻蜓點水後即刻退開,他不滿。
她的聲音快要染上哭腔,「我不會……我真的不會,我怕……」
「怎麼不會,妳試試,妳再試試。」他開始移動他的下體。
年紀不宜的想像一定不是庸人自擾。她想這麼死了算了。
「好晚了,我想回去了,真的,拜託……」
「我不要……我會怕,拜託,我要回家了。」
她只是魁儡似的重述,她甚至想不起來她有沒有膽敢說她不喜歡。
磨了多久呢。一分鐘、兩分鐘、五分鐘,或是十分鐘,她感覺自己在枯萎老去,她感覺自己的裂痕深刻了無數分。
她也許再也好不起來。
他頹然放棄,像是好久之前的她,自暴自棄的失了掙扎,他帶著焦躁和無語,在失控邊緣放棄勉強。
坐在原地半晌,戲笑著調侃她,惡意模仿她剛剛害怕的拒絕,然而,她已經連生氣的力氣都沒有了。她內心空洞透著風。
離開記憶混亂的地方,細節在離開起模糊糊起來,她很努力要忘記。
進了電梯,他從後方要貼上她,她倏地扭開退左,眼角餘光瞥見他單手解開皮帶,她立刻躲開視線,她以為她已經麻木了,才知道她已經墜入害怕的深淵,引起懼怕的閥值低極。像個驚弓之鳥。
她曾經差點目睹前任自慰,她自然知道接下來能發生什麼。她想吐。
他跟她說話,她再也不辨清他說什麼、也不探究他真實意義,她只是死死盯著別處,隔絕不了耳邊的摩擦聲和他低啞的呻吟,她覺得電梯上升得好慢,她想拽著他直接下地獄。
她只說了幾句害怕,便開始不知所措。她有模糊的體會,是不是她的聲音會令他動情激烈,他製造的聲音讓他心顫。
終於終於,暈呼呼回到路面,回到有他者的世界。她才感受到自己真實存在的呼吸,才因為風過攏起一些理智。
路上繞去買了珍珠奶茶,她藉此借來他的行動電源充電,用生命在請求可以讓電量撐到她查好公車、撐到她抵達旅館。
她不敢讓他知道他住的旅館名稱,只說了她要搭哪輛公車。分別之際,他硬是要加了他帳號,硬是將另一瓶未拆封的酒給她。
逃離他本人,卻沒能逃開他的訊息,依舊甜言蜜語說著想念,她衝進浴室裡強迫症似的搓揉著嘴唇,用卸妝油、用洗面乳,再用沐浴乳,直到紅腫、直到有破皮的感覺,她卻刷不掉再回憶裡的污漬。
她敲打著腦門,悶聲如她心沉深淵的聲響。
她甚至不敢也不能放聲大哭,因為她住的是混宿房間,外面另一張雙床上已經有一位外國男生呼呼大睡。是的,男生。
她彷彿攥著最後的一根神經才能捆住理智,才能好好面對現實。
筋疲力竭,她呆呆坐在桌前,心中彷彿有一頭狠戾怪獸,想要抓起眼前的玻璃酒瓶狠狠砸碎,她閉上眼睛,彷彿能看見滿眼汩汩血液,夾雜著拚不回的碎片。四肢百骸忽然刺刺痛起。
衝上電的手機開始刷進消息,將她扯回現實。
沉默良久。她封鎖了初加入的帳號,試著刪除不堪的照片和牽扯,她以為只要不說、不想、不在人際社群裡留下痕跡,就可以裝作什麼也沒有發生。
於是,她只撿選了好的部分訴說:陌生路人送的酒,還載我觀光,但把我越載越遠啊。
那些陰暗她留在背後。
只要不說,就可以當作從未發生過。
只要不說,就可以不用面對別人憐憫或責備或震驚的眼光,不論是什麼,她都無法承受,她已經從頭到尾將自己唾棄一遍又一遍。
為什麼會看到廣告
留言0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