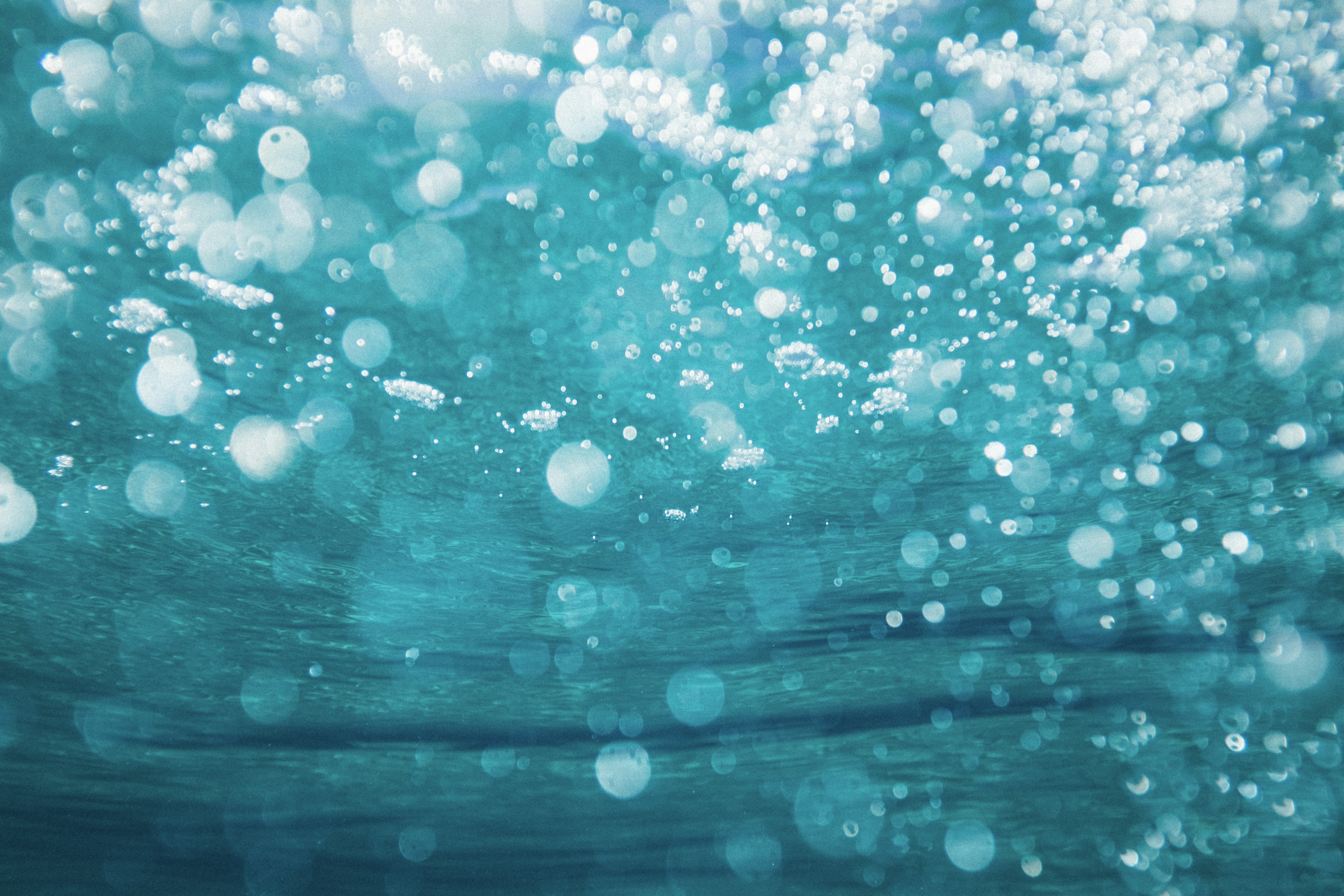原創短篇|紅的夢(五)
「我總是能看見她,在每個角落,用視線掐緊我脖子。」
即將熟爛的果實馥郁,載起女子鼻頭沁出的汗珠,向下,撥過肌膚的細絨探勘,甜蜜的滋味誘出密林的破口。
秘果的藩籬抵著紅淺薄如露又滾燙如電的指頭;軟糯的指尖甫一刺入,洞壁脫出鱗片,墜入蛋白石的流光中,甘甜霎時流竄於腹地,瞧著窄小的甬道向上,再向上,漫入身體的全部角落。
雙枕的夾縫擠壓著紅,一雙鳳眼鑲嵌在她素白的臉容上;這吊起的眼梢像極了沼先生吹奏的裝飾音,作為一首樂曲的掛件,華美得不可方物。燥熱的室溫浸染著她的呼吸,狂亂的心跳早已超出樂器的節拍速度,這時被褥竟纏上她的腰部,將她牢牢捆在墨色的大床;淌下的濕潤流入花海,身下的被單一塊深一塊淺,一如一腳深一腳淺地踏過果園,熟爛的果實一個全一個缺,一個生一個死。
紅將額抵在冰涼的牆面,好一陣止不住地輕顫。
澆過汗水的肌膚幾乎馥郁出勝過秘果的的香甜,她舔動破裂的雙唇,嚐下這口熟爛的果實。
唇齒的甘甜還未散去,隔壁的樂曲卻開始破音,斷裂的音符刺進不堪一擊的壁癌,粉白的牆面霎時爬滿不規則的裂紋,張牙舞爪地吞噬陰濕的房間;這時,母親森隨著坍塌的碎屑進入紅的視線,直勾勾地審視她身上的纏繞。
紅這才清醒,原來刺進壁癌的不是斷裂的音符,而是母親的叫聲;牆面的壁癌不是陰濕的紋路,而是堆積在自己心頭的癌。
再醒來,陳舊的毛毯早不翼而飛,取而代之是一堵冰冷的牆。她將滾燙的臉貼上,房子徹骨的冰冷滲入皮膚,身體彷彿住了個爐灶,一股熱氣直沖她的腦袋。
頭昏腦脹的,早忘了是如何回家。
白烏鴉再也沒有出現,窗上的足跡也隨時間模糊了過去。隔著蒙塵的玻璃,紅開始懷疑自己是否真的見過白烏鴉。
只是熱水壺中的涼水眼看著要到底了,那整天披在身上的毛毯某天起便不見了蹤影,母親的氣味也因此淡了許多。時間的確在流逝,彷彿一切也將走到盡頭。趁著入夏,紅想收起屋子厚重的織物,拿出幾件乾淨、得體的衣服,再敲響沼先生家的門,走進去,學一學如何煮湯、嚐一嚐紅蘿蔔的味道,她天真地計算著陰霾散去的時間。
當木製的衣櫥打開,細碎的飛灰漂了出來,很是浪漫地,像母親為自己製造的重逢驚喜,那一股烙印在她腦海中的味道又回來了。
紅顫顫巍巍地掀起一件舊式棉大衣,裡面還夾著一根森的頭髮。飛灰讓她禁不住地鼻酸,眼眶酸酸軟軟睜不大,只瞥見不翼而飛的毛毯此刻正蓋在眼前的女人身上,她捲縮在櫃門後,垂著頭、氣若游絲。
紅輕喊了一聲「媽」。
女子還是垂著頭,海藻般的長髮遮蓋了大半張臉,凹陷的雙眼似幽深的井口,深褐色的痣沿著顴骨生長,引導著人看向她可怖的眼睛。
紅再喊了聲「媽」。女子依舊沒有動作,只是胸口微微起伏,那股殘留的氣支撐起這陋室的壁紙、白水、飛灰......一切活了起來。
夢醒了嗎?紅想起母親曾與自己一同觀賞的《歌劇魅影》中的第一個場景,吊燈拉起,死去的一切復生,使人再走一次痛苦的路。
「你活不久了,為什麼要回來呢?」紅伸手穿過兩人之間飛揚的灰塵,停在母親的頭上,觸手便是她粗糙的髮質。「我見到沼先生了。雖然他不是你情人,但想必你也喜歡他吧?」手繼續向下定在她的顴骨,輕輕撫過那些痣。「可是能讓我擁有一樣屬於自己的東西嗎?媽。」紅的手伸向耳朵的位置,卻徑直地卡進森茂密的髮絲中;掌心沒有如期蓋上軟骨,髮鬢與臉部之間涇渭分明,沒有耳朵。
「你不是想聽人喊你一聲母親嗎?可你怎麼沒有耳朵......」
紅的掌心一片冰涼,眼前的人似是抬起了頭,兩個碩大的井口不知藏起多少秘密,只見藤蔓刺破幽暗的洞穴爬了出來,與滿頭藻髮纏繞一起,往碧綠的壁紙爬去;那張熟悉的臉龐被扯開,扭曲的五官傳來尖銳的聲音,眼眶持續被撐開直至母親森全然不見。
銳利的聲音刮損她的耳膜,臉頰僅是一片殷紅的溼潤,可血腥的氣味並沒有如期而至,取而代之的是木頭腐朽的味道。整個空間都被刺穿,坍塌就在一瞬間。
房子吐出了最後一口氣,牆壁皺巴巴地軟了下來,隨後她的步履也跟著輕盈了起來,這感覺讓她想起某天沼先生練習的樂曲;那些直線行走的音符鋒利又斷裂地壓迫在兩人所處的空間,沼先生繃緊身上的一切,在樂曲的懸崖搖搖欲墜。
他用瀕死的狀態演奏,縱身一躍之際切斷聲音,宛如輕盈的氣球飄盪在寂寂的空間中。
母女的家十分簡潔,柔軟的裝飾性布料總是比堅挺的傢俱來得多,一張單人沙發椅、一張床、一張合成木桌、一塊落地鏡、一個三門衣櫃、一個擺放布料的層架......差不多就是所有。
儘管沒有的東西很多,鮮少與外人接觸的紅不善比較,多與少也不曾立足在她心頭,但撇除數量,她卻知道該如何捕捉森的喜好;就像被折疊整齊的織品永遠不及藏在衣櫃深處的一塊舊布,自然,上頭的一塊淡紅印記也勝過萬千調色留下的印象。
森剛離開時,紅躺在一覽無遺的空間中,看著母親所佈置的一切,屋子的灰塵似乎多了許多,一切看起來都灰濛濛的。半掩的櫃門吸引了她的注意力,那堆遠看依舊整齊的衣物,近看卻發現它們壓著一團捲起的舊布。紅知道是它了,那塊陪著母親進出精神病院卻最終留下的披肩。
母親總念叨著一個男人,一個在這張披肩下與她做愛的男人。
甫一打開,森的氣味隨著棉絮蕩起,逆著光,輕柔的身姿落了下來,沾在鏡子上,落在鼻頭上;紅彷彿嗅到母親黏膩的汗味、瞥見她折疊衣物時低垂的眼眸。
女兒拉起毛毯整張蓋了起來;閉上眼恍恍惚惚睡去的她,正感覺靈魂漸漸離開肉體。
在這間充滿森意象的空間中,不再有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