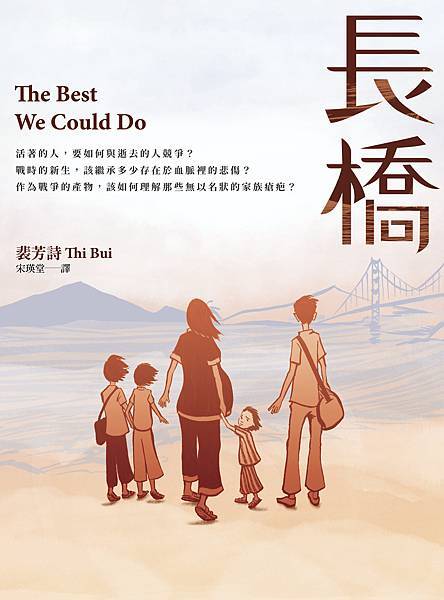文/謝鑫佑
如果在當代,有什麼文學作品能讓人讀後察覺自己的生命被改變了的,恐怕不在少數;反之,看完後,覺得自己改變了作品裡頭的什麼的,卻恐怕只有《克雷的橋》。
2005年以暢銷小說《偷書賊》受到國際矚目的澳洲小說家,馬格斯・朱薩克(Markus Zueak),醞釀13年後的作品《克雷的橋》,出版首刷便突破50萬本,並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榜,受到國際文壇與大量讀者的好評。相較《偷書賊》裡的女孩在戰亂期間,透過閱讀與文字力量,度過人生黑暗低谷的同情與憐憫,《克雷的橋》卻在看似日常平凡之中,推展仿若《百年孤寂》的家族光譜,以更有力量卻不一定溫暖的「橋」,講述一段生命歷程的爬梳與整理。雖然作者受訪時曾說,「《克雷的橋》不一定要比《偷書賊》好,但它必須很不一樣」,以上市後全球的熱烈反應來看,《克雷的橋》不僅不一樣,而且更好。
《克雷的橋》講述鄧巴家五兄弟在母親病亡、父親離家出走的情況下,在這個「風吹即倒的悲慘一家」自生自滅的故事,透過橋的修建,讓家或家庭變得可被理解、被接納、被原諒、被包容,很多原本可能一碰即碎的生命以及關係,能被看見並微笑以對。
為了讓這樣的梳理能順利穿越於現實與心靈,馬格斯運用攝影鏡頭般無所不在的亡靈視角對焦一切,包括巨大的歷史動盪,或細微的時間之流,或深刻延展的關係,或叨叨絮絮的日常,深淺景深,俯視或微觀希臘神話與小鎮的一朵雞蛋花。當博大與細瑣交疊之刻,家族關係與生命鑲嵌便得以獲得救贖。
1981年出版至今仍備受討論的多重人格真人真事傳記式小說《24個比利》中,作者丹尼爾・凱斯(Daniel Keyes)描述「老師」這個人格成為其餘23個人格的「橋」,只是這個橋與克雷的橋不同,它不修補不整理;但同時,這個橋與克雷的橋相似,也通向或離開某處。鄧巴家的五兄弟,馬修、羅里、亨利、克雷與湯米,他們不僅是馬格斯筆下的人物,更是馬格斯自己。
1960年代德國心理治療大師伯特・海寧格(Anton Hellinger)開發出家族排列(家族治療),試圖在緊張情緒、衝突,或重要關係中尋找新的面對方式,這樣的治療可以是針對家庭或家族,更可以應用在個人。《克雷的橋》彷彿是一場馬格斯的家族排列,也可能是每位讀者的家族排列,只是探究問題的根源或解決方式,已不再成為唯一的解答,如同克雷最好的朋友凱莉,曾給克雷的一封信中寫道:「他用以創作的材料不只銅、不只大理石、不只油彩,而是他自身⋯⋯以及深藏他心中的一切而我知道——那座橋就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