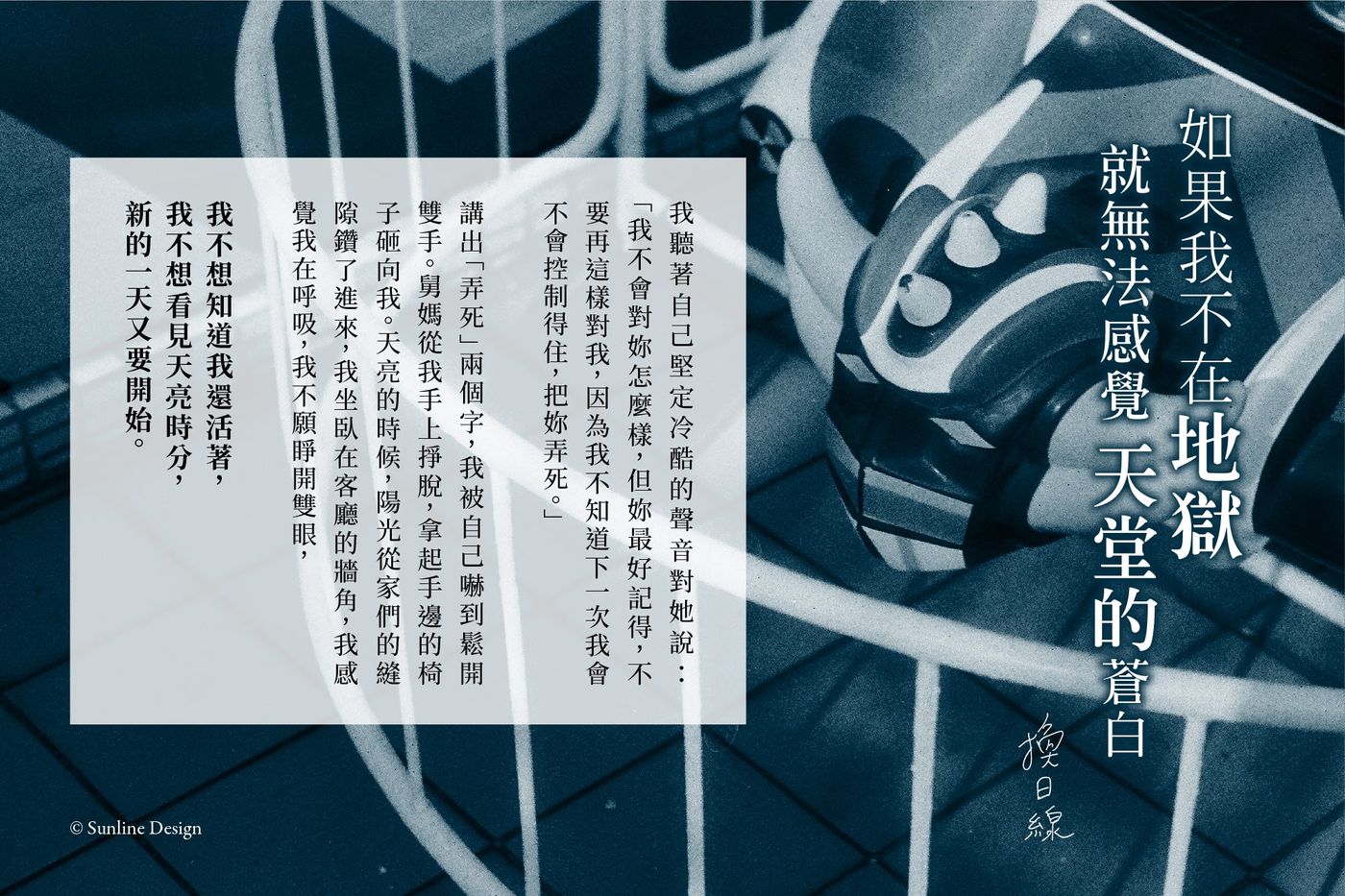這晚間我懶坐電視前,簡讀。
電視開著,正停留母親常看新聞台,我知內容多數不具意義,未曾認真聽過。
「唉,兒子殺父親。」
「嗯?」
我聞見母親小嘆,目光飄去電視螢幕。新聞正播報,看來是父子衝突間,動了手,還見了血……老的進了醫院,小的沒了手指。
「好慘。」我笑笑。
「你笑得出來喔,死小孩。」
「沒有啦,就是覺得怎麼會這樣打起來。」見母親小叨,我趕緊補話。
那新聞上,記者多話,揪著那父親猛問,想來若能揪到兒子,管他斷了手指又如何,照樣是要受訪。這父子吵得激烈,記者問得激烈,也不過是成了電視機前的茶餘飯後。
「嗯……。」連父子都能相殺,要在這塵世間遇得一個好人,更難。
塵世、塵世。我們人以塵世謂之,便是因為凡音太眾、嘈雜錯切,且還烏煙瘴氣;而在如此塵世間,要遇到什麼樣人都是可能,但想遇到好人,更添困難,如此,遇人知心、有心、癡心、交心,哪一個都是珍貴。
「不是人人都能遇到嘉敏,」我喃喃未完,突然思索起來:要有什麼原因,能令護士嘉敏在短短日子內盡心盡力照顧惠君姐的話,想必有其因素。
「過來人。」我沒想多,直覺如此。
是了。她或許是過來人。
我不禁想像,或許嘉敏也曾在某間醫院、某個時間,自己挺著肚子、忍著眼淚,生下孩子。雖說暗自猜想罷,我又感覺好真,否則,她便不是對著惠君姐說「只能好好撐著」如此話語;純然富同情心之人,往往還要想更多辦法予以安慰,但過來人心裡是明白的,有些事情,到了,就只得努力撐過,多餘的什麼話語都是無用。
我想起惠君姐那濛然雙眼。
關於那西昌街上的夢露,她的故事,逐漸的全然浮出。 而夢露的反面,是惠君,是那個從彰化眷村出走了的孩子,也是帶著夢想到了臺北,從此幾乎被夢露吞噬的女人。
「嗯?」我突然地想起,惠君姐久未聯絡的父親。
「難道不想回去嗎?」惠君姐好久不曾回家,平常感覺,是無所牽掛。但說起父親,面色仍有所慟。
我心想起惠君姐父親,便看著父親書房。
這數日間,我有空閒便從臺北搬些東西回家,慢慢收進書房;我瞧著父親留下的那書房,眉間不覺輕敘,自父親離世,我未曾進了那書房內作書寫。
並非自己用慣電腦,更多感覺,卻又彷彿礙於父親,走不進去。那是父親的書房,父親高之於我,博之於我,他留下的書房,還仍然威嚴著,非我等閒之輩能夠進入。
「哦?等閒之輩?」那是我看待自身,所予之評價。
『許逸飛的兒子,知道自己要去哪嗎?』
父親那句話,又掠過我混沌腦袋,如今,我似乎依然不明白自己該往哪去。但父親這句話提醒了我;是啊,我仍對自己視之等閒,或許正因如此,我哪也不曾想去。
「罷了,睡吧。」我自沙發彈起,大步進了房裡,關上燈。大姊見我進了房裡還熄燈,也來。
「喂?九點耶,這麼乖要睡了?」
「嗯,就睏。關門啦。」
「才不要,自己關。」
我瞥見大姊一臉頑笑,一手便抓了一旁娃娃扔去,大姊一把接住,抱著娃娃便往客廳去了。
我一面笑,一面沈沈睡去,做了個夢。
那夢裡,是一處老舊水泥矮房,所有窗杆皆為木造。而其中有三人,是老人、女人、女孩。那女孩活潑,於家中四處作樂,奔來奔去,不時躍起不時藏。而老人與女人雖看來年齡相差甚巨,老人身形巨大,直頂天花,仿若屋柱,並手持籐棍,動也不動,而女人不過家中處處愣走,形同殭屍。
我好奇,上前相詢,卻無人與我相應。只得獨自杵在牆角,瞧著。
突然間,老人持籐棍手緩慢舉起,作勢要打,看來是待女人經過;女孩見此狀,便躲藏電視櫃下,不敢再動。我見女人緩速遊走,竟不知要閃,便上前去阻止,想不到女人力大如牛,不過輕推便將我甩開。
但這力大如牛女人,卻緩慢走去老人跟前;老人見女人來到,便一次次、一次次不斷的揮下籐棍,打她。
日換星移,這屋內,不斷往復如此畫面。老人不動,女人遊走,女兒玩樂,只要女人經過,便遭籐棍擊打,而只要女人遭打,女兒便消失無蹤。我環視屋內,不覺間,竟像是經過數年,而那水泥屋內,不知何時,唯獨剩下老人。
他仍手持藤棍,但已不再動靜;我疑惑,上前觀之,不料輕觸其身,老人竟成敗絮,灰飛煙滅。
「嗯?」醒來,已是早晨。我思索那夢,心裡還懸。
「唉。」那夢中女人,似乎怎麼都只想著受打,而女孩不見了,或許逃了去。
「老人?」思索至此,突然有感。那老人自始自終,不過拿著條棍子,見女人就打;但屋裡無人,便無可動靜,只有呆立,最後也成了風中灰絮。
我笑笑,這是像誰呢。
這日,我於豆花店與美麗姐閒聊,談起惠君姐孩子。
惠君姐孩子,是在三年級時去世。美麗姐說起孩子,總皺起眉頭,先記得避開惠君姐。我明白,先前曾於病房內聽美麗姐不經意提起,那時惠君姐眼光藏於髮絲之間,卻依然洩出幾點濕潤,所以美麗姐犯一次錯,總不想再犯第二次,可得提防自己的不經意。
「我看惠君什麼都跟你說,才跟你說啦。」美麗姐小嘆。
夢露生過了孩子,休息了幾日,那時她已出院,但孩子仍在院中。她沒抱孩子離開,要求多待幾日,院方不想,只是予她惡臉。因由脫不開夢露未婚生子,且除卻未婚,夢露還是一人來到醫院,身旁無人聞問;夢露這錢付的慢,院方深怕要虧,不曉得眼前女子有何從事、又意欲如何?說穿了,是怕夢露將孩子遺棄病院,逃了去。
於是,嘉敏替夢露做了擔保,若她沒有回來帶孩子,那麼便由她來養。夢露對嘉敏很是感激,幾日後,才又回了醫院,抱孩子。
「可是,惠君姐為什麼要慢幾天才抱小孩?」
「他回家去準備,怕整理家裡,顧不到孩子。啊……生意也是要繼續做,」美麗姐頓了一會兒。
「反正生了小孩以後,他就開始……做客人了。錢也比較多啦。」
那幾日,夢露回家,不僅僅為了整頓。
她尋了一間較大的住處,公寓式,另外再租;一方面,她擔心自己生意影響孩子,一方面,又想予孩子一個好的環境,於是便先離了醫院,花上幾天,另覓它處,將那些該搬的搬,該丟的,也全丟了。
惠君姐曾向美麗姐說,那時搬了家,整頓好,她在家裡呆坐了好久。問她做什麼?她說,想名字。
夢露待在家中,那一日,她周圍都是撕下的日曆紙,上面寫滿了許多名字,全都是要取給自己孩子。楊瑞峰?楊貞驊?楊琪軒?還是楊儒行?夢露腦袋閃過許許多多的名字,但總覺得好像哪個都不夠好。她索性起身,繼續擦拭已被擦拭過的傢俱,重複搬整一塵不染的廚房。夢露已經整理了一整天。但她卻不覺得疲倦;四點半了,夕陽斜射,房裡全是金黃。
那金光入了室,便暖黃充盈,夢露感到心神舒和,不自覺走去客廳,望向那縱陽入室的窗框。那時夢露心裡,有答案了。隔日,夢露便到了醫院,抱回了她的孩子——楊和光。
「我後來問惠君為什麼叫楊和光,」美麗姐翻一白眼。「結果他說,那是他爸的名字。」
「啊?惠君姐他爸名字?」
聽美麗姐一說,意外。在我印象裡,自過年時惠君姐有所描述,她的父親待她都不算好,甭說對惠君姐有什麼影響、又令她有什麼懷念。但如此聽來,惠君姐父親卻依然留下了些什麼在惠君姐心裡。
「是什麼呢?」我思索起來,這樣的問題值得玩味兒。
這一道題,免不了又令我疑惑了千絲萬縷,難以透心。我疑惑惠君姐之於她父親情感,實際上,也疑惑自己之於父親情感;說穿了,父親直至離開,似乎都未曾留下些什麼予我,但我卻也想念父親。那些書冊故事中,待兒女溫柔善良的父親們,在我心中,純為一篇篇的神話。
「神話?」想來,諸多神話,沒有什麼是不荒誕。不過也因此有其迷人之處。不過,再迷人,終究是故事,到不了現實中。我似乎多少體會了,人一旦去世,什麼都是停下的,想追的,都沒得追了。
「對啊,」如此一來,惠君姐還有得追……不,該說是或許有得追。說對家裡無牽無掛吧,惠君姐在講父親時,卻是有些神傷;以往,我或許會感覺那是淡然,如今,我卻總有感於惠君姐那絲絲絮絮,藏於那副淡然之下的熱烈。
惠君姐想必是念著父親的。
但臺北數十年,她已不知該如何回去,也不知回去了又要做什麼。那家裡一切,即便是逃開了家時,或許都不曾悉熟過,那麼又為何要回去?如此久來,似乎也沒什麼好想著回去了。但我是明白的,惠君姐如我一般,之於自己父親,都還要懸念著。
「哈,好奇怪。」我一面思索,一面憨笑。
自己到了現在,也仍是不明白如此情感究竟為何。幼時父親待我極為疏離,直至去世都不曾有過太多交集,最多,便是去世前那段日子;但那段日子的父親,已不明白了。如此一來,我的疑問便永遠尋不著答案——或許成了我一輩子的懸念。
而惠君姐年過半百,在我思索,或許也是念家的。在臺北,她的家不過自己一人,在彰化,她則有一個家,一個標準的家,有父親、母親,或許還跟一般家庭那樣,有爭吵、有溫馨;但隨著時間過去,那個家漸漸糊了去,不知不覺間,母親去世,父親也像是消失。如今還有誰在,早已不清楚了。
「惠君姐會想回去嗎?」
「回彰化?」
「嗯。」
美麗姐低頭思索,客人進來,又旋即招呼。她一邊挖豆花,一面招呼客人,動作雖說俐落,看來仍有所思;客人多了,我見美麗姐正忙,便自己去一旁幫忙清洗碗碟,惠君姐則從後面忙完,到了前頭幫忙。
我洗碟盤,又一邊瞧著這店裡,客人來去不斷,生意雖稱不上極佳,卻也不錯。這六、七個月下來,惠君姐、美麗姐熟稔生意之快,像已行之有年,不過,如今生意複雜,收入得扣各式雜支,還得想辦法更熱絡生意;但怎麼說,至少都是實在的。
忙碌一輪,我將全部餐具洗罄,坐回了位置上,惠君姐則與美麗姐店外吞雲吐霧,閒聊。我取過紙筆,小做書寫,是一些店鋪記趣。
小做店鋪記趣,是因為自己也曾在店裡打工;來美麗姐、惠君姐店裡幫忙,總要憶起昔日時光,偶時亦覺得,那段日子的自己竟已離得如此遙遠。老闆與老闆娘對待自己,說來不錯,有時都像極父母,念念叨叨的,怎麼責怪也罷,就是沒真厭倦過自己。
「嘻嘻。」思想起那夫妻二人,是好人。而那十九歲時遇見的好人,如今想來都還令我會心一笑。
「哎唷,在幹嘛。一個人在這邊傻笑。」我自個兒拍拍頭,瞧見惠君姐二人走進來。
「笑得這麼開心?」惠君姐坐上了一旁高椅,拿起指甲剪,開始修指甲。
「沒什麼,想起一些事。」
「稘宥啊,」美麗姐突然喚了我一聲,我轉頭,見她擠眉弄眼,是想要做暗示。
我皺起眉頭,不覺間洩出一絲笑容,美麗姐這臉……好醜啊。美麗姐見我毫無反應,還一臉帶笑,擠眉弄眼更是誇張,我見她五官大有波瀾,又增加許多動作,只得瞪大了眼,要笑不笑,搞到自己也醜極。殊不知,那不過短短數十秒間,我倆你來我往的醜臉全讓惠君姐一旁瞧見。直到我倆停下了那時,才發覺了惠君姐盯著我倆。
「在幹嘛?」惠君姐那一臉嫌惡,像看著兩個神經病。
我瞪大眼又聳聳肩,像對惠君姐說「我不是神經病」,表示無辜,頭上隨即挨了美麗姐一掌。
「惠君啊,要跟你說啦,你要不要回去彰化看看啦?」
「啊?」
「啊?」
聽了這句話,一時間也疑惑、也訝然,我與惠君姐不覺間同時出聲。
那訝異來得突然,我笑容未歇,瞧著美麗姐,那一臉才漸漸平了;原來美麗姐心裡盤算著,是這一回事兒。
「……你們在聊的是這件事?」惠君姐如此一說,我傻笑。我與美麗姐說話,惠君姐當然有感,怎麼會無感。我雖然不曉得美麗姐打此主意,但也靜靜地認了。
「惠君你聽我說啦,」
「等一下,先別說。」
「啊……」美麗姐見惠君姐抬手示意停止,只得靜了下來。
惠君姐並無太大情緒,該說吧,她似乎兇起來了那麼一瞬,但極短時間內又平復了去。我見惠君姐臉龐上有些微無所適從,便看去一旁美麗姐。美麗姐與我兩人對視,這下換她挑眉、聳肩。
相視間,我耳聞打火機打火聲,看了過去,是惠君姐點菸。見她點菸,我倆明白,惠君姐心情不算好受。美麗姐走去,提前了半小時拉起店門,小歇。我倆傻坐店內椅子上,直盯著惠君姐瞧,那支燃菸耗得好慢,盯著,像過去大半輩子。
「呼——」惠君姐噓了好長一口煙,然後又看去美麗姐。
「你知道我想回彰化喔?」
「我知道啊。」
「……想是想,不過那是之前了。我後來是在想,乾脆不回去了吧。去年過年前就有這麼想了。而且,回去我爸也不知道死了沒。」
「惠君啊,你這樣會後悔啦!」
「後悔什麼,」惠君姐小翻白眼。「是要後悔什麼?」
「看不到你爸爸啊。」
「看我爸,」
「看到了,然後咧?」
聽了這句話,美麗姐噘起嘴,沒再說話。我見美麗姐低頭噤聲,又看看惠君姐,她只是繼續修著指甲,沒說什麼話。
「惠君姐,你還是會想回去看看吧?」美麗姐聽我聲音,才又抬起頭來。
惠君姐一邊修著指甲,聽見我說,仍沒有太多動作。
「……想啊。可是又不知道回去要做什麼。」
「就當作回去看看你爸啊!說不定他也會想你啦!」美麗姐憋不來,又說了一句。
「那要是不想呢?」惠君姐停下手邊動作。
「連我媽去世都沒說過的人,而且他還有我的電話……美麗,稘宥……要是我爸不想我咧?」
惠君姐說這話時,也沒看著誰。她只是將指甲剪放著,撐著下巴,看著天花。在距離之下,我凝視惠君姐,那副憂愁模樣,扭轉有致的腰身,搭在櫃台上像個模特;我心裡暗想,惠君姐現在思索的,定是父親的種種關於。
「惠君姐,我覺得該去誒。」說完,惠君姐好沒氣的轉過頭來看著我。
「嗯……大概是因為我爸才過世吧。我覺得很多事情,我都得不到答案了。雖然我很早就知道我爸其實對我不好,從小到大他沒陪我玩過,也沒有陪我聊天過,大概可以說一般爸爸該做的事情都沒有,」
「我的成績也不好,很多事情,我爸從來沒有陪我一起做。所以我的人生,一直都沒有我爸參與。就算是這樣,我也還是有很多疑問,我想知道我爸到底愛不愛我,然後……他到底為什麼容忍我在這個家。我其實有很多問題想知道,」
「不過我爸去世了,他到去世前腦袋都不明不白了,跟我有過幾次對話,我都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了,只知道自己慢了。本來以為他出院以後,慢慢的可以從生活上,多一些接觸……補回一些以前沒有的,所以他住院五年,我都沒什麼去醫院看他,甚至去看他的時候,就只是呆坐半小時,其實什麼也沒做。結果出院不到一年,就突然去世了。現在……想問什麼、弄清楚什麼,也沒辦法了。」
本應是我要勸惠君姐,是不是回彰化去瞧瞧。
但自己如此一說,倏然發覺,原來這些話,我自己都憋了好長一陣。
我不禁尷尬笑笑,眼眶也潤了去;想想,這話我也不是非對誰才可說,主要是覺得沒人聽。這時間,我似乎才終於找到機會說了。
「惠君姐,」我大大吸了口氣。
「我不知道我說的對不對,可是我覺得,你跟我應該是差不多的。所以我覺得美麗姐說得沒錯,你應該回去看看。」語畢,惠君姐仍看著我。我們三人呆了半晌,也是惠君姐碎了這片沈默。
「好啊,就當作去玩玩吧。有沒有都好,」她從椅子上滑了下來,走去廚房。
「至少去過吧。」
美麗姐眼睛直瞪瞪,看著惠君姐走去廚房。
「齁,少年仔,他說好了吶。啊你……還好嗎?」
「沒事啦。美麗姐,啊你到時候要陪惠君姐去吧?」
「陪是要人陪啦,但是齁,當然是你陪啊。」
「啊?」
美麗姐聳肩。
「啊不然豆花店都不用營業喔?」
「嗯……」
「好啦稘宥,你就幫忙一下啦,我們也認識很久了啊。我跟你說啦,你雖然年紀小我們很多,可是我跟惠君真的把你當成好朋友,而且齁,我比較呆啦,有時候說話也是跟他吵吵鬧鬧而已,又不能安慰他什麼。」
「美麗姐,我沒什麼關係啦。我想的不是幫不幫忙,是因為我覺得你跟惠君姐……其實是一家人,尤其我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耶,你應該陪他去。」
「那你要幫我顧豆花店喔?」
美麗姐這一說,著實把我問倒,我確實無法替他們照顧這間店。又說,我與美麗姐都想著,惠君姐此行,是得要有個誰與她一同去的,那麼,閒者如我,難道就不陪著惠君姐去嗎?
「那,我陪惠君姐去好了。」
「對啦、對啦!謝謝稘宥啦!」
我笑笑,便又拿筆寫來。但見惠君姐自後頭端來一鍋湯,擺放桌前。
「先喝湯。」
「煮好了喔?」美麗姐湊過頭來,便朝鍋裡直盯著瞧。
「不知道味道怎麼樣,我很少煮這種。」
「喔?」
我也探頭來看,那湯頭清澈,下方是一推排骨,聞起來好香。惠君姐舀起一匙便是一碗,弄了三碗,各自予了塊排骨。我暫擱紙筆,便取湯來嚐。
「好鮮。」
一般說來,排骨湯煮得好的,顏色都偏白濁,且湯中富含濃郁骨、肉二味,這便令人食指大動。不過要說鮮味,那可是困難,不知得要下好多少工夫。不過惠君姐還是厲害,這一鍋煮來,入了口馥郁乍然,入喉卻餘下一股清甜,再下了肚裡則暖了胃,最後,還有一股濃郁鮮香留在喉頭亂竄,好舒暢。
我一面貪心模樣,差點不管燙的灌下。
「喝慢一點,又不是有人跟你搶。」惠君姐小小叨念,一面自己喝了起來。
我瞧見湯裡排骨,又看看惠君姐喝湯模樣,很是享受。
「對啊。」我笑笑,便改回湯匙來喝。
或許自己多想。但我逐漸有感,惠君姐料理這湯,像料理自己人生一般,到了如今階段,她似乎也自在,懂得享受突來的濤濤浪浪,艱難之中,也還要仔細嚐嚐看,自己這般生命,味道究竟如何。
在我心中,惠君姐與美麗姐,成了另一種我未曾成為之人。她們遇事太多,又像是看淡,如今,卻又重拾了心眼,當真去面對自己人生。
思索至此,我一面喝湯,一邊拾起紙筆,蹭紙書寫。
「馥郁湯鮮染心田,釜中醍醐熬成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