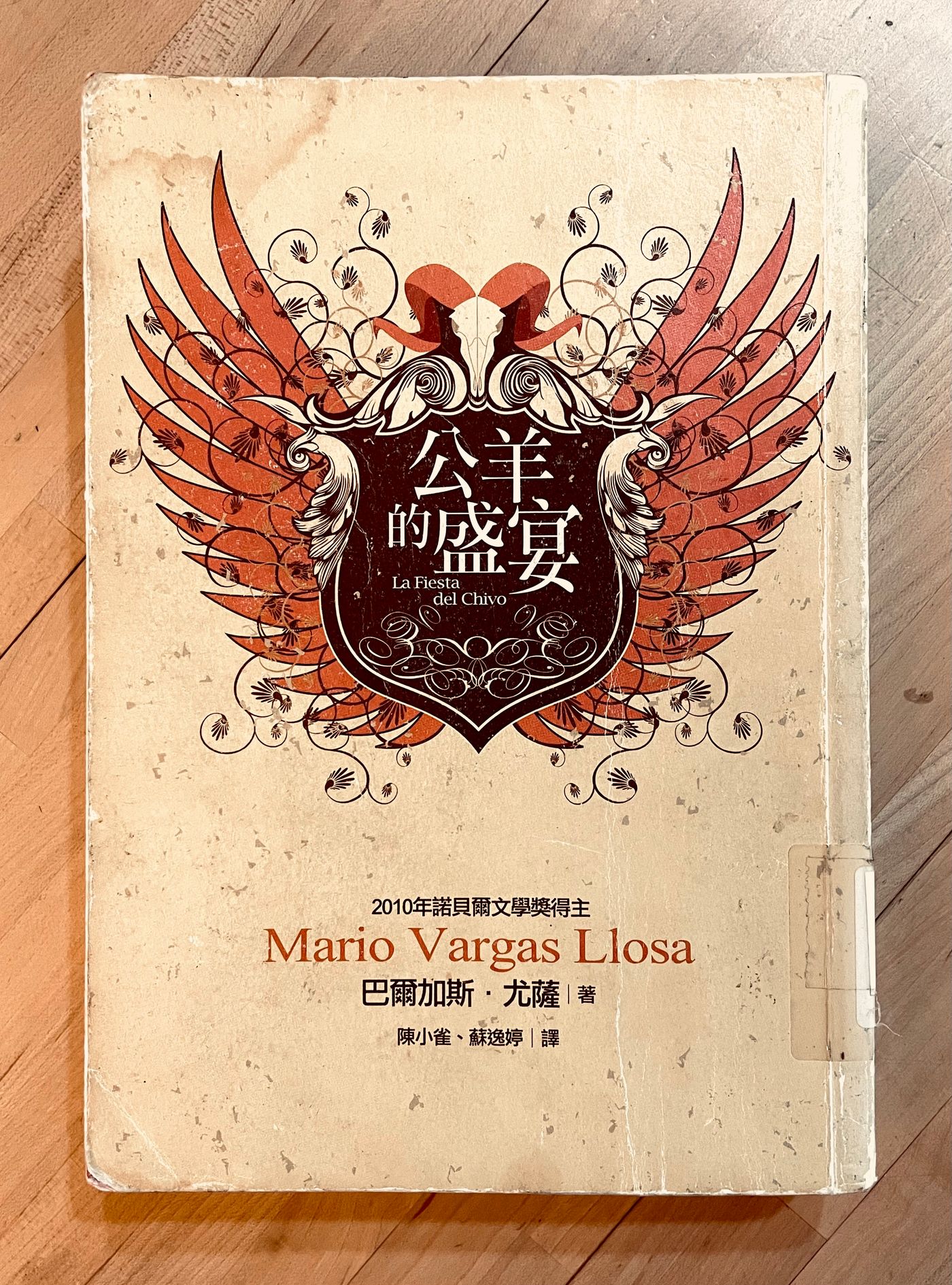作者:朱諾.狄亞茲
繪者:李歐.埃斯皮納索
譯者:何穎怡
「所有關於阿貝拉入獄、家人陸續過世的事,可是世代都必須緘口的祕密,想要重建那段歷史,就像企圖解開斯芬克斯的謎語。探掘所得僅有耳語,如此而已」(《貧民窟宅男的世界末日:奧斯卡.哇塞短暫奇妙的一生》,頁259)。

創傷太悲慟,可以的話,千瘡百孔而死裡逃生的人都只想往前看;把創傷折疊好,收納在心眼不易望見的抽屜裡。記憶是篩網,在有光的時刻裡,篩出的都是甜蜜,例如:比空氣還多的音樂、涼透心的椰子水、腦袋般大的芒果、比彩虹更鮮豔豐富的顏色、如詩的海灘、與浪嬉戲的鯨豚、與毯子一般大的蝙蝠。
這些是《島國的孩子》裡的主角──蘿拉──藉由拼湊他人回憶而得到的、那個她沒有記憶的大島。Leo Espinosa在繪本裡,用了大島那些再繽紛也不奢侈的鮮麗色彩,重新將過去的記憶上色,使之輕盈,易於消化。不過,收在抽屜裡的傷不會過去。「我們的島聽起來好美麗。我們幹嘛離開?」蘿拉問。
「還有其他的事」。創傷未解,那些過去死裡逃生的人想轉過身去,卻時不時被時間纏住,「掐住我的脖子,叫我非說不可」(《貧》,頁28)。這符枯(註一),需要言說的煞化(註二)。
「知道的人也不是很喜歡談他」繪本裡的老米爾先生幽幽地說。曾以《貧民窟宅男的世界末日:奧斯卡.哇塞短暫奇妙的一生》榮獲普立茲獎與美國國家書評人獎作家Junot Díaz,在繪本裡,輕巧地將大島(多明尼加共和國)的獨裁者楚希佑(Rafael Trujillo),轉喻為嚇壞全島人的妖怪。對小孩子來說,這是一個他們能馬上捕獲並理解的意象。僅管是讓所有人嚇破膽的大妖怪,畫家Leo Espinosa依舊是用鮮艷活潑的色彩處理,不走悲情灰暗路線。
而Junot Díaz在《島國的孩子》的創作風格,我想是與《貧民窟宅男的世界末日》很相仿的。不打悲情牌,而是用一種讓人彷彿被陽光射進眼裡的刺癢,不得不瞇起了眼,去觀測萬花筒般的大千世界。因為光芒,使得一切顏色更加劇烈鮮明,卻也因為光芒,感受到刺卻不會真的傷了你。
比如說,在《貧》中,他透過一個沉迷於科幻文類的臃腫宅男,如海嘯般地間接傾倒出多明尼加共和國的楚希佑暴政歷史,連串的噤口、血洗、黑暗、否定、彎刀與洋香菜屠殺手段……楚希佑幾乎把多明尼加人當成他個人的魔多城(《貧》,頁243)。瘋狂之程度,與宅男奧斯卡所迷戀的奇幻/科幻文類幾乎如出一徹。小說並不嚴肅,它讓你不可置信地笑。然而有時往往是這樣,更襯出骨子裡的寒與慟,現實竟能如此超日常、荒謬、暴力。(當然,在閱讀楚希佑與他戒靈們時,很容易覺得熟悉)
《島國的孩子》也是如此,比喻簡單易懂,色調快活,仍然能夠講述曾被妖怪統治的時代。這讓我想起《班雅明先生的神祕行李箱》,同樣也是採類似路線在講述一個時代創傷與悲劇。
也因為妖怪的意象的多重指涉,它當然並不需要僅被指為獨裁者楚希佑。每個國家,都有過(過去式或現在式,都可以吧)讓人聞風喪膽的妖怪,讓人不得不逃離家園的妖怪。多明尼加有、台灣、中國、印尼、越南、印度、巴基斯坦、波蘭、德國……何嘗沒有?
在繪本的最後,蘿拉把音樂、舞蹈、顏色、芒果、海灘、鯨豚、妖怪、與打敗妖怪的女人男人們,一起放入她的島國畫像中。光亮與黑暗、笑聲與流血,唯有併置,島嶼才會跳出來,才能完整,創傷也終不需再被收起。
這幅對島國的美麗記憶,也並非要強調本質主義(比如血源論)。而是如同繪本一開始所言:這個學校裡有許多來自遙遠國家的孩子。繪本中很自然地穿插西班牙語,呈現多語聲道書寫(中文譯本較無法譯出),反映出Junot Díaz自身所處的多文化狀態。在《貧》裡,多語聲道則更為明顯與多元。我們都是來自某個遙遠的地方,如何把我們自己的島嶼畫像,完整地呈現,並與其他人一起貼在牆上,共構一幅新的島國,尋根才有意義。
「有時我們很害怕,但是我們也很勇敢」。
如果對楚希佑有興趣,再閱讀《貧民窟宅男的世界末日:奧斯卡.哇塞短暫奇妙的一生》(註三)。當然該國歷史還包括了「什麼?你不知道美國在廿世紀曾兩度佔領多明尼加?」。中譯本譯得非常賣力與用心,乃我最愛之譯者之作品。
- 註一:fukú, 一種符咒或厄運。一般相信是歐洲人到了伊斯帕尼奧拉島,才將符枯釋放到人間,而我們就狗屎上身至今。(《貧》,頁23–24)。
- 註二:zafa, 西班牙語,意指解除糾纏,免除危機(《貧》,譯者註17)。
- 註三:2019年6月出版社重新校訂出本版該書,更名為《阿宅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