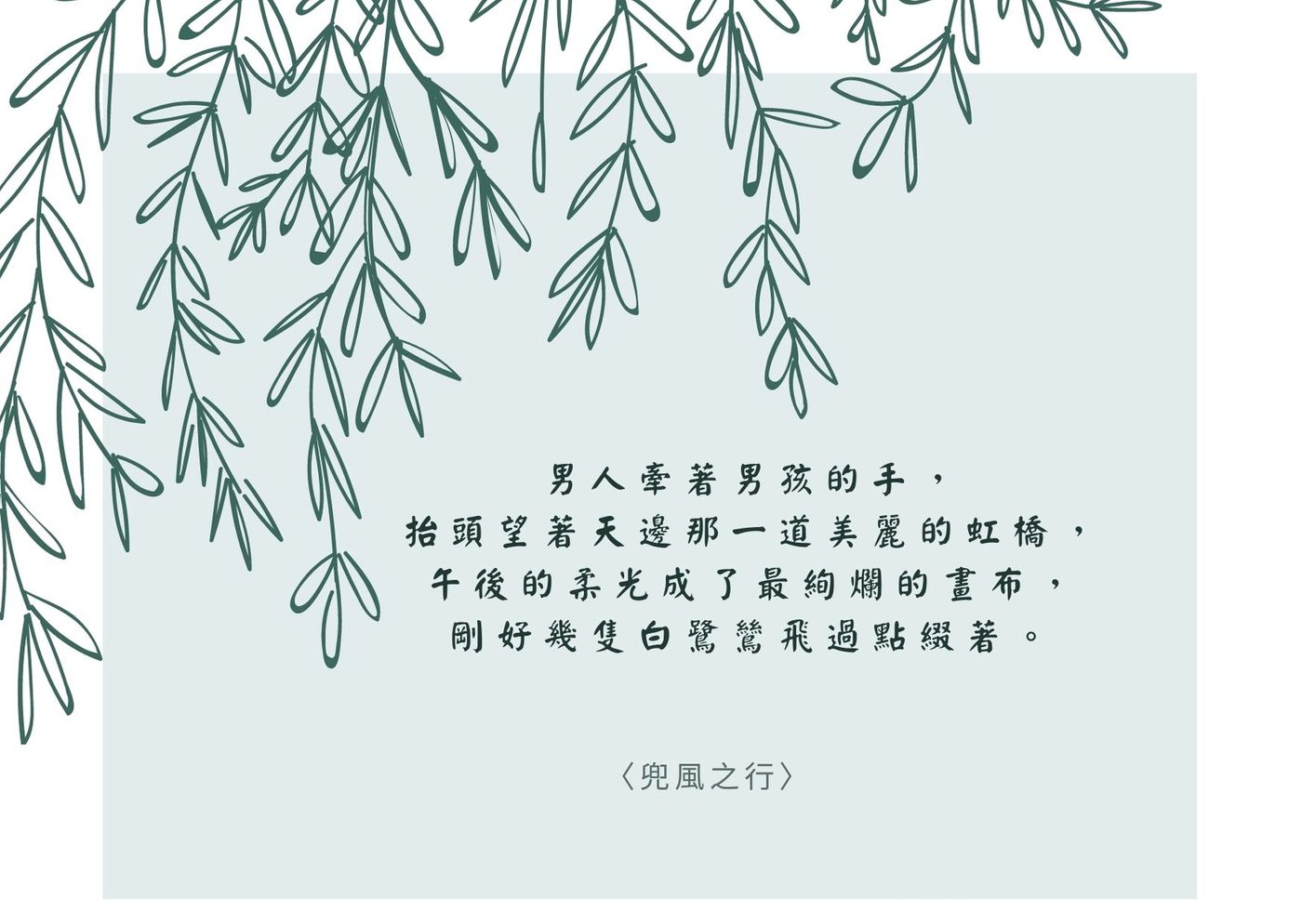躺在床上聽吉卜林工作室卡通配樂的音樂盒版本。
小兒子爬上床躺在我旁邊聽了一會兒,問:「你喜歡音樂盒子嗎?」「喜歡。」
「為什麼?」
有很多事情我不曾細想,愛一個人就是愛了,喜歡吃湯泡飯或是絕對不吃榴槤,都不會想去追究原因,總是要等被問到了才會開始想想,恩,為什麼會那樣喜歡音樂盒子的音樂呢?
想了想才慢慢地回答:「我喜歡那個聲音,跟一般的樂器不大一樣,有種特別孩子氣的天真可愛,同時聽上去又有點寂寞。」
其實還可以陰氣森森。在暗洞洞的屋裡響起音樂盒那種細碎的曲調還略微有點回音,馬上就是恐怖片的場景了。不過這個就不用說給十歲的小孩聽免得他做惡夢。
第一個音樂盒,是爸爸出差的時候從外地帶回來的禮物。
每次聽到人家說星座,講到巨蟹座,第一個提到的特質就是「很顧家」,這句話在我爸身上是很準的,他不管去到哪裡出差,都從來不買自己的東西,第一優先一定是買給媽媽的新奇玩意兒:像是台灣還沒有的家居用品,餅乾糖果玩具,珠寶首飾衣物,都是買給家人而不是買給自己的。
有一次他從國外回來,帶回來一個音樂盒給我。
淺色木頭盒子。上面畫著粉紅色的玫瑰花。蓋子掀開,裡面襯著絨布軟墊,用來放珠寶。一個小小的芭蕾舞孃穿著粉紅色紗裙,單腳站在圓形的小鏡子上。旋緊發條,芭蕾舞孃會隨著音樂翩翩起舞,在鏡子上一圈一圈轉著。
音樂是柴可夫斯基的天鵝湖。
當然是沒有首飾,拿來存放各式各樣我珍愛的小玩意兒:貝殼,石頭,羽毛,書籤,貼紙,造型迥異的橡皮擦.....放學路上撿到小塊的「寶石」,一顆碧綠一顆琥珀色(大了以後知道那不過是磨得光滑的啤酒瓶米酒瓶破片),幾顆碎米珠,全部都是孩子們眼中的寶物/成年人眼中的垃圾。
幼時一直做重複惡夢,幾乎夜夜驚喊著醒來,堅持床底下有怪物。我媽不堪其擾,終於給換了張新床,底下有抽屜的,邏輯是「床底下沒有空隙=怪物無處容身=沒有怪物」。
我爸照例的覺得媽媽過分縱容小孩,就像因為我怕黑就准許我開盞小燈睡覺一樣沒有必要。他覺得睡著了也看不見還開著燈浪費電,小孩半夜哭醒,揍幾次就好了。
不能說我爸是壞人,他有他的想法,而以他成長的環境來看,他對我也已經夠寬容,可比爺爺跟祖爺爺對待小孩要溫情得多。
媽媽在床底下的抽屜裡面墊了洗乾淨的舊毛巾,拿來存放床單枕頭套,還有冬天的毛衣大外套,放了樟腦丸免得蟲蛀。音樂盒就放在抽屜角落,躺在床上伸手拉開抽屜就摸得著的位置。
晚上跟父母親道過晚安,回到自己房間,躺在小床上,把音樂盒摸出來,旋緊發條,在昏黃的微光中聽著帶著金屬感的細碎曲調,看那個小小的芭蕾舞孃孤單的一個人旋轉,一圈又一圈,跳著沒有伴侶的足尖舞。
或是雨季中天色暗淡的午后,坐在窗前看著窗玻璃上雨滴滑落的軌跡,雨聲和著音樂盒,心緒沈澱得更外明澄,同時也寂靜而溫柔。
小兒子把頭親暱地靠在我手臂上,一會兒爬起來,睜著圓大清亮的眼珠:「我覺得音樂盒的聲音很悲傷。」
也許在某些人耳中,音樂盒的聲音很悲傷,我只覺得音樂盒的聲音連結到還沒有失去母親的童年時光,當時一切仍然溫柔而美好,在音樂聲中慢慢鬆弛,於是得以舒適的進入無夢的睡鄉。
他抱我一下。「你要不要一個魔術親親,I can kiss your sadness away。」
「當然要。」雖然我並沒有什麼好悲傷的。
「那,一個親吻加一顆糖果,那通常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我笑了,啊,如果一切都可以用一個親吻加一顆糖果解決,這個世界想必會變成一個簡單快樂點的地方。
他很響亮的在我臉頰上啾了一下,然後跳下床,跑去儲藏室拿了一顆水果味的mentos來餵食,恩葡萄口味的,lucky。
仍然很喜歡音樂盒,以後聽到音樂盒子的音樂,大概也會想到此際這個跟兒子相親相愛的片刻吧。
而且是葡萄口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