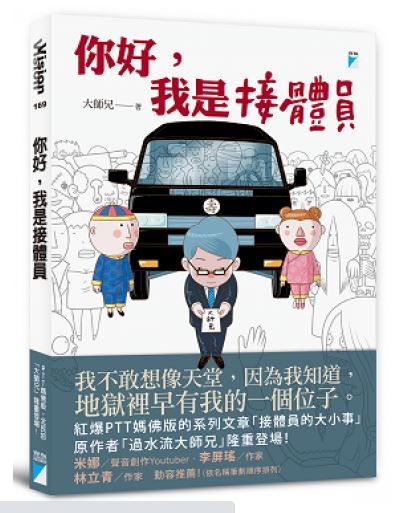闔眼之前與之後,其實也差不了多少。
我想。
會這樣覺得,大概跟林老先生脫不了關係,林老先生在闔上眼之前,終究沒有機會看到他心心念念、時時刻刻掛在嘴邊的夕陽。不過這裡一天到頭下雨,最後會是這種結局,也是沒辦法的事。
喪禮辦得簡單,家屬大概付了一大筆錢給殯葬業者,連整理屋內也由他們一手包辦,等我下班趕到時外頭已清理得差不多,沒有搭棚、沒有嗩吶和樂手敲鑼打鼓、沒有孝女、甚至沒有見著林老先生的其他家屬。
兩個年輕員工套著黑色短袖制服,站在路邊的垃圾與老舊傢俱旁,手裡各夾了根菸,等待清潔隊員開貨車前來運走,我走上前去,和他們打幾聲招呼。
「清完了嗎?」
輕鬆站著的兩位員工先是面面相覷,約莫半秒後,其中一位才開口反問,「你是他的家人嗎?」
「不是,我只是剛好也姓林,之前會來幫忙老先生的……」
我一時語塞,癟起嘴,忽然不確定自己的定位,嚴格說起來不太算是朋友,也不是社工或志工,就只是因緣際會下認識,覺得有些可憐,同情心氾濫,因此三不五時撥空前來幫忙的關係。腦袋又轉了幾圈,最後還是選了最為方便,不需解釋太多的一個選項,「呃,志工。」
「志工?」另一個較矮的員工忍不住插嘴。
「喔喔林先生對吼,之前家屬好像有提到你。」
「咦?」老實說我有些訝異,雖然林老先生的兒女知道我每週都會前來陪他聊聊或出門走走,但從未對此表示過什麼,這次忽然想起有個人陪伴林老度過最後幾年,說不定會好好獎賞我一番──怎麼可能,大概只是想將不要的東西一併扔給我吧?
「他們說了什麼?」
「好像是跟火化有關的事,詳細我不太清楚,你可以進去問問陳大姐。」
「陳大姐?」
「就是那個捲捲頭那個,你進去就會看到。」我點點頭跟他們道謝,穿過菸霧,走進敞開的舊鐵門中。
地板很髒,白瓷磚布滿混亂鞋印,原本單調無比的客廳現在似乎更加空洞,白蒼蒼的牆面上長了些壁癌,雜物一箱箱塞在角落,搬家公司和清潔公司的人正打算將彈簧床搬出樓梯口,忙得不可開交。看起來廉價的棕色捲捲頭應該是陳大姐吧?她同樣穿著黑色制服,背對門口指揮其他人動作,我湊近,清清喉嚨:「陳大姐嗎?」
和外頭年輕人一樣,她轉過身來上下打量我一番,稍稍思考數秒,才爽朗露出兩排黃牙,「林先生?」
「是的,林先生。」
「來,有一點東西是林老先生要留給你的。」
「嗯?」
「你等等──喂喂那邊會卡到牆壁啦!」
陳大姐嘴裡唸著「抱歉嘿等我一下⋯⋯」,再度忙碌了起來,我點頭示意,乾脆暫時退到一旁,等了大概十幾二十分鐘,她才大致處理好樓上搬下來的大型傢俱。
這十多分鐘並不好受,我到外頭跟另外兩位員工擋了根菸,這裡一點也不像剛辦完喪禮的地方,反倒像是搬家時的最後確認,而我是與屋主有最接近關係的人,卻無權決定任何事情。
說有最接近關係……也許從頭到尾都是我自己一廂情願,早就被貼上想分遺產或詐騙的標籤,連有名無份這樣的形容詞都稱不上,結果現在勒,還是只有我出現在這裡。
第二根──好吧,跟別人借了兩根菸是有些厚臉皮,啊,無所謂,矮子員工的白眼是一時的,反正以後應該不會再見面了。第二根菸抽到剩菸屁股時,陳大姐才踏出那老舊的破敗的門,一口肝功能不好的臭氣噴在我臉上,「久等了久等了。」
「不會不會,大姊辛苦了。」
「那個啊,家屬說要留給你的,他們說畢竟你陪林老好一陣子了,理應留給你才是。」
「他們是指?」
「大兒子說的啦!他是說他們最後這樣決定。」
「好⋯⋯所以是什麼東西?」我還是十分困惑。
「我們的員工去拿了──啊,剛好回來,他在那裡。」
我順著陳大姐的手勢,不遠處一輛小客車剛熄火,中年發福的男人推開車門,雙手捧著乳白色大罈搖搖晃晃走來,看不清上頭照片。
「等一下,林老的骨灰?」
「對啊,家屬說要留給你的。」
*
陳大姐留了家屬的電話給我,打過去四五次,也傳了簡訊,一點也不意外,沒有任何回應。
同時問了塔位的事,一個月要將近一萬元,我手邊沒有餘裕,也不知道要以怎樣的理由跟家裡的人解釋,去籌措這筆經費。
煩,真的很不負責任。
手機震動,老婆打來的,「喂,怎麼了?」
「你在林老那裡嗎?狀況怎樣?」
「狀況喔……」我轉頭看著副駕駛座的骨灰罈,伸手幫它繫上安全帶,嘆了口又長又深的氣,「不怎麼好處理。」
沒想到林老這次坐我的車卻是以這樣的形式。
林老其實是喜歡坐車的,只是一直沒有機會,上次是什麼時候來著?啊,對啊,那天原本天氣不錯,我也提早下班,想說載林老出門看看夕陽,沒想到忽然傾盆大雨,只得作罷。我還記得他坐在後座,明明滿臉失望的神情,卻還裝作毫不在意,不停用台語唸著「無要緊啊,也毋是足稀奇的物仔……」
雖然不是我的錯,我還是莫名感到愧疚,對他說了聲抱歉。
「是嗎?那你回家吃晚餐嗎?」電話另一頭問道。
「會,可能會晚一點。」
「好,路上小心。」
掛上電話,黃澄澄的太陽離地面還有一段距離,看起來比平時更加巨大,隨時都會爆裂開來的鵝蛋黃。記得沒錯的話,林老的兩隻眼睛這兩年早已退化得差不多了,積上灰塵的眼皮皺褶後頭,大概只能感覺到光亮強弱的變化吧?但他還是執著於夕陽這件事。
我並不非常清楚林老為何如此執著,可能和他的孩子們有關?好像聽他說過,年輕時曾帶著他們到海邊還山邊看過夕陽?要是沒記錯,他的三個小孩似乎都頗有成就,大兒子和小兒子在學校當老師,女兒似乎也有不錯的工作,可怎麼會變成現在這樣呢?聽說大兒子退休後還跟著慈濟到處關心獨居老人,但是自己的父親能不見就不見,連死後都要將骨灰扔給別人來處理。
林老先生雖然有時候難以溝通,大部分時間還滿好相處的,老人總是會在某些微不足道的點上固執己見,好吧,這倒不一定,畢竟我只是個外人,很多時候表面上和藹可親的人,家裡的問題都比想像中更加艱困且難以解決。
要是當初沒搬到這附近,不知道林老最後這幾年會變得怎樣,或許不干我的事,我不會知道林老先生的存在,也不會在回家途中差點撞上他而彼此認識,甚至成為他獨居在此最後的僅存的依靠。
說依靠似乎有點太自負了,我又扭頭看了看骨灰罈,再盯向後視鏡裡的自己。
模模糊糊的,我甚至有點看不清自己的面貌。
最後還是發動車子,緩慢開動。
估計回到家也無法將骨灰罈帶進家門吧?家裡兩位老頑固絕對無法理解我在做些什麼,負責處理別人家的骨灰?別開玩笑了,若是親戚還能稍微讓步,但完全沒有血緣關係的人死去,他們絕對不想插手、甚至擺在家裡祭拜啊?也不知道該怎麼跟老婆解釋……
太陽快要下山了,我心一橫,朝附近的小山丘開去。
*
如果要論不負責任的程度,我是絕對比不贏林老的子女們的。
我何德何能?就只是個多管閒事的傢伙。可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即便退一百步,不道德的事情是可以拿來比較的嗎?
你比我更不孝,我比他更不敬老尊賢,他比你更棄父母於不顧。
有夠荒謬。
我停下車子,將骨灰罈一把抱起,冷冰冰、沉甸甸的,彷彿罈內裝滿石頭。粉末也可以這麼重嗎?應該大部分都是罐子的重量?
這裡是不錯的位置,結婚以前常來,自公路旁延伸而出的荒草與峭壁適合一個人沉思,也適合觀賞日落,沒帶過其他人來,我自己的秘密基地。選了靠近崖邊的地方,確定土石不會崩落,小心翼翼坐下,撥開雜草,將罈放在地上。日頭正好移動到最適當的角度,地平線上緣沒有浮雲之處,又紅又腫,不刺眼,絢爛如畫。
額間冒出幾滴汗液,我就這樣呆坐在骨灰罈旁,要是有人經過,大概只會感到詭異而加速離開,遇到神經病。這座小山雖鄰近市區,但也有幾處孤墳,和林老有點像,只是他們年代更久遠,還多了磚瓦堆成的假房子。
夕陽下沉的速度很快,夜空帶來的黑暗自後頭逐漸覆蓋而至,如果林老能說話,不知道他會說些什麼?我的鼻子突然有點酸,沒有人要的老頭子,甚至連最後的朋友也曾想拍拍屁股走人。
我承認在行車途中,曾經有股強烈的衝動想將骨灰罈丟在這兒,畢竟,我的罪孽遠不及林老的子女,收下陳大姐給的骨灰罈也已經是仁至義盡,而林老生前又心心念念著日落之景,這樣反倒是最好的選擇。
我搖搖頭,又嘆了口氣,一掌放在骨灰罈上。
「嗯?」
有那麼一瞬間,掌心的觸感就像拍在老年人細瘦的臂膀上,但隨即恢復瓷器的冰冷,我想了想,再度抱起罈罐。
「林老你可能要辛苦一下,先暫時住在車子裡了,明天再帶你上來看夕陽吼──」